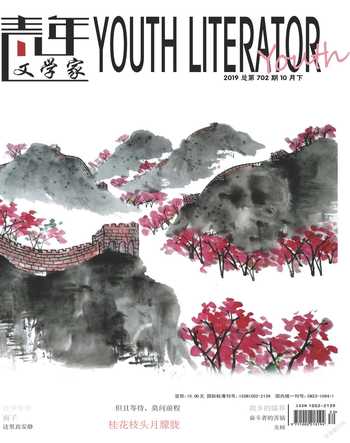論《人間詞話》中所蘊含的憂患意識
摘? 要:憂患意識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中國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傳統,這一憂患意識也包含在《人間詞話》中。一方面,王國維將憂患意識——憂生憂世作為其批評觀念。在這一觀念的指導下,王國維將詞劃分為憂生與憂世之作,并表現出對于憂患之作的欣賞與推崇;另一方面,王國維將儒家以憂患意識為基礎所構成的“修己以安天下”的精神境界與精神目標作為文學批評標準,納入文學批評實踐之中。
關鍵詞:儒家;憂患意識;王國維;人間詞話
作者簡介:袁竟蘭(1994-),女,漢族,六安人,安徽師范大學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30-0-02
儒家的憂患意識形成了中國自古以來的以憂為主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傳統,王國維在文學批評中滲透著這一憂患意識。一方面,王國維憂將憂生憂世作為其批評觀念。在這一觀念的指導下,王國維將詞劃分為憂生與憂世之作,并表現出對于憂患之作的欣賞與推崇,體現出其直面人間憂患的悲天憫人的情懷;另一方面,王國維將儒家以憂患意識為基礎所構成的“修己以安天下”的精神境界與精神目標作為文學批評標準,納入文學批評實踐之中,體現其勇于承擔人類憂患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
一、憂生憂世的批評觀念——悲天憫人之意識
“儒家的憂國患民‘憂世’情懷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亦是千百年來維系國家民族發展的文化情愫。”[1]憂世情懷即是憂患意識的表現。憂患之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浩如煙海,憂患意識也是貫穿于中國文學史發展的一種歷久彌新的情感。王國維敏銳地察覺到這一種情感,將憂生憂世作為詩詞的劃分標準,而在對于憂生憂世之作的評價中,流露出對這一類作品的喜愛的審美情感,顯現出他對于人生與世間的悲憫情愫,這一情愫便是憂患意識的內在表現。
(一)憂生憂世的劃分標準
在《人間詞話》第二十五則中,王國維將詩詞劃分為憂生與憂世之作。他引用《詩經·小雅·節南山》第七章的詩句:“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認為這是憂生之作;而憂世之作,則是引用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中的詩句:“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作為代表。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一句顯露出作家一人在偌大的世間漂泊無依,毫無歸屬之感,一種蒼涼凄冷的情感撲面而來。這一種情感顯示了詩人精神上的空虛與寂寥;這就是憂生之感;“憂生是對于生命的憂患,抒寫個體對生命的理想、焦慮、追求、失望”。在這一憂患中,個體往往會表露出對于宇宙的感慨,“一種無法揮除的孤獨感貫注其間,它的情調總是悲愴的”;“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一句描繪出詩人所處時代的急功近利的風氣,表露出詩人對于世風日下的時代風氣的深深的不滿和憂患。這一憂患便是憂世之患。“憂世是對于人世的憂患,以抒寫人情事態,展示人間百相為底本揭示人世的困厄、艱難、凋敝”。[2]憂生之作一般抒發自身之感,通常是悲壯的;而憂世之作的情感則具有超越性,是詩人明知前方人世間萬般險惡,卻憑著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直面痛苦,徐徐前行。正如歷代儒家先賢縱使不被重用,卻依舊為國為民,“終日馳車走”。由此可見,憂生憂世蘊含了憂國憂民之意。
總的來說,無論是憂生還是憂世之作,都是作家憂患意識的產物,都屬于作家的憂患之作,是儒家憂患意識在文學作品上的體現。王國維用憂生憂世兩類標準劃分詩詞,凸顯了他對于憂患之作的憂患內容的深刻理解,也是對于儒家憂患意識的深刻感知和感悟。
(二)憂生憂世的批評實踐
王國維不僅僅是將憂生憂世作為詩詞劃分標準,更是將憂生憂世作為其批評觀念。在這一觀念的指導下,“王國維對表達了‘憂生憂世’感受和承擔人生苦難、在人生旅途上含淚行進這種悲壯精神的作品就情有獨鐘。在《人間詞話》中,他最為稱道的詞都有這種性質”。[3]
在《人間詞話》中,王國維對李白《憶秦娥》中“西風殘照,漢家陵闕”一句大為稱贊,認為“寥寥八字,逐關千古登臨之口”,及具有“氣象”。[4] “就是因為它含蘊了一種‘時間摧毀一切的傷痛’”。[5] “西風殘照,漢家陵闕”一句,詞人通過對于漢赫赫王朝的遺跡——陵墓的意象的擢取,從而進入了歷史的反思和對現王朝未來的憂患中。古道悠悠,音塵杳然,繁華,奢侈等一切都被埋葬在時間里,而只剩下陵墓樹立在如血的殘陽中。由此,一股悲壯憂愁的情感油然而生,詞人對于現世的王朝的憂患之情滿含在其中。而后,王指出范仲淹的《漁家傲》“差足續武,”[6]因為范仲淹寫出了“將軍白發征夫淚”的思鄉之憂與為國獻力之壯,側面烘托了戰爭的殘酷,由憂世而引起的悲壯的精神滲透進一字一句中。在第十三則中,王國維認為李璟《攤破浣溪沙》一詞中“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一句要比“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更加好,因為前一句抒發了美人遲暮之感,這是一種普遍的人類的情感,是對于時間不可逆的憂患之情,后一句則是表現思婦個體的情感。前一句由個人上升到對于時間,對于人類的憂患而產生的悲痛之情。
從王國維對于李白、范仲淹、李璟等詞的評價中可以看出王國維自己對于憂生憂世之作的推崇以及對于這些作品之中的悲壯的感情的由衷愛惜。“敢于直面人生痛苦、展示人生真相,并在直面、展示中表達一種承擔的悲壯,是他心儀的文藝作品的共同的內涵”,[7]表現了王國維直面人生憂患的悲憫情懷。
綜上,王國維在憂生憂世的觀念下,將憂患之作進行了區分,并在批評實踐中,表達其對于直面憂患的憂生憂世之作的欣賞,展現了其思想深處所受到的儒家憂患意識的侵染。
二、修己、安天下的批評標準——承擔責任之實踐
儒家憂患意識的存在,成為儒家先賢不斷追求世界之道的動力。這一自覺意識和歷史使命感熔鑄成為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目標。這一理想目標的第一步便是修身,即自我實現。“自我實現內在地關聯著 ‘安人’、‘安百姓’、‘博施濟眾’”。[8]《論語》記載“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9]修己即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安人、安百姓則是指社會整體的穩定和發展,這里,體現了儒家學人將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 自我完善與社會穩定統一起來的思維路向。
“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體現了儒家敢于承擔的救世精神,而王國維則將“修己”與“安天下”分別作為《人間詞話》中詞的批評標準,這兩條批評標準是王國維對于儒家這一精神境界的重視以及推崇的一個表現。
(一)重人格以修己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學之事,于此二者不可缺一。”[10]王國維將內美作為文學的必備要素之一,內美即是“美好的心靈”[11]對于內美的重視即是對于人格修養的重視,也就是對修己的要求。只有具有內美之人才能寫出偉大之作,正如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提出:“三代一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茍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學者,殆未之有也”,在這里,王國維明確地提出了人格修養與作家之關系,高尚之作家必定有高尚之人格。所以在這一理念的指引下,王國維將人格認定為詩詞批評的一大標準。
在評判東坡與稼軒之詞時,王國維說道:“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懷有東坡和稼軒這樣寬廣的胸襟方可寫出有此等風格之詞。再者,將東坡與稼軒之詞和夢窗、梅溪之詞進行了比較,“蘇辛之詞狂,白石尤不失為狷,若夢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輩,面目不同,同歸于鄉愿而已。”運用《論語》中形容他人品格的詞語來說明各家詞作的風格。且不論鄉愿一詞形容夢窗等人的詞作是否合適,從這句話中,王國維用人格來評價作品,顯出其對于作家人格修養的重視,對于“修己”的重視。
“厭惡‘鄉愿’而首肯‘狂娟’,無疑是為詞人的人格、道德修養樹立了又一正確標準”。[12]將人格作為批評標準,奉行“文如其人”的批評法則,凸顯了王國維對于作家人格修養的重視,這一批評標準也為作家提出了“修己”的要求。
(二)“擔荷人類罪惡之意”以安天下
修己則是從自身來說的,而儒家的精神目標的落腳點是“安天下,”也就是“平天下”。“安天下”是追求全人類精神解脫的精神境界,這是儒家自覺承擔起社會和人類責任之所在。受儒家影響,王國維便將“安天下”作為批評的又一標準。
《人間詞話》第十八則說:“‘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后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生世之戚,后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故都為“血書”。但是《燕山亭》詞與李后主的詞有根本區別,宋徽宗的詞只是在感慨身世之悲,是其個體意識的呈現,而李后主有擔當人類苦難的自覺,他的詞所關注的并不是個人,而是全人類,他將自己的身世之感上升到人類普遍情感的高度,融匯了人們生存中的失意悲傷,寫出了人類的共同感。
王國維在對白石的詞進行批評時,認為白石之詞無內美,祖保泉先生則認為這一評價切中要害,他在《關于王國維三題》中提到:“姜白石一生是個高級清客,寄食四方。在社會,他好像沒有什么責任,他只游離在社會生活的漩渦之外。什么異族侵略,山河破碎,人民流離,都很少在他腦里盤旋。因而他的詞的內容,絕大多數是較為空洞的個人情趣,極少數的略略帶有時代色彩。”
在詞作的批評中,王國維對于承擔人類、社會責任的作品的情有獨鐘表現了他的高尚的思想境界,這一思想境界與儒家“安天下”,將天下解脫作為自己的任務的精神境界不謀而合,顯現了王國維思想深處所受到的儒家思想的熏染。
結語:
儒家的憂患意識經歷過從孔子到孟子的發展,從憂道到憂國憂民,其涵義在不斷豐富和發展;而這一憂患意識為儒家的“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精神目標的設立提供了無窮的動力,也激勵了歷代儒家先賢為國為民勇于承擔社會乃至人類的責任。而從《人間詞話》中憂生憂世的批評觀念和以“修己”與“安天下”為批評標準的批評實踐中可以窺見王國維思想中的儒家憂患意識的存在。
注釋:
[1]楊萬歡.阮籍的用世之心與憂世之情[J].文史博覽(理論),2009(08):33-34.
[2]劉鋒杰、章池.人間詞話百年解評[M].合肥:黃山出版社,2002:128.
[3]程亞林.近代詩學[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196.
[4]王國維.人間詞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2.
[5]程亞林.近代詩學[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196.
[6]王國維.人間詞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2.
[7]程亞林.近代詩學[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197.
[8]鄒振卿.先秦儒家的憂患意識與救世精神[J].常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1(03):62-65+88.
[9]楊伯俊.論語澤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221.
[10]王國維.人間詞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17.
[11]陳鴻詳.人間詞話·人間詞注評[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282.
[12]方智范、鄧喬彬、周圣偉、高建中.中國詞學批評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474.
參考文獻:
[1]邵漢明.中國文化研究二十年[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2]劉鋒杰、章池.人間詞話百年解評[M].合肥:黃山出版社,2002:128.
[3]程亞林.近代詩學[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4]楊伯俊.論語澤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
[5]陳鴻詳.人間詞話·人間詞注評[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