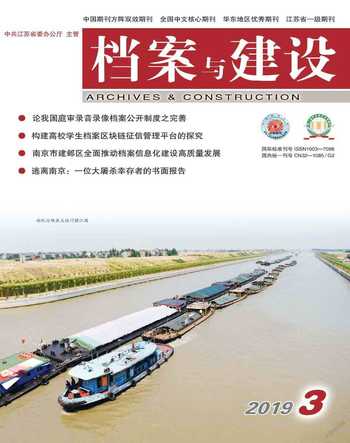數字人文環境下檔案信息傳播服務的新思考
張澍雅
[摘要]數字人文是人文學科與信息技術交叉研究的新領域,從數字人文角度探討檔案信息傳播服務有很強的現實意義。論文通過對檔案信息傳播服務歷程與傳播模式進行探討,厘清數字人文與檔案信息傳播間的關系,同時,從信息傳播效果形成和效果分析兩個層面闡述數字人文對檔案信息傳播的影響,并提出應從創新傳播理念、融合傳播技術、探索合作模式、深化傳播層次等方面思考檔案信息傳播服務。
[關鍵詞]數字人文檔案信息信息傳播
[分類號]G270.7
New Thoughts on Archiv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ervice under Digital Humanistic Environment
Zhang Shuya
(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Digital Humanities is a new field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Humanitie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t has a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archive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er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humanity and archiv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archiv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ervice process and transmission mode.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expounds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n archiv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effect formation and effect analysis.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thinking about archiv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ervice from the aspects of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concept, integra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xploration of cooperation mode and deepening of communication level.
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Archives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英國哲學家培根曾說:“知識的力量不僅取決于它本身價值的多少,更取決于它是否被傳播,以及傳播的深度與廣度”。國家的發展離不開傳播、社會的進步離不開傳播、個人的成長也需要傳播帶來的文化積淀。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激發全民族的文化創造活力;推動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1]。政策的提出為檔案傳播服務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檔案作為見證國家歷史文化的重要記錄,檔案的價值在于利用,利用的前提在于傳播,傳播的影響力在于傳播效果發揮,而傳播效果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從我國檔案信息傳播歷程來看,檔案傳播方式已實現從一元到多元、簡單到復雜、封閉到開放的轉變,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數字人文涉及多學科、多領域,它的出現將影響檔案信息傳播服務方式,檔案傳播服務也需要接受數字人文技術,整合傳播模式,創造檔案信息傳播服務新常態。
1數字人文的內涵與研究現狀
1.1數字人文內涵
數字人文的歷史可追溯到1949年的人文計算。2001年《數字人文指南》一書出版后,“人文計算”被“數字人文”所取代。當前學界對數字人文的本質存在不同的看法,包括將其視為研究領域、實踐方法、通用方法、社區、解決人文問題的計算工具等[2]。對于數字人文定義的界定,王曉光教授和徐力恒博士認為“數字人文”的內涵是不斷發展的,不同時期不同領域的人對其內涵有著不同的認識[3]。王曉光教授認為數字人文將改變人文知識的發現、標注、比較、引用、取樣、闡釋與呈現,從而實現人文研究與教學的升級和創新發展[4]。數字人文通過可視化、文本挖掘等技術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各種可數字化資源進行研究,不斷推進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為其提供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新視角。
1.2數字人文研究現狀
以“數字人文”為主題詞在中國知網期刊庫中進行檢索,截止到2019年3月,共檢索出348篇文獻。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數字人文基本理論、技術驅動下的人文學術實踐、合作模式下的人文學術變革、數字人文下基礎設施建設四大方面[5]。在研究領域上,“數字人文”的研究主要分布于信息科技、哲學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經濟與管理科學領域,充分體現了學科間的交叉性。其中,圖書情報學是數字人文主要的研究領域,研究內容包括國內外圖書館的數字人文研究進展、圖書館數字人文項目建設、數字人文架構下圖書館定位、圖書館數字人文架構和館員設置等。
1.3數字人文在檔案學領域研究現狀
理論研究層面。以“數字人文+檔案”為檢索詞在中國知網期刊庫中進行主題檢索,去除不相關文獻,共檢索出14篇,從研究情況上看,當前數字人文在檔案學領域的理論研究還相對較少。在檔案學與數字人文關系研究上,加小雙認為檔案概念在文件管理領域和數字人文領域研究中出現脫節情況,提出檔案學與數字人文應在充分對話和互動融合的基礎上謀求協同合作,并強調數字人文不能在檔案學建設過程中缺位[6]。在檔案工作與數字人文關系研究上,吳加琪介紹了數字人文的內涵,對數字人文參與檔案工作的需求進行分析,提出檔案工作數字人文建設的參與機制[7];龍家慶等厘清了數字人文與檔案事業的聯系,并從多個角度分析數字人文對檔案工作的影響,探索新時代檔案事業發展與數字人文相結合的規律[8]。在檔案資源開發與數字人文關系研究上,張衛東等將數字人文方法引入檔案資源整合中,實現從“數字技術”維度把握和優化檔案資源開發與整合路徑[9]。在檔案領域數字人文實踐項目研究上,趙生輝闡述了國外檔案領域數字人文項目建設概況和特征,得出我國檔案領域數字人文建設的啟示[10]。
實踐探索方面。目前檔案“數字記憶”研究迅速發展,而“數字記憶”與“數字人文”實則有許多共同之處。雖然“數字記憶”側重于對資源的長期保存,維護記憶的長期可獲取性,“數字人文”更多強調利用數字技術進行資源整合、開發,輔助人文學科開展學術研究,但二者在資源整合、處理、存儲、利用、展示等方面均可相互借鑒。因此,可以說檔案領域在某種程度上已參與到數字人文的建設之中。如馮惠玲主持的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歷史文化村鎮數字化保護與傳承的理論、方法與應用研究”,其實質正是數字人文與檔案理論實踐的融合。
2檔案信息傳播服務的發展歷程與發展模式
傳播是指處于社會系統中的人應用媒介進行的信息交流,這些交流往往伴隨著一定傳播效果的發生[11]。傳播具有四個特點:它是人類特有的社會活動;需應用相關傳播媒介;傳播活動的目的在于信息交流;傳播活動必須實現一定的傳播效果。檔案信息傳播是實現檔案信息服務的有效途徑,也是實現檔案信息價值的重要手段。研究檔案信息傳播服務的發展歷程與模式將有助于改善現有傳播方式,更好地滿足公眾對檔案信息的需求。
2.1檔案信息傳播服務發展歷程
根據檔案工作的實踐情況和理論研究的發展,可將檔案信息傳播服務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12]。第一階段為檔案信息傳播的起步階段。20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國檔案工作處于恢復發展時期,檔案主要用于機構內部查檔或學術研究查閱,總體來看檔案信息傳播局限于機構內部,屬于檔案信息的單向流動。第二階段為檔案信息傳播服務的初級階段。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檔案法》中明確規定公民具有利用開放檔案的權利,給檔案信息傳播帶來了新的機遇。與此同時,檔案編研成果的不斷發展和檔案網站的建立也為公民利用檔案提供了條件,檔案信息受眾由機構內部擴展到社會公眾,屬于檔案信息的單向傳播階段。第三階段為檔案信息傳播服務的發展階段。21世紀初至今,隨著信息化的不斷發展以及《全國檔案信息化建設綱要》《檔案事業“十三五”規劃》的頒布實施,檔案信息傳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檔案信息傳播方式逐漸發生變化,從檔案展覽、檔案網站建設逐漸擴展到檔案微博、檔案微信公眾號等新媒體的應用。檔案館的角色定位也在發生改變,開始關注公眾需求,如上海檔案館舉辦的展覽《信仰的力量——中國共產黨人的家國情懷》;為響應“一帶一路”政策,在深圳舉辦的《錦瑟萬里,虹貫東西——中俄“絲綢之路”歷史檔案展》;檔案部門在革命圣地開展歷史文化講堂等。檔案信息內容由實踐需要發展為探尋知識、傳承文化,檔案信息傳播從單向傳播轉為互動傳播。縱觀我國檔案信息傳播發展歷程,它的發展只能說是初步實現了人們的檔案信息需求,知識時代對檔案信息傳播發展帶來更大機遇和挑戰,需發揮聰明才智迎接時代需求。
2.2檔案信息傳播服務發展模式
傳播的重點在于如何將信息有效地傳播給受眾,而傳播模式則是通過簡明易懂的模式描述和解釋復雜的傳播過程[13]。徐擁軍基于傳播學視角來研究檔案工作[14],總結出了檔案傳播模式,涉及檔案信息源、檔案信息傳播者、檔案信息傳播媒介、檔案信息受眾、檔案信息傳播效果五方面。第一,檔案信息源即檔案的擁有者,包括檔案館、各種組織機構、社會大眾等,其中檔案館在檔案信息傳播源中占主導地位。第二,檔案信息傳播主體是檔案館和檔案信息專業人員,他們是檔案信息傳播的“守門人”,是傳播過程中的第一環節,通過對檔案信息的篩選、整合、加工、處理,滿足利用者的檔案信息需求,實現既定的傳播目標。第三,檔案信息傳播媒介,它經歷了印刷媒介、電子傳播媒介和網絡傳播媒介階段,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社交媒體在檔案信息傳播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如利用微博、微信公眾號等方式傳遞檔案信息,增強了信息交流的互動性。數字人文環境下,人們對信息傳遞方式的要求越來越高,它改變了信息流動模式和公眾的信息思維方式,這對檔案信息傳播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第四,檔案信息受眾即信息的接收者、反應者和解讀者,不同受眾對于同一信息會產生不同的反映,檔案信息傳播應在充分了解受眾心理的基礎上,選擇恰當的方式進行信息傳遞。第五,傳播效果是指傳播者的傳播行為對受眾或整個社會帶來的作用或影響,包括認知、情感和行為三個層面[15],檔案信息傳播效果是衡量信息傳遞影響力的重要標準,檔案工作者應關注傳播效果并進行不斷優化。
3數字人文環境下檔案信息傳播服務效果分析
無論是有意識的傳播還是無意識的傳播,都會產生相應的傳播效果。而傳播過程的復雜性、人類自身的復雜性和社會環境的復雜性,都會影響傳播效果,因此,從效果形成和效果分析兩方面進行論述,能夠理清數字人文在檔案信息傳播中的優勢。
3.1效果形成
影響檔案傳播效果的內部因素——信宿(即受眾)。受眾不同的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經濟狀況等因素,使他們在信息接收能力上存在較大差別。不論是檔案館提供的實現查閱檔案的被動傳播方式,還是利用社交媒體如微信、微博等主動傳播檔案信息的方式,往往忽視了受眾間的差異性,傳播效果沒有較好地實現。面對受眾間的差異性,如何有針對性地傳播檔案信息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人文社科類的研究往往注重定性分析,對事物進行“質”的方面的分析,而數字人文的出現將給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帶來新的理念,即通過引入定量分析、可視化技術[16]等手段,分析受眾對檔案信息需求的差異性,針對受眾間的差異,有針對性地提供檔案信息服務。
影響檔案傳播效果的外部因素——信源、傳播內容、傳播媒介。首先,信源即信息的傳播者,檔案信息的傳播主體為檔案館,檔案館往往通過編研的方式整合檔案信息資源,但所涉及內容往往局限于本館館藏。科學研究的核心是進行開放式探索,技術的變革則促進了研究者間的交流與合作[17],它一方面豐富了學習工具和拓展了研究網絡,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學習門檻。數字人文增強了信息資源的流動性和可獲取性,促進了不同領域間的交流與合作,實現了知識的傳播與共享。其次,傳播內容是實現信息傳播的前提,內容質量將直接影響受眾的感受,因此選擇恰當的傳播內容至關重要。而傳播內容的選擇往往伴隨著傳播技巧的實現,傳播技巧是為了達到預期目的而采用的策略方法,因此在選擇傳播內容時可結合文本分析法、內容分析法、情感分析法等方法,深入挖掘用戶需求。最后,傳播媒介是信息傳播的中介,信息傳遞必須依靠傳播媒介來實現。現代技術的進步推動了檔案傳播媒介的變化和發展,當前檔案信息主要通過展覽、影視媒體、社交網絡等方式進行傳遞,而數字人文時代的檔案傳播可利用可視化技術,將檔案數據轉化成圖像展示出來,并通過虛擬現實技術和增強現實技術,讓用戶通過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直接感受虛擬空間中的事物,使他們有身臨其境之感。
3.2效果分析
傳播效果可從認知、情感和行為三個層面來分析。認知效果是指用戶感受到的檔案信息存在狀態,是最基本的傳播效果;情感效果是在認知效果的基礎上,受眾所產生的情緒,并從中得到共鳴;在情感效果的基礎上對受眾的行為產生影響的則是行為效果,它是傳播效果作用的最終歸宿。當前檔案信息主要通過大眾傳媒的方式進行傳遞,在傳播學理論中,“議程設置功能”從人們的認識層面出發,認為“人們對當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認識主要通過大眾傳媒來進行判斷,從而強化某一話題在受眾心中的重要程度”[18],通過大眾傳媒的方式傳播檔案信息固然重要,而傳播哪些內容則更值得我們思考,從而在此基礎上利用大眾傳媒來固化受眾對檔案的認識,因此對檔案傳播內容的篩選尤其重要。數字人文時代的到來給傳播者帶來了福音,他們可以利用輿情分析、文本分析來確定檔案信息傳播的著眼點,既滿足了受眾對檔案信息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固化了人們對檔案的認識,提高社會的檔案意識。“知溝理論”則是從傳播技能、知識儲備、社會交往、對信息的選擇性接觸等方面來闡述傳播中的階層分化[19]。由于傳播受眾的文化習慣、經濟地位的不同,導致他們在信息獲取渠道、閱讀、知識儲備等方面存在差異,而檔案信息傳播要想縮小這種差異,需要在傳播方式上進行改變。身臨其境的感受要比單純講述更讓人印象深刻,數字人文環境下,檔案傳播可利用虛擬現實技術創建和體驗虛擬世界,讓受眾體驗到身臨其境之感。如“威尼斯時光機”項目,這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減小了受眾之間由于不同知識儲備、信息獲取能力等帶來的差異,最大程度提升檔案信息的獲取效果。
4面向數字人文的檔案信息傳播服務思考
4.1創新檔案傳播理念,營造社會氛圍
數字人文已是人文學科發展的趨勢,它正不斷突破學科間的邊界,融合多方力量來壯大自身,檔案領域也應抓住機遇,創新檔案傳播方式。理念是實踐的先導,只有在思想上認識到它的重要性,才能推動實踐的進步。檔案領域應在理解數字人文內涵的基礎上,將其與檔案學相融合,同時可借鑒國外已有的實踐經驗,多渠道宣傳數字人文理念,認識到檔案領域運用數字人文技術的重要性。檔案主管部門應認識到數字人文的發展趨勢,在政策、經費上給予一定的扶持;檔案管理人員應積極學習新技能;檔案研究者要順應時代的發展,在數字人文環境下開展檔案信息傳播服務研究,以理論助力實踐,從而形成“局館研”三位一體的戰略布局,營造良好的檔案信息傳播氛圍。
4.2融合新型傳播技術,引領服務升級
新技術的融入需要人文學者在數字化環境中尋找新的信息傳播方式,促進傳統傳播方式的轉變。“新媒介的多元性和可拓展性在設計、計算、分析、可視化等方式上重塑人文知識,為研究者提供差異化、規律化、趨勢化的研究線索,拓展了學術研究潛力,也更符合人文學術的本質特征”[20],借助新媒介技術,可以實現傳播內容的不斷創新,發現新的研究視角,拓展檔案研究新領域,進一步滿足受眾對檔案信息傳播內容的全面性、時代性的需求,從內容和方式上打造人文知識傳播的新形式。
4.3探索新型合作模式,拓展傳播領域
數字人文從本質上而言是一種學術交流形式,在數字人文環境下,科學研究的核心將轉變為開放式探索,技術的發展促進了研究者之間的交流。傳統環境下檔案部門往往是自主探索,缺少領域內部和領域之間的交流,在內容開放上相對古板、封閉。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則為研究者提供了交流工具,拓展了研究網絡,使溝通交流更加快捷、透明,促進了開放的學術交流環境。圖博檔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融合,但他們更側重于資源本身的數字化融合,在服務融合上仍比較欠缺[21]。數字人文在現有合作基礎上,要加快資源的大眾化知識獲取與流動,打破學術封閉的局限,形成多學科、多領域、公眾參與的開放性學術文化機制。開放的合作機制帶來多樣化的信息交流內容,在檔案信息傳播上將融合多領域、多角度、多層次的內容,從而滿足受眾對信息的多方面需求。
4.4深化信息傳播層次,驅動服務優化
數字人文的重要特點在于對海量數據的分析,它提供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工具,人們能夠通過它來發現研究問題,在此基礎上幫助人們研究問題,找出問題的出路。以往檔案信息傳播的內容往往是檔案部門自行開發的產物,在傳播內容的設計上具有一定主觀性,檔案信息傳播的針對性和創新性往往比較欠缺,檔案部門可利用這些技術手段開發特色檔案信息,滿足用戶需求。在創新檔案傳播方式和內容的基礎上,可通過知識組織進行知識發現,通過數字化展示技術,實現跨學科、跨實踐、跨領域數據的使用,實現檔案信息服務升級。
當前我國數字人文的研究剛剛起步,跨學科的數字人文環境將給檔案信息傳播服務帶來新的機遇與挑戰,跨界需要確定的目標、理解事物本質的能力、審時度勢的理性、處理問題的智慧、超越過去的勇氣[22],檔案領域應在充分理解和認識數字人文的基礎上,從中獲取處理問題的方法和靈感,吸收先進思想與技術,深層次、寬域的開發檔案信息資源,傳承檔案文化,擴大檔案影響力,提升社會檔案意識。
參考文獻
[1]新華網.習近平十九大報告(全文)[EB/OL].[2018-12-07].http://news.sina.com. cn/o/2017-10-18/doc-ifymyyxw3516456.shtml.
[2][5][17]柯平,宮平.數字人文研究演化路徑與熱點領域分析[J].中國圖書館學報,2016(6):13-30.
[3][4]朱本軍,聶華.跨界與融合:全球視野下的數字人文——首屆北京大學“數字人文論壇”會議綜述[J].大學圖書館學報,2016(5):16-21.
[6]趙生輝.國外檔案領域數字人文項目的實踐與啟示[J].浙江檔案,2015(9):14-17.
[7]吳加琪.數字人文興起及檔案工作的參與機制[J].檔案與建設,2017(12):12-15.
[8]龍家慶,王玉玨,李子林.融合與建構:數字人文研究與檔案工作的關聯及路徑探索[J].檔案與建設,2018(12):4-7+12.
[9]張衛東,左娜,陸璐.數字時代的檔案資源整合:路徑與方法[J].檔案學通訊,2018(5):46-50.
[10]趙生輝.國外檔案領域數字人文項目的實踐與啟示[J].浙江檔案,2015(09):14-17.
[11][13][15]杭孝平.傳播學概論[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4,410,189.
[12]張慶莉,滿春玲.我國檔案信息傳播的發展過程及內容體系初探[J].檔案學通訊,2017(5):57-61.
[14]王馨藝,徐擁軍.多學科視角下的檔案學理論研究進展(之五)——傳播學視角[J].山西檔案,2017(2):12-18.
[16]朱本軍,聶華.互動與共生:數字人文與史學研究——第二節“北京大學數字人文論壇”綜述[J].大學圖書館學報,2017(4):18-22.
[18][19]劉儉云,祁媛,王昆.傳播學導讀[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344.
[20][22]馮惠玲.數字人文:在跨界中實現交融[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12-21(8).
[21]朱學芳.圖博檔信息資源數字化建設及服務融合探討[J].情報資料工作,2011(5):5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