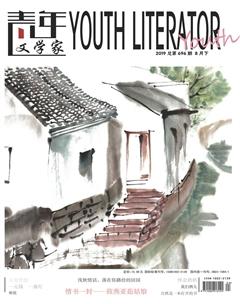廣場舞背后的故事
史軍
李女士作為一名資深廣場舞愛好者,在此5年之前剛害了一場大病,子女出于她身心健康的考慮,決定讓她辭了工作,專心在家休養。剛剛50歲出頭的李女士總閑不住,要往家外跑,為此家里沒少鬧矛盾,“那時廣場舞正在興起,老鄰居便向她推薦去跳廣場舞”,李女士回憶講。
起初,李女士覺得老太太跳舞恐怕不太好看,要鬧笑話,幾次都拒絕了老鄰居的邀請,不過抵不住家里閑,還是隨著老鄰居去看了幾次。
“第一次去看,都是些老頭老太太,有的年齡比我大,有的年齡比我小,我看他們跳得很自然,沒什么尷尬的,隔壁老頭又總拽我去,我就稀里糊涂跟著進去了。”李女士回憶講。
第一次跳廣場舞并不順利,李女士講:“剛開跳的時候啥也不會,只是傻站著跟著一旁的人學,不過倒也沒人在意,可能是每天都有新人吧?我記得第一次跳的時候還不小心把別人腳踩了。”
“其實第一次就圖個熱鬧,家里無聊,廣場人多些,其他倒沒什么特別的感受的。”李女士很鄭重地講。
“后來隔壁老頭隔三岔五來叫我,家里又閑,就跟著去了。”李女士講道:“剛開始跟著隔壁老頭跳,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拍子也簡單,慢慢就習慣了。”
李女士自述剛開始跳廣場舞的時候,除了學拍子之外,每天出門還得特別精心打扮,她說:“到了她這個年紀,說打扮也比上年輕人,說不在意,廣場舞也是個拋頭露面的地方,太隨意了也不適合,不過后來慢慢和周圍的人熟悉了,也就沒有那么講究了,有時候穿雙拖鞋就出門了。”
跳廣場舞的人群里,有八十歲還在染發的老阿姨,也有穿著背心出門的老太太,如果當天沒有什么活動之類的,一般穿得都很隨意。
在李女士開始跳廣場舞不久,子女還擔心她的身體狀況不好,可能會影響康復,后來李女士入院復查,醫生說她子宮摘除術后恢復良好,比一般患者恢復更快,子女們也就放心了。
“我記得我爸、我媽那一輩,沒有事情干就去茶館喝茶,我就想廣場舞能不能也成為我的娛樂活動呢,跳廣場舞還不像喝茶一樣花錢。”李女士回憶講。
也是這種觀念驅使下,李女士跳廣場舞的次數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與越來越多廣場舞愛好者熟絡起來。
雖然后來老鄰居搬走了,李女士還是經常去跳廣場舞,和小區其他人越來越熟悉了,除了晚上廣場舞,也經常一起去參加別的中老年人活動,為此兒女還調侃說李女士除了晚上,白天都看不著人影。
“那次她晚上8點才回來,結果還帶著個老頭兒,把我們嚇了一跳。”李女士兒子講。
李女士在十年前由于一場車禍喪生,十年來她除了工作和照顧子女外,基本沒有時間再尋找伴侶,跳廣場舞認識的王先生55歲,也就成了現在她的丈夫。
王先生和李女士同在一個小區,基本上跳廣場舞的時候都能遇到,認識半年時間,逐漸熟悉了,也就經常一起結伴去跳廣場舞。王先生也是中年喪偶,現在唯一的女兒也已經嫁人了,家中只剩他一人。王先生平日里喜歡下棋,不過棋友較少,因而很多時候也都在家閑居,偶爾公園散步結識了李女士,也逐漸加入了廣場舞的隊伍。
李女士講:“剛開始他比我還笨,膽子還小,束手束腳,經常踩著我。”
后來兩人在廣場舞過程中逐漸熟悉,了解了彼此家庭情況,逐步融入各自的家庭生活后,也就組成了新家庭。
李女士說:“人有空閑總要找點事情干,廣場舞總比打麻將要好些,每天去跳一跳,出點汗,自己高興了,對身體也好。”
現在李女士和王先生每晚定時六點半出門,去廣場準備跳廣場舞,樓下的鄰居說:“每天我都不用看手表,只要聽到樓上開門就知道六點半了,他們總這個時候去跳廣場舞。”
最近一次復查醫生認為李女士術后恢復得很好,得知李女士經常參加廣場舞后,表示廣場舞對李女士影響是從身心兩方面的,尤其是心理方面,廣場舞作為一種娛樂活動很好調節了像李女士這類切除子宮病患后的女性易出現的抑郁、焦慮情緒。
李女士自己認為廣場舞說神奇也不神奇,不過是一群人聚攏在一起做一件事情而已,不過在做這件事情的過程中,取悅了自己,讓生活多了一點情趣。
李女士的故事僅僅是中國廣場舞故事的冰山一角,它是社會群體的一種生活符號,通過群體共同舞蹈的形式體現出我國中年老年群體積極、樂觀的精神面貌。廣場舞的集體性是廣大社會群體在生活中尋求團體支持的表現,每個不同的個體在同一種音樂與舞蹈找到共識和統一,通過統一的舞蹈形式進行表現,而廣場舞的自娛性是也民眾在生活中自我調節、自我認同的表現。廣場舞的自由性、自發性,更受廣大群眾的喜好,而在廣場舞這一活動過程中,不同個體的精神訴求、人際關系訴求得到滿足,身心得到愉悅,為其生活富裕了藝術感。通過廣場舞可以看到社會秩序的縮影,可以看到一種集體訴求在一種表現形式下獲得滿足。不過由于廣場舞集體性,在廣場舞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如組織問題、擾民問題,廣場舞的故事說之不盡,好的故事、壞的故事,動聽的故事、丑惡的故事,作為我國特有的文化,應揚長避短,取其精髓去其糟粕,民眾在豐富日常生活,鍛煉、愉悅身心同時,顧及廣場舞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減少廣場舞對周邊居民的影響,防止被貼上“嘈雜”、“人多不講理”等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