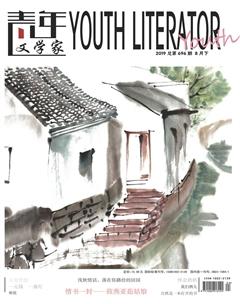“肉身”的符號化
許童星
摘? 要:孫頻的小說集《鹽》,以六個中篇講述出小人物認真、堅強地活著的故事,在極具個性化的女性書寫里體現出一種對“肉身”的符號化。本文剖析“肉身”中恥和魅的所指意義后,探尋作者在去符號化中對小人物生存困境的執著追問。
關鍵詞:肉身;符號化;祛魅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4-0-02
“80”后作家孫頻,以其細膩的手筆和對底層人物的深切關注,從同時代“青春疼痛系”作家中脫穎而出,得到蘇童、韓少功、閻連科和莫言等同時代嚴肅文學作家的一致認可。中篇小說集《鹽》講述小人物“在破碎中重生,再卑微中堅持”的6個故事,以“鹽”為喻,揭露世間中渺小卻最卑微、最真實、最有韌性的人之存在意義。因其對人生、命運的關注,對精神救贖之路的探索,使創作免陷于私小說的絮絮自語,作品的主題和哲理性得到質的提升。在孫頻筆下,“肉身”被賦予特殊的意義,本文將以索緒爾的“能指”和“所指”為理論基礎,從符號學角度解讀《鹽》中的“肉身”。
一、《鹽》中的“肉身”
在這部小說集中“肉身”頻繁往復地出現,它不等同于身體,而作為一個能指符號被賦予更多意義,使文本里呈現出一種形而上的闡釋內涵。《無相》講述女大學生從小看母親以“拉偏套”的陋俗出賣身體而養活一家人,走出大山后又因對老教授資助的虧欠感而忍受其提出的觀看、撫摸裸體的要求。《我看過草葉葳蕤》中的李天星是一個時代轉變過程中的零余人,被現實踐踏和捉弄而沉淪,最終女人肉身在他眼里均變成一種草葉腐敗之味。《東山宴》中失去母親的阿德對于女性的乳房有異化的依戀。《乩身》中殘缺的男女主人公相互取暖,在人前自殘而自我神化,最后通過毀滅肉身逃出“生的地獄”。《因父之名》里被父親拋棄的女兒,不斷為父親重塑肉身,最后將侵犯自己的男人認做干爹逼死生父。《祛魅》里女主人公對男人的遐想和期望逐次破滅后,開始依戀無生命的東西,為肉身祛魅后毀滅。
二、“肉身”的符號化
符號化是感知被解釋出意義的過程。符號過程以意義不在場為前提,符號之在場反而說明意義之闕如,符號始終是一個“待在”。在《鹽》的各中篇里,肉身不再是單純的“肉體,人的體內紅色、柔軟的組織”之意,被賦予的所指意義主要為帶有負罪感的恥和不斷移情的魅。
(一)恥、負罪
《我看過草葉葳蕤》中寫到“肉身只是一種隨時會腐爛的植物,一春,一秋,一夏,一枯,一榮,每個瞬間都會腐爛……血液棲息于血液,骨頭棲息于骨頭,身體棲息于身體,這個世界是多么荒謬,又是多么堅固。”所有女人對于李天星來說均成為一種符號,充滿肉質的潮濕和類似于菌類的腐敗氣味。這一中篇里,孫頻將大歷史與個人的小歷史相融合,通過李天星的流離處境和男女關系變化,賦予肉身一種寄托。這種寄托隨著李天星的沉淪漸漸化為恥和負罪感,蘊含植物轉瞬即逝的死去和腐爛的意義,滿篇充滿荒謬的存在主義意味。
在《無相》中女大學生于國琴走出大山,受過教育后反觀兒時村里時興的“拉偏套”,對肉身產生一種厭惡和恥辱感。在她眼里肉身化作符號,是關于“肉體”的解釋意義之缺失,同時又是“恥”的所指意義之存在。在于國琴眼中“肉身”是自小而生的“疼”的來源,所以盡管理解老教授的孤獨和對年輕身體的渴望,仍舊在他心臟病發時放棄救援。正如作者孫頻所言,“因為她覺得他無恥,正如他自己一樣,同樣的無恥”。
《乩身》里對女性的書寫蒼涼而悲壯。先天性失明而被丟棄的常英,讓別人相信她是個男人才可活命,被收養后改男性化名字常勇,自此“女性成了她的一種疾病,一種恥辱,一種遙遠而模糊的幻影”。這種恥在女主角身上極具張力,與常勇作為女性的自我認知不斷沖突直至異化,“只有被男人強奸了才能證明她終究是女人”。
(二)魅、移情
《因父之名》中田小會的父親離家出走后便每日給父親寫信,重塑父親的肉身,“她在這些信里在這些文字背后為自己創造出一個誠信的父親……一塊石頭可以是他的肉身,一棵樹可以是他的肉身,一堵墻也可以是他的肉身,他成了全世界最自由的肉身……就像她已經忘記他真實的肉身究竟該是什么樣子。”她塑造出父親的肉身是一種魅,蘊含的是她對父親的崇拜,對父愛的渴望,對救贖的急需,為肉身賦魅使她甘愿成為肉身的祭品。傷痕累累的她抓住大海中一片浮木,將父親的肉身寄于一個陌生殘疾男人,認為干爹后犧牲自己滿足這個男人的欲望。
《東山宴》里五歲的阿德是個母喪父嫌的傻子,母愛的缺失而對女人的乳房異常迷戀。作者將其本身意義放大到遠超出原載體的價值上,女性乳房的魅所蘊含意義是源自人性最基本對母愛的需要,賦予阿德的行為一種本真純美感。肉體的所指既是母親,更是安全感,它們將母子關系復制于白氏與阿德、采采與阿德。
《乩身》中一個被閹割了的男人和一個被閹割了的女人因肉身殘缺而惺惺相惜,彼此需要。“他們各自的殘缺才能天衣無縫地融合起來,他們兩個合在一起,才能變成一個人”。肉身的完整對于他們而言是一種魅,通過在人前自殘和用一根鋼釬把兩人腮幫子刺穿相連的賦神表演,完成對肉身完整性的終極賦魅。
三、去符號化——無相、祛魅
《無相》中老教授說:“宇宙間最本質、最圓滿的生命,其實是無相可言的,眼中看不到色相,才是真正的光明,所以我們要敬重那些拉偏套的女人,敬重你的母親。所有的妓女和妖女其實都是佛的化身”,“我正在走向衰老和死亡,可是你讓我想起所有美麗青春的東西,想起我的母親、愛人。這個時候我會覺得我們跨越一切,離得那么近。這一眼就夠我回憶幾年”。老教授對肉身的執著與大學生于國琴以肉身為恥是兩相對立的,他提出觀看和撫摸于國琴裸體的要求被去符號化。將于國琴眼中蘊含“恥”的肉身去符號化,呈現出一種“無相”,給予老教授一種自在、自為的力量來沉著面對衰老和死亡。
《祛魅》中描寫山村女教師李燕林年輕時候與旅美作家發生一夜情后其肉體賦魅,沉淪于對虛假男人的幻想耽誤八年青春。“最后她想清楚了……她高看了他,她心甘情愿仰著臉看他,把他當做寺廟里的一尊佛像似的供起來仰著看”,“再見到任何一個男人的時候,她幾乎是不由自主的、下意識地,先要把他祛魅——把他肉體上一切虛假的磁場全部消除掉”。她與男學生的師生戀,同樣建立在懵懂的男學生對李燕林肉體的賦魅,最后磨滅于賦魅。
結語:
在《鹽》中始終體現出一種近乎殘忍的觀察力,描寫極致的愛與痛,“肉身”的符號性書寫貫穿于中,這與其經歷和創作理念息息相關。作為女性作家,她對女性的關注使文中的肉體多為女性肉體,抑或女主塑造的肉體,作品中的女性用一種近乎偏執、自虐的方式擺脫性別原罪意識。原罪來自基督教義,指人與生俱來罪行。“以男性為主體的男性本體論,已內化為一種女性日常的倫理觀念、生活習慣與價值取向,溶解在女性習以為常的言行與心靈中,成為一種自覺依附男性的原罪意識。”[1]這種性別原罪意識便是“肉身”的所指意義負罪感的恥和不斷移情的魅的根源所在。正如孫頻所說“在卑微中堅持,在破碎中重生”,我們可以從這六個故事中看到小人物惺惺相惜的生之努力,呈現出最極致的隱痛和尊嚴。
注釋:
[1]楊若蕙. 性別原罪與異化困境中的自我救贖——孫頻小說女性人物論[J]. 名作欣賞,2018(29):94-96+171.
參考文獻:
[1]徐剛. 蒼涼而卑微的女性敘事——孫頻小說論[J]. 百家評論,2013(02):90-94.
[2]管季. 被施虐的愛與尊嚴——評孫頻中篇小說集《鹽》[J]. 百家評論,2017(06):98-102.
[3]唐詩人. 極致敘事與憐憫之心——孫頻小說論[J]. 文藝評論,2017(12):42-50.
[4]馬明高. 情欲:孤獨、失敗和時間的幻象——讀孫頻中篇小說《我看過草葉葳蕤》[J]. 百家評論,2016(05):116-123.
[5]舒晉瑜. 孫頻:我的小說并不是一種嚴格的寫實主義[N]. 中華讀書報,2018-06-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