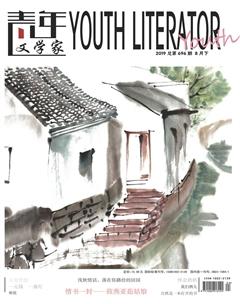非虛構(gòu)文學與報告文學的真實性之辯
佟與格
摘? 要:報告文學自新文學誕生起就以其即時性和真實性的特征屹立于文學之林,并在一定時期起到了政治宣傳的作用。近年來以《人民文學》開非虛構(gòu)文學專欄為起始,非虛構(gòu)文學這一外來概念成為了文學界不可忽視的一隅。本文將非虛構(gòu)文學與傳統(tǒng)報告文學進行比較并探討二者的真實性特征。
關(guān)鍵詞:非虛構(gòu)文學;報告文學;真實性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4-0-01
就真實性而言,非虛構(gòu)文學與報告文學都繼承了文學的真實性精神,但是與傳統(tǒng)文學相比,二者之真實具有鮮明的紀實性特點。如果說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任務(wù)在于創(chuàng)造,那么非虛構(gòu)文學與報告文學則是記錄和刻畫,把現(xiàn)實原有的樣子通過作者的視角和藝術(shù)技巧展示給讀者。“非虛構(gòu)”(Nonfiction)文學與報告文學(reportage)二者均可以視為紀實文學之范疇。但是由于二者產(chǎn)生的話語語境與藝術(shù)表現(xiàn)方式有所不同,二者的關(guān)系既繼承創(chuàng)新又相交相離,加上近年來非虛構(gòu)文學占據(jù)了一定優(yōu)勢,使得二者的理論范疇研究需要進一步的解決。本文將通過三部分來進行二者有關(guān)真實性的論述。一是生活與宣傳的真實性之辯,這是從二者產(chǎn)生的社會歷史背景角度來談的;二是個體視角與群體視角的真實性之辯,這是從作者立場和思想的角度來論述的;三是生存困境演化的真實性之辯,這是從二者描述的人物生存發(fā)展需求的不同來闡釋的。
一、生活與宣傳的真實性之辯
非虛構(gòu)文學在中國大陸初露端倪是在新世紀的初期,伴隨著報刊媒體的宣傳和譯介書籍的出版,人們對于非虛構(gòu)文學這種回歸生活真實性的文體類型產(chǎn)生了極大的興趣。“關(guān)于非虛構(gòu)的特質(zhì),寫作者和研究者都認可它是崇尚真實、呈現(xiàn)事實、尋求真相,但在‘真實觀上出現(xiàn)較大爭議。非虛構(gòu)寫作的真實觀,顯然不是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的‘來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的真實觀,而是力求無限接近社會現(xiàn)實本身。”[1]在經(jīng)濟社會的背景下,社會總體態(tài)勢穩(wěn)步發(fā)展,激烈的矛盾沖突已經(jīng)較難見到,可是生活中的個體和群體困境依然繁多。非虛構(gòu)文學便是將目光投入進社會生活之中,還原生活本來的面容。很多優(yōu)秀的非虛構(gòu)文學作品給讀者帶來對于生活新的認知,如慕容雪村《中國,少了一味藥》、梁鴻《中國在梁莊》、賈平凹《定西筆記》和李娟《冬牧場》等等。雖然非虛構(gòu)文學的“真實”性存在諸多爭議,但是我們應(yīng)該看到非虛構(gòu)文學面向生活的人文關(guān)懷精神。在今天網(wǎng)絡(luò)小說等虛構(gòu)文學逐漸膨脹也逐漸模式化的情況下,非虛構(gòu)文學給了讀者更多的現(xiàn)實感和更加真實的閱讀體驗。它積極地向人們描繪出生活的不同側(cè)面,拓展了讀者對于生活的理解力和感受力。此外我們應(yīng)當思考,非虛構(gòu)文學在今天的興起是否與報告文學的文學基礎(chǔ)有關(guān)呢?
就歷時的角度而言,報告文學傳入中國的時間更早,在中國新文學肇始的新文化運動時期,報告文學作為一種即時性、新聞性、政論性和宣傳性于一身的文學形式受到讀者的歡迎。傳統(tǒng)中國文學中起到紀實性作用的主要是散文一類,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魯迅的雜文以短小精悍的匕首投槍姿態(tài)出現(xiàn)在中國近代文學的舞臺上。但是和雜文相比,報告文學具有更強的可讀性,與雜文的片段性相比報告文學具有更加完整的線性行文結(jié)構(gòu),并且報告文學也被廣泛地作為新聞稿件來使用。近代報告文學多展示社會大背景相下的群體事件,以體現(xiàn)時代特征和宏大歷史視角,具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和宣傳鼓動作用。這是在國破家亡的危機下時代對文學提出的要求,不僅僅是報告文學,幾乎全部的文學形式都是以宣傳救亡圖存思想為己任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涌現(xiàn)出大量優(yōu)秀的報告文學作品,如夏衍《包身工》、蕭乾《流民圖》和宋之的《1936年春在太原》等等。抗戰(zhàn)時期涌現(xiàn)出來許多反映抗日戰(zhàn)爭的報告文學,新中國成立后很多表現(xiàn)新中國建設(shè)的報告文學大量發(fā)表。可見報告文學是與時代風云的跌宕同呼吸的,它的題材與社會歷史大環(huán)境不可分割,具有宏大的敘事特征。但是我們也應(yīng)該看到它的局限,那就是政治功利性較強、宣傳氣息較濃和時效性較明顯,也就是說報告文學的優(yōu)勢在一定條件下成為了它的弊端。“盡管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仍可以毫不謙虛地說,非虛構(gòu)寫作對于被報告文學所弄丟的文學真實性,對于被虛構(gòu)文學所弄丟的現(xiàn)實感,是一種拯救。”[2]
二、個體視角與群體視角的真實性之辯
就作者的書寫視角的不同,其真實性給讀者帶來的感受也大不相同。非虛構(gòu)文學的作者往往采用個人化眼光進行審視和判斷,而報告文學則立足于更加宏大的社會歷史角度審視描寫對象。非虛構(gòu)文學具有較強的個體體驗性,而這種個體性給非虛構(gòu)文學帶來更加真實的觸感,就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新寫實小說具有毛茸茸的真實感。但是畢竟非虛構(gòu)文學是以非虛構(gòu)立足,這一點與需要虛構(gòu)的新寫實小說依然不同。并且與新寫實小說冷漠敘述相比,非虛構(gòu)文學的人文關(guān)懷意識是搭建在現(xiàn)實生活與心靈之間的橋梁,如果沒有這一點,它將只是記錄流水賬的新聞稿件,而很難歸屬于文學領(lǐng)域。
非虛構(gòu)文學的體驗性與調(diào)查報告的調(diào)查性有相似也有相異。非虛構(gòu)文學的體驗性往往從個人角度出發(fā),強調(diào)親眼所見和真實感受,其動機也主要是個人化的。而調(diào)查報告的調(diào)查雖然也需要作者進行體驗,但是由于作者需要服從于某種更加宏觀的目的,其搜集真實的視野是需要經(jīng)過過濾的,或是為了迎合時代潮流或是為了宣傳某種思想意識,調(diào)查報告的作者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種群體意識,或者是被期望的群體意識。
由于寫作視角的不同,帶給讀者的整體觀感也往往不同。非虛構(gòu)文學的個人視角書寫帶給讀者更加真切的體驗感,作者的眼睛就好似讀者的眼睛,作者的疑問也是讀者的疑問。這種浸入式閱讀體驗與優(yōu)秀的小說相似,但是小說究竟是虛構(gòu)的,讀者對其情感來自于故事的跌宕起伏。但是非虛構(gòu)文學描繪的是真實事件再加上作者的藝術(shù)技巧就使其感染力更強帶給讀者的回味與深思更加豐富。“與傳統(tǒng)的報告文學相比,非虛構(gòu)寫作者的姿態(tài)也是大不相同的。后者往往是以個人化視角,用一種樸素、準確的筆墨來描寫生活,而不是像前者那樣,寫作者往往是一個巨大的、膨脹的形象,習慣于用夸張的筆墨來表現(xiàn)宏大乃至被極力拔高的文學形象和主題。”[3]
報告文學的寫作者則往往采取鳥瞰式的視角描述事件,這在真實性上就沒有非虛構(gòu)文學那樣帶給讀者更強的體驗感,或者也可以將之論為創(chuàng)作動機與讀者接受的失衡。并且基于報告文學長久以來的作用是宣傳,其行文模式相對固定化,其標題也具有類型化特征,以引起讀者對于所述事件或人物崇高感的蒸騰。崇高感是必須的,但是由于報告文學在一定時期被錯誤利用,其崇高感和“不及物”的脫離生活姿態(tài)會招致一些讀者心靈上的反感和抗拒。“報告文學精彩作品的稀少,正是因為報告文學與人民的現(xiàn)實關(guān)注點的偏離,是作家在紛紜的現(xiàn)實社會矛盾現(xiàn)象面前把握的盲目和無力。”[4]但是我們也應(yīng)當意識到如今市場經(jīng)濟的大背景下,消費主義、物質(zhì)主義給我們帶來的對于思想意識的消解和對于思考人生的淡漠,而將物質(zhì)作為自我價值確證的唯一標準,這是我們需要警惕的。而與報告文學相比非虛構(gòu)文學更加親民更加面向生活并且作者情感更加濃烈和真摯,視角也是從個體人的角度出發(fā),這有利于彌補報告文學宏大敘事方式的不足,讀者接受感更強。
雖然非虛構(gòu)文學的個人化視角下的真實性更有血有肉,但是作者對于事件的體驗和對人物的尋訪仍然難以避免帶有個人先驗觀念。那么作者對于事件的書寫是否帶有自我價值判斷的透析而將讀者引導進某種情境之中呢?并且如今互聯(lián)網(wǎng)十分發(fā)達,對于文學而言傳播速度更快、受眾范圍也更廣,這難以避免一些無良營銷號打著“非虛構(gòu)文學”的名頭行煽動大眾焦慮的事實,如咪蒙團隊的《一個出身寒門的狀元之死》。這篇文章錯漏百出,但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大數(shù)據(jù)的傳播下很多人來不及多思考便跟風轉(zhuǎn)載,而那些草草閱讀后發(fā)出對人生消極慨嘆的網(wǎng)友更是不勝枚舉。“作者所提供的‘真實故事足夠奇觀化,能夠贏得讀者,獲取利益;讀者在閱讀過程獲得獵奇體驗;而平臺從中收割了足夠多的流量。這似乎是一個無需計較真實與否的皆大歡喜的‘非虛構(gòu)文學生產(chǎn)、傳播、接受流程。”[5]可以說如今的大眾在消費著物質(zhì)而資本也在消費和愚弄著大眾。對于“非虛構(gòu)”文學的真實性檢驗需要更多讀者的關(guān)注和思考,同時也需要互聯(lián)網(wǎng)營銷者建立起道德良心并受到法制監(jiān)管,以幫助非虛構(gòu)文學免于向虛構(gòu)墮落從而得到更好的完善和發(fā)展。
三、生存困境演化的真實性之辯
報告文學興盛于近代中國的救亡圖存時期和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shè)時期。在第一部分生活與宣傳的真實性之辯中我們已經(jīng)談到了報告文學具有很強的社會歷史性和宣傳鼓動性,它主要表現(xiàn)的大環(huán)境下的大事件或者是大環(huán)境下具有代表性的個人。就生存困境而言,個人是與民族國家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二者是個別與一般的關(guān)系。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描寫了朝鮮戰(zhàn)場上的中國志愿軍戰(zhàn)士,這篇報告文學感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這篇文章將抗美援朝戰(zhàn)爭與志愿軍戰(zhàn)士結(jié)合起來描寫,既有群像描寫也有個像描寫,這些人物都有著強大的精神感染力,那就是赤誠的愛國主義。他們的生存和發(fā)展是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其個人生存困境主要來自于國家和民族的困境。
而在以經(jīng)濟建設(shè)為中心的今天,個體的生存和發(fā)展被人們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慕容雪村《中國,缺了一味藥》中被簡單的傳銷套路蒙蔽的人們追求金錢卻無努力,追求成功卻毫無遠見,這類群體是如今一部分好逸惡勞夢想發(fā)財者的縮影。極度的金錢追求使傳銷者被幼稚的騙術(shù)蒙蔽,急功近利的心理被傳銷者充分利用。非虛構(gòu)文學對于現(xiàn)實生活問題的關(guān)注與展現(xiàn)帶給讀者預(yù)防針一般的效果,它提示著人們對于自我貪婪和外界誘惑的警惕。
但是我們也應(yīng)當看到由于非虛構(gòu)文學注重挖掘社會問題和揭露陰暗面,為了寫作而挖掘為了陰暗面而挖掘的現(xiàn)象值得我們反思。我們需要承認,今日的中國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經(jīng)濟社會整體是健康發(fā)展的。對于發(fā)展中的困難和問題我們應(yīng)當重視并且解決,但是如果沉迷于此則有可能陷入晚晴黑幕小說的窠臼之中。“非虛構(gòu)作品經(jīng)常關(guān)注平民、底層和社會邊緣群體,非虛構(gòu)的文化職能是讓弱勢者變得可見。”[6]這是非虛構(gòu)文學值得肯定的方面,而對社會積極面的調(diào)查和宣傳,非虛構(gòu)文學應(yīng)與報告文學共同發(fā)力,走出各自的書寫舒適圈向更加廣闊和全面的社會各個維度邁進。甚至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非虛構(gòu)文學的成熟和報告文學的完善,二者存在著殊途同歸的可能,而對于二者概念和理論的研究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未來會取得更大的進展。
注釋:
[1]宋寧《非虛構(gòu)寫作的文學史維度與構(gòu)想》[J].《文藝評論》,2018年第5期。
[2]王磊光《非虛構(gòu):它拯救了多少現(xiàn)實感和真實性?》[N].《文學報》,2019年4月25日,第018版。
[3]王磊光《非虛構(gòu):它拯救了多少現(xiàn)實感和真實性?》[N].《文學報》,2019年4月25日,第018版。
[4]《把脈問診報告文學》[N].《人民日報》,2010年3月25日。
[5]信世杰《非虛構(gòu)與報告文學:互為毒藥還是良藥?》[N].《文學報》,2019年4月25日,第019版。
[6]張慧瑜《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非虛構(gòu)寫作》[J].《新聞與寫作》,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