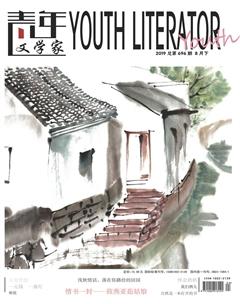論蕭紅作品灰色意味中的死亡態度
孫蘭若
摘? 要:蕭紅的作品中無論表現歡樂抑或痛苦,都不是涇渭分明的情感表達,是一種介于白色與黑色中間的灰色意味。蕭紅筆下在庸庸碌碌中度過一生的小人物一個個死去,無論其生命中泛起多大波瀾,都逃不過死亡氣息的侵染,這種灰色意味貫穿蕭紅的作品,是絕望與沉淪,也是對生命價值與意義的叩問。
關鍵詞:蕭紅;灰色意味;死亡態度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4-0-01
引言:
灰色由白色與黑色調和而成,不如黑白兩色清晰分明,是一種含混不清的色彩。作為魯迅口中“當代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蕭紅在新時期以來成為文人學者競相研究的對象,蕭紅的作品與經歷都被打上了悲慘的烙印——孤獨寂苦的童年、接連受挫的婚姻、漂泊無依的生活、貧困與病痛的折磨,這些都使蕭紅的生命染上令人無法忽視的灰色。強烈的灰色意味滲透在她的作品中,匯聚成死亡情結,彰顯其對死亡的態度。
一、底層螻蟻混沌的死亡
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于動物的生命與環境是直接同一的,動物在消極地適應環境,而人卻在主觀上擁有能動性,積極地尋求與環境的平衡。但蕭紅構造的人“糊糊涂涂地生殖,亂七八糟地死亡”,這一從出生即走向死亡的群體,與動物沒有了任何區別,沒有自我意識,也就失去了對死亡意義的體味,從而缺失正確積極的生的意識。
這種特點的死亡在《生死場》《王阿嫂的死》《啞老人》等作品中均有體現。《生死場》為蕭紅的成名作,在農戶家凡俗的日常生活中,處處都充斥著愚夫愚婦們的死亡場景。王婆服毒、五姑姑難產、小金枝夭折,這種任憑自然與社會擺布的放棄,是蕭紅筆下對生的決絕。“生、老、病、死,都沒有什么關系,生了就任其自然地生長;長大就長大,長不大也就算了。”這種對生死無知且默然的態度,反映出社會底層螻蟻寂寞悲涼的生活。面對生活的困苦、社會的重壓,他們渾渾噩噩地過日子,死亡或許是一種拯救,但他們也僅有在死亡來臨前本能的掙扎,掙扎一番沒有結果,也就隨波逐流了。
在蕭紅的作品里,我們看不出那些身處逆境的人飽受磨難,為了走出逆境而敢于與艱難困苦斗爭的反抗,只有壓迫和被壓迫。他們沒有自我意識的覺醒,僅作為動物的本能赤裸裸地活著,一代又一代重復著相同的悲劇。不等同于魯迅筆下的麻木不仁,蕭紅作品中的小人物連最后一點稀薄的自得其樂也消失了,金枝對愛情的一點點美妙憧憬到頭來得到的不過是成業野蠻的欲望,在墻角的灰堆上約會也無半點溫存。一個又一個生命的消逝也換不來村民們對施壓者的不滿和反抗,這種濃厚的灰色壓抑住人性,人的精神荒漠化,再無生機可言。
為死而生,生的潦草,生的同時,死亡如影隨形相伴。蕭紅對生的尊嚴盡力追求與召喚,透出的卻仍舊是死的寂寥與無奈。這種反差,激起人們的恐懼與反思:死的意義就是這般單薄無味嗎?
二、掙扎卻夭折的死亡
沉滯、落后的生活環境和茍且、麻木的人群共同構成的人文環境使反抗窒息而亡。在逼仄的生存空間中,“愛”無處扎根,“人”無處容身,掙扎與反抗如同隆冬嚴寒中鉆出地面的草芽,尚未舒展身軀便被風刀霜劍般嚴酷的生存環境毀滅。
《小城三月》讀起來淡淡的,開篇不覺得如何輕松,結尾也不感到如何悲痛。翠姨苦尋的絨繩鞋、三月里懵懂青澀的早春,仿佛淡化了死亡的灰色意味。但就在這種仿佛被淡化了情緒的敘述中,蕭紅把束縛女性生存的森嚴禮教、陳規陋習等精神牢籠套在翠姨身上,用愚昧的人群、冷酷的世態、委頓的人格、蒙昧的靈魂,以殺人不見血的手法摧殘了她的生命。作品灰色的基調無所遁形。
翠姨不是沒有抗爭的。母親與外祖母把她許配給了一個又矮又小的寡婦之子,翠姨“更愿意遠遠的推著”;當婆家再三催婚的時候,翠姨不斷地糟蹋自己,只盼望著趕快死。在臨死前,翠姨終于握住了自己心愛人的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直白大膽地袒露自己的情感,用死亡來成全自己的愛情。這種死亡本身就是一種抗爭,盡管生命無法擺脫悲劇的鎖鏈,但肉體的死亡換來了精神的解脫。
三、無畏卻無力的死亡
《呼蘭河傳》中那個“頭發又黑又長,臉長得黑乎乎的,笑呵呵的,兩個眼睛骨碌骨碌的轉”的小團圓媳婦,那個天真無畏的小孩子,被吊在大梁上用皮鞭子抽,被燒紅的烙鐵烙腳心,被鎖鏈子鎖起來等各種手段“教育”,最終還活活被燙死了!小團圓媳婦的婆婆親手斷送了如此富有活力的年輕生命,左鄰右舍卻稱贊道:“這是為她好!”王大姑娘的死也不足為道,甚至馮歪嘴子最好家破人亡。本來關于死亡的人人都應回避的話題,在這里卻變成了談資。這種無時無刻不存在的對死亡的漠視與麻木,才讓灰色更為濃重。
一個人對于孩提時代的回憶本不該充斥著如此多的死亡的,當蕭紅從兒童的視角道出死亡的平常,那種深灰色的悲涼便愈發不可化解。蕭紅一生最難以釋懷的便是對生與死的冷漠,最不能容忍對生命的褻瀆和扼殺。在《呼蘭河傳》中,蕭紅以孩子旁觀者的眼光直面死亡,恰恰就直白地寫出了她反感的丑惡。雖然作品中并沒有直接表達對死亡的看法,但蕭紅選擇在童年的回憶中加入大量灰色色彩,本身就是一種抗議與諷刺。
四、結語
“藝術的真正的誕生地是死亡,沒有死亡,就沒有藝術。沒有死亡,人類就會無所恐懼,無所悔恨,無所理想,也就用不著制造一個虛幻的藝術世界來彌補人生的遺憾,來滿足自己對永恒的追求和向往。”[1]這段話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作家在文學作品中描繪死亡的意義。蕭紅在無數筆關于死亡的描寫中,終是叩問了生命的存在和價值,繪出對生的深情眷戀,表達了對生命意義的渴望!
參考文獻:
[1]殷國明. 藝術家與死[M].? 廣州:花城出版社,19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