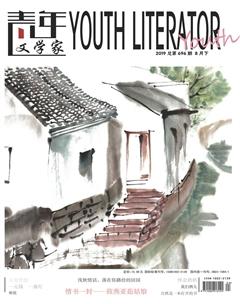淺析《莊子》中的“知”與“真知”
馬婷
摘? 要:《莊子》中從不同的生命狀態詮釋了“知”的不同層次,世俗之知由于成心而只能認識到事物的表象,極物之知不能徹底擺脫事物的局限性,只有達到“道”層面的“真知”,才能回歸到生命的本真狀態,天人合一,與道相通。
關鍵詞:《莊子》;知;真知
[中圖分類號]:B2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4-0-03
認識論是莊子哲學的核心,而“知”是《莊子》認識論中所探討的重要問題。那么知是什么?莊子在《庚桑楚》對“知”詮釋道:“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接”可看做是感性的知,出于與外物的相接,是認知的第一個階段,但只能認識到事物的外在形態;“謨”是理性的知,意即思維,出于心中的思慮,是認知的第二個階段,能深入認識到事物的客觀狀態。我們對世界的感受、認識和判斷正是在“知”的經驗基礎上形成,當感性的知接觸事物后,思維繼續進行思考。然而每個人的認知終究是有限的,在莊子看來,生活在世俗世界的我們,由于受到各種成心成見的“知”,導致了各種偏心偏見的爭辯,也導致了人失去了自我的本真狀態,因而無法達到對“道”的體認,唯有超越對“知”把握的局限性和相對性,才能獲得真知。。
莊子對真知的探求的原因,也是《莊子》一書的真正含義。春秋時期的中國,是一個充滿弊病與欲望的動蕩時期,諸侯爭霸、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生活的悲苦成為莊子最關心的現實問題。這一時期,諸子百家針對社會問題提出了諸多策略,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然而在莊子看來,他們的思想言論都是各執己端的偏見,都是站在自我立場來審視問題,不能針砭時弊,付諸實踐,挽救社會。故而莊子構建出自己的思想體系與理論,從知的層面出發,提出了真知。在《莊子》中,不同的知揭示了不同的生命狀態,在不同的地方對知做了不同的區分。
一、世俗成見的淺陋之“知”
“知”是我們對外部世界的一種感受和判斷,生活在世俗世界的我們,首先是通過事物的外在之形來感知事物,認識到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現象,而不能深入到事物本質,這樣一種知只能是世俗之知。《莊子》認為,知有不同的形態,最先形成的就是世俗之知,《莊子·胠篋》一篇中談及了世俗之知: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
世人為了對付撬箱子、掏口袋、開柜子的小偷而做防范準備,必定要收緊繩結、加固插閂和鎖鑰,然而這種所謂的聰明作法只不過是一種淺陋的世俗之知。“夫世俗之人,知謨淺近;顯跡之圣,于理未深”[1],因而,世俗之知其實是不可信的,它更多的是一種帶有成見的“知”,會影響對事物本質的感受與把握。并且,世俗的知還會致使自我堅守自我成見: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異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在宥》)
世俗之人喜歡別人和自己相同而厭惡別人和自己不同,這顯然是一種帶有自我成見之心的認知,只是停留在感性方面的知,也就是以“接”的方式來認知世界萬物,可以說是一種小知,是很低俗的認知。《逍遙游》中便有對大知與小知這兩種生存狀態的描述: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時則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在這里,蜩與學鳩用自己的淺近俗見來嘲笑志向高遠的大鵬,被莊子稱之為“小知”,蜩與學鳩的生存便是局限于“小知”的境遇當中,這種差異便是生存境遇的不同而產生的帶有世俗成見的知。面對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無休止的爭論,莊子感嘆到:“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斗。縵者、窖者、密者”,世俗之人都是從自己的主觀成見出發,以片面的眼光來看待世界,難免會有偏見不斷的爭斗,最終只會導致身體和心靈上的衰退,徒勞而無所得,并且這種世俗之見還會帶來很大的危害:
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倏與忽時相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應帝王》)
倏和忽只從自身的帝王身份出發,自以為是地想要改造混沌,而導致了混沌的死亡,在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莊子對于帝王無為而治的功效的否定,對世俗之人以己之主觀成見而行為處事感到深深的焦慮。
因而,世俗之人總想以自己的成見之知去把握世間萬物,卻因主觀看法的狹隘性而無法獲得真知。正如莊子所言:“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客觀上講,任何人都無法擺脫這種成心,“是己之所是,非己之所非也”,那么,這種彼此相非的一件是不是沒有解決辦法呢,針對這種情況,莊子提出“莫若以明”,“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用一顆明凈之心來看待世俗的偏見才能避免其狹隘性。
二、言意限制的極物之“知”
人們對物質世界的探索追求,很多時候語言和思慮所能達到的,只是很少的事物,這是知的另外一種形態,這種認知稱為極物之知[2],“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莊子·則陽》中論道: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里,萬物之所生惡起?”
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于是橋起。雌雄片合,于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天地之變化、陰陽之運轉、四季之循環,這些自然現象都是事物的現象,萬事按照其自身的規律而發展變化,而言語所能致意的,思慮所能達到的,只限于人們所熟悉的少數事物,這樣的認知便是以物觀之,較世俗之知雖并少了成見,但還是擺脫不了“物皆濁我之色彩”的局限。通過言意之辨,名實之辯獲得的對事物的認知也只是限于天地萬物的產生起源而已。而作為一個想要體悟大道的人,不會去追逐和探究事物的消亡與源起,因為物也是處在不斷的發展和變化中的。可以說,受言語限制的極物之知想要達到知天的層次,然而還是不免會帶有一定的局限性,莊子在《大宗師》中提出“知天”這一概念: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天”是自然,“人”是人為,“知天之所為”是知道天的自然本真狀態,“知人知所為”是知道人的本真狀態,如果能達到知天和知人,那么就可以接近真知的狀態了,而天和人往往是對立而區分的,并且“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即使達到極物之知也是有問題的:“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也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大宗師》)知在很多時候要有相對變化的,而人自身和物也是不斷變化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我們對于知與不知、我與非我的界限也很難把握清楚,而言往往是不能正確地或者完整地表達出事物本來的意思或是體現出事物的本質,如:
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鰍然乎哉?木處則惴栗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蟣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猶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鰍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對正處、正色、正味的質疑,便是處于以物觀之的狀態,言語和思慮所能達到的最高層次限于很少的事物,而大多的事物是言意之辨所不能正確認識和區分的,也有相對的局限性。因而,受言意限制的極物之知依舊不能擺脫相對狹隘的界限。于是,莊子讓真人出場了,只有真人才能獲得真知,才能達到“道”層面的知。
三、真人之“真知”
當世俗之“知”和極物之“知”都不能達到獲得真知,莊子提出“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要想有“真知”,必須首先成為“真人”,而真知就是“道”,莊子所說的“真人”是與道合一的,也即是要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真人是為解決真知而產生的,可以看出莊子的主要用意在于:讓真人全面性的代表道,真人的一切所知,就是道的一切所知。他不僅要知天,還要知人,還要擔當知天與知人的真理即真知的評判官。
何謂真人?莊子在《大宗師》篇刻畫了真人的形象:
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如此。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颒。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在這里,莊子具體論述了真人的五個認識標準:一是“知之能登假于道”,其知識與智慧要達到與道相通的境界;二是要超越生死的境界,“不知悅生,不知惡死”,能自然地享配生死。同時,“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極是萬物變化的規律,無論自然怎樣變化,真人都能與之相協和適應;三是要做到自適其適,任性自然,世俗之人往往為了使別人安適而驅使自己不適,而真人自我適宜,不受他人安適與否的影響;四是要懂得萬物齊一,這也是莊子之道的最高信仰,萬事萬物都是處于彼此相互對立的狀態中,若以道觀之,則萬事萬物是沒有差別的,真人是要能走向“齊一”的道,因而這種真知是一種超越了感性與理性的存在。因而,真人的真知成為莊子思想認識中的最高形態。但是,在莊子看來,并非所有人都能學到,《大宗師》中有: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無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無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徹;朝徹而后能見獨;見獨而后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這說明得道是需要一個過程的,首先是要能“外天下”,即遺忘天下,天下本來就離我們很遠,其次是“外物”,不要去追逐物質上的滿足,接著是“外生”,忘卻生死所帶來的煩愁。通過“外天下、外物、外生”,讓自我脫離現實世界,這樣的心靈,而后才能進入“朝徹”、“見獨”、“無古今”和“入于不死不生”,讓自己心明澄澈,得道,不受時空的限制,無生死之意識,實現無往不在的自由,達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這一過程中,想要獲得真知,還要有“坐忘”,即“ 墮肢體, 黜聰明,離形去知, 同于大通,此謂坐忘”《大宗師》,忘卻自我與現實的牽系,進入“道”的世界。同時,還要“心齋”,“汝齋戒,疏瀹而心, 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 《知北游》),凈化心靈,摒棄一切成見達到虛而靜的狀態,唯有虛靜,才能回歸自我本真狀態,與道相通,才能獲得真知。
四、總結
《莊子》中不同生命形態、不同認知領域的知有不同層次和境界,世俗之知更多的是一種帶有自我成見的偏見,受言意限制的極物之知也只是以物觀照的對萬物起源的一般認知,只有達到“道”層面上的真知,才能實現天人合一的境界。可以看出,莊子對帶有世俗偏見的認知和以物觀照的認知是持否定和批評態度的。從現實層面來看,莊子的認知論能超越知識的有限性與局限性,避免陷入爭論的泥潭。與此同時,這種認知又是矛盾復雜的,莊子主張要“去宥”,破除成心,齊是非,齊萬物,而他對知的前兩個層次的批判卻打破了自己的一個評判標準,這也體現了莊子思想的矛盾與復雜,以及他在現世的焦慮和無奈。于是,在獲得真知后的歸宿只能是“安命”,人們對“道”的探索與追尋正是想沖破“命”的限制,在獲得真知后卻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流露出莊子靈魂深處的孤獨、寂寞與無奈。
注釋:
[1]郭象注,成玄英疏.莊子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88頁.
[2]楊國榮,莊子的思想世界[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77頁.
參考文獻:
[1]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陳鼓應.莊子注譯及評介[M].北京:中華書局,1984.
[3]楊國榮.莊子的思想世界[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4]嚴春友.莊子思想的獨特性及其內在矛盾[J].河北學刊,2006,3(26).
[5]陶悅.從“齊物”與“物物”的矛盾化解看莊子哲學的主體性思想[J].哲學研究,2015(12).
[6]常超.莊子哲學中“知”的問題研究[J].安陽工學院學報,2011,(03).
[7]楊鋒剛.論莊子哲學中的“知”[J].中國哲學史,2013(3).
[8]張祥明.寬容:莊子的認識論精神[J].齊魯學刊,199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