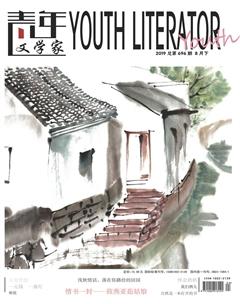現代性批判視野下的《美麗新世界》
孫艾琳
摘? 要:阿道司·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呈現了一個技術統治的未來世界,發達的物質文明似乎消解了社會矛盾,但冰冷的人際與機械化的生活卻唱出極權的悲歌。因而,如何突破“單向度”,警惕技術異化并重構個體自由,成為“現代性”值得反思的一面。
關鍵詞:《美麗新世界》;現代性批判;單向度;主體重構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4--02
以控制自然,消除匱乏為宗旨的科學技術,在《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如同塞壬之歌,營造著人人幸福的幻象實則暗流涌動。失去獨立思考的“單向度的人”,體現了作者對技術異化的擔憂。西方馬克思主義直面現代性的負面效應,啟迪我們審視物質至上和信仰失落的現實,重塑人應對科技文明的方式,重現人的天賦以及對世界的關懷。
一、現代性的表現及其困境
發端于啟蒙運動的現代性運動,以科學變革的腳步開辟了現代文明之路,但現代性的世俗王國對科技征服力的推崇引發了思想和情感危機。“單向度”(one-dimensional)理論源于法蘭克福學派的“新左派哲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他在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念中認識到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對人自我意識的奴役。
馬爾庫塞認為,一個全面發展的社會應該具有兩個向度,一是肯定社會現實且與現實社會保持一致的向度,二是否定、批判、超越現實的向度。但是在新型的科技話語與極權主義結合的社會中,人們失去了批判的聲音,從而淪為“單向度的人”。在發達技術世界中,技術理性通過確立富足與自由的生活目標維持著新的異化:“在抑制性總體的統治下,自由可以成為一種強有力的統治工具。決定人類自由的程度的因素不是可供個人選擇的范圍,而是個人能夠選擇的是什么和實際選擇的是什么……在大量的商品和服務之間進行自主選擇并不意味著自由,而只能證明這些控制的有效性。”[1]如果說“以技術進步作為手段,人附屬于機器這種意義上的不自由,在多種自由的舒適生活中得到了鞏固和加強”,[2]那么人在技術理性下依然是發達工業文明的奴隸,人淪為工具被物化。
馬爾庫塞認為,技術統治有其合理性的外觀,通過滿足人的物質需求,或通過大眾文化為人提供越來越多的消遣,來消解人的主體性和反抗精神。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在《棱鏡》( Prisms)中提到,“整個文化都只是依靠已在生產領域犯了罪的不公正力量來維持它的存在,就如商品的所作所為一樣”。[3]逐利性和拜物教化為主導的單向度的社會,也給人設置了一種虛假幸福感的氛圍。
正是人應對技術的方式給予了技術統治的話語權,致使人自身的內心“向度”失守,陷入物欲奴役和理智消解的生存困境。這也看出,現代性批判不反對技術的發展有多先進,而是關注未來社會將以何方式運用這些技術,以及技術未來的社會架構對個人生存和精神狀況的影響。
二、《美麗新世界》的現代性憂慮
《美麗新世界》是英國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筆下知名度較高的反烏托邦小說,這里的烏托邦已不再像人類理想的藍圖,而是傳達了作者對未來人類共同體的悲觀預測。
書名典出莎士比亞的戲劇《暴風雨》,在孤島長大的女主角米蘭達首次看到衣冠華麗卻內心邪惡的人們時,脫口贊嘆:“人類有多么美!啊,美麗的新世界,有這樣的人在里面!”這對于新世界而言不啻于一種反諷:實現了普世福利和全民幸福的世界國,未必是美麗的。高科技使得階級固化從胚胎業已形成,高消費使得人們與自然割裂,欲望被光明正大地放大,經濟思維自動生成。科技極權和消費主義形同魅影,充斥新世界的每個角落。
首先,世界國脫離了與保留區的原始關聯,取締了人在時空上的歸屬感。這也是吉萊斯皮(Michael Allen Gillespie)在《現代性的神學起源里》(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對現代性割裂的時間觀的批判,即現代性并非全新的,人的能力也不是一直優越的;其次是世界國的格言“社會,身份,穩定”,實則掩飾了寡頭政治本質,即使是頂層階級阿爾法也被設置為先天不足,在社會運轉中充當白領奴隸;再次,世界國對藝術創作如臨大敵。教師亥姆霍茲因追求自我表達而獲罪流放,正如柏拉圖將詩人逐出“理想國”的規劃。總統穆斯塔法·蒙德與野蠻人約翰的辯論讓人有所體會:“把強調真與美轉軌為強調舒適和幸福。”[4]
當大家都順從于毫無個人空間的生活程式,覺醒了自我意識的人就會格格不入,甚至被官方代表的“單向度社會”流放保留區以示懲罰。最有代表性的約翰,與控制中心的主任湯馬金有著血緣關系卻不被承認,胎生與家庭觀念在新世界里被厭棄。他與蒙德爭論時說道:“可是我不要舒適。我要神,我要詩,我要真實的危險,我要自由,我要至善,我要罪愆……我就是要求不開心的權利。”[5]這是他對權力規訓的反抗,也是莎士比亞所代表的人文精神賦予他對抗荒誕現實的支柱。雖然約翰最終不堪煩擾“在有生之年就已經死了,但卻是真正的獲救者”。[6]他以個體掙扎對抗群體脅迫,以本真對抗欲望,以殉道的方式邁入人類尋求理智和自主的希望,這“死亡是對烏托邦最強烈的反擊”。[7]而這希望可藉由伯納德和亥姆霍茲延伸,在保留區發現“向前的夢”,[8]重現真實生活的生機,變成雙向度的人。如同布洛赫(Ernest Bloch)的“希望哲學”,把希望作為一種積極的活動,而人們需要以樂觀與實踐來對抗虛無主義。
通過基因改造來預設命運,通過藥物控制、精英統治的實驗來企圖消解矛盾,通過創造中性人來進行反自然的嘗試,通過隔離和流放降低社會容錯率……這個充斥著機械化的無趣生活和冰冷的人際關系的社會,這個擴散欲望和群體沖動的社會,反轉了我們對未來文明的期待,取而代之的是對現代性的痛點的反思。而所謂的高科技文明與文化的斷裂,需要人文知識的彌合。[9]
三、現代性批判的警示意義
衣俊卿稱20世紀是一個“文化焦慮”時代的開始,日本學者大前研一認為21世紀誕生了“低智商社會”。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認為社會存在著人類精神新的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尋求契機以擺脫“工具理性”帶來的精神迷失。
在文化哲學視野中,現代性批判警示我們重視“文化自覺”,[10]構筑人的敬畏心和終極關懷。恩斯特·卡希爾(Ernst Cassirer)在《人論》(An Essay on Man)主張,從文化及人自身的活動而不是某種外在的實體來理解人的本質規定性。他指出人的突出特征正是人的勞作,這種人類活動的體系規定和劃定了人性的圓周語言,神話、宗教、藝術、科學、歷史都是這個圓的組成部分和各個扇面。[11]這也印證了以文化自覺應對文化焦慮,才能加深“人的哲學”的認識。
技術一旦擺脫有限工具和手段的地位,它就會獲得挫敗人的神性地位,人面臨臣服與抗爭的二難境遇。[12]馬爾庫塞認為最有希望提出抗議的是青年學生、邊緣知識分子以及其他種族的受迫害,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甚至將目光鎖定在“游蕩者”“流浪漢”的身上,雖然帶有一絲悲觀情緒,但“只是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賜予了我們”。[13]比如,面對這種危機,195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代表了處于文化焦慮和文化危機中的現代人自發的文化反抗。這場以青年學生為代表的“不單為了面包,還為了薔薇葉”的斗爭席卷一眾發達國家,[14]矛頭直指官僚化、科技化、效率化的社會整體。相比之下,中國當代的物質生活水平大大提高,“90后”面對無孔不入的人工智能、廣告泛濫,卻難以保持清醒獨立的思考。這也應和了阿多諾對“文化工業”的擔憂,現代科技形同一條思想光纜,給文化傳播加速的同時也讓泥沙俱下淹沒了理智。
吉萊斯皮認為現代性形成的核心并不是對宗教本身的拒斥,文明植根于宗教信仰而不是理性的自身利益,個人應在世俗王國更需建立不可摧毀的信仰;而在消費大潮中,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對“價值哲學”(value philosophy)促使主體進行估價帶來的夢魘的批判,[15]也有助于我們支持社會重塑人文文化的氣氛,以平緩群體欲望的沖動浮躁。
綜上,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首先是作為一種現代性辯證法出現的,我們不能只對現代社會關系作出解釋的話語批判,還要認識到主體對歷史進程的參與具備的改造作用。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理論論述了技術統治使人喪失批判與自由選擇,從而成為“單向度的人”,正如在《美麗新世界》中,機械化的生活日復一日困住了人對精神自由的追求,這個被異化的社會代表了束縛與牢籠,而人們沖破這種狀態關鍵在于對奴役狀態的覺醒。人需要走出科技入侵的精神癱瘓,擁有“內心向度”,保留私人空間,時刻保持對現狀的警惕心。
注釋:
[1](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8頁。
[2](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頁。
[3]Theodor W. Adorno, Prism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3, p.26.
[4](英)阿道司·赫胥黎:《美麗新世界》,宋龍藝譯,北京:北京理工大學,2013年版,第193頁。
[5](英)阿道司·赫胥黎:《美麗新世界》,宋龍藝譯,北京:北京理工大學,2013年版,第204頁。
[6](德)瓦爾特·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張旭東譯,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14頁。
[7](德)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一卷),夢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頁。
[8](德)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一卷),夢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5頁。
[9]陳麗:《2016重訪<美麗新世界>》,《外國文學》,2017年第1期,第138頁。
[10]衣俊卿:《20世紀的文化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深層解讀》,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頁。
[11](德)恩斯特·卡希爾:《人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頁。
[12]衣俊卿:《20世紀的文化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深層解讀》,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頁。
[13](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頁。
[14](法)安琪樓·夸特羅其:《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3頁。
[15](德) 卡爾·施米特:《政治的神學》,劉宗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7頁。
參考文獻:
[1][德]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一卷)[M].夢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2][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M].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
[3][德]卡爾·施米特.政治的神學[M].劉宗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4][德]瓦爾特·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M].張旭東譯.北京:三聯書店,1992.
[5]林計鑫.“技術統治”造就“單向度的人”——以《美麗新世界》為例對馬爾庫塞“單向度理論”分析[J].思想文化研究,2014,(2):49-52.
[6][美]米歇爾·艾倫·吉萊斯皮.現代性的神學起源[M].張卜天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
[7][日]大前研一.低智商社會[M].千太陽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8][英]阿道司·赫胥黎.美麗新世界[M].宋龍藝譯.北京:北京理工大學,2013.
[9]衣俊卿.20世紀的文化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深層解讀[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10]陳麗.2016重訪《美麗新世界》[J].外國文學,2017,(1):130-142.
[11]陳文旭.阿多諾“文化工業”批判的哲學解讀[J].教學與研究,2016,(12):97-102.
[12]Adorno, Theodor W. Prisms[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