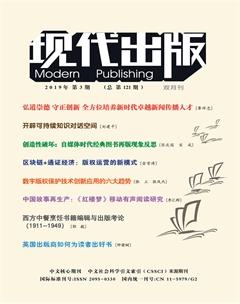創造性破壞:自媒體時代經典圖書再版現象反思
張慶園 宋成
摘要:自媒體時代,專業出版機構在經典圖書再版實踐中進行了諸多頗具爭議的創新性嘗試。在“創造性破壞”理論視角下,這些嘗試雖然破壞了經典圖書的舊有體系,但同時也打破了傳統閱讀的封閉性,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生機。具體表現在標題重編適應注意力經濟的生存邏輯、內容重構迎合需求變遷的價值邏輯和營銷創新開拓新型市場的市場邏輯三個層面。“創造性破壞”是經典圖書再版發展繁榮的一種策略性選擇,值得探索的路徑包括:分層分級定位讀者群,差異化吸引閱讀關注;重構圖書內容和體例,提升閱讀效率和價值;社交化參與讀者互動,用戶共創內容再出版;等等。
關鍵詞:創造性破壞;圖書出版;經典圖書;內容重構;圖書營銷
一、引言
《必然》(TheInevitable)一書的作者凱文·凱利(KevinKelly)曾將內容載體分為“言語之民”和“書籍之民”,并認為,在未來每一個表面都可能成為能改變人機交互模式的屏幕,人類由此遷徙為“屏幕之民”。數字化媒介閱讀的快速發展正踐行著凱文的媒介隱喻,將紙質閱讀推向“時間偏向”的另一場域①。紙質媒介趨向脫離原始的經濟功能,游離在市場經濟邊緣,卻仍不甘寂寞地進行著一系列創新性嘗試。
近年來最直觀、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一些專業出版機構紛紛嘗試借鑒自媒體“10萬+”的流量經驗,將名著經典以“標題黨”或網絡文學的方式重新提煉書名再版。文學大師沈從文的《邊城》被改名為《我明白你會來,所以我等》,俄國文學家《蒲寧散文集》變成了《我的青春是一場煙花散盡的漂泊》。2016年出版的“民國大師的經典書系”收錄了魯迅、胡適、徐志摩、朱自清等名家的九部作品,均釆用了網絡文學書名的方式和精致唯美的封面包裝來吸引眼球。
經典圖書以網絡文學式標題再版的做法迎合了自媒體時代的注意力規律和市場需求,但同時也備受爭議。批評者認為經典圖書再版的“標題黨”行為是對原著的“破壞”,“為名家文學作品集取的書名糟蹋經典”,“鼓吹傷感傷懷的無病呻吟用經典著作冠名,著實令人匪夷所思”。而有支持者則認為該行為是一種“創造性”的創新行為,認為“標題黨在時下出版界是一種趨勢”,“圖書再版不只要考慮作品質量,適應都市人的閱讀需求更加重要”。②其實,對于再版圖書的重命名一直存有爭議,早在2012年,作家桐華將自己的作品《被時光掩埋的秘密》以新書名《最美的時光》再版也曾遭到鐵桿書迷的質疑和抵抗,但她在向粉絲道歉之后仍堅持更換了書名。③因此,再版圖書重命名并不罕見,關鍵在于如何看待其背后的價值邏輯并以此揚長避短。
不可否認,在數字化媒介和消費主義主導下的社會閱讀環境中,專業出版機構的很多創新性嘗試都對傳統出版既有操作模式和思維理念產生了破壞性沖擊,尤其是經典書籍和嚴肅閱讀所蘊含的文化精神內涵面臨著被消解的風險。但另一方面,也應看到這種破壞性沖擊其實也為紙質經典出版的創新性發展開辟了巨大的想象空間。在經典閱讀式微的總體趨勢下,專業出版機構對經典圖書各式各樣的重編、再版和商業化包裝,是經典閱讀回歸值得把握的歷史機遇,還是文化精神消散前最后的回光返照?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問題。
二、“創造性破壞”理論及其現實意義
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基于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研究對“創造性破壞”這一概念做了闡釋。他將資本主義生產譬喻為一種“創造性破壞”,認為當經濟周期由景氣跌入谷底之時,也會是某些企業主體淘汰出局而另一些企業以“創新”求生存之機,這種創新會創造性地打破原有的經濟結構、創造新的經濟結構,舊的技術和生產體系被打破的同時新生產體系得以建立。④后來,“創造性破壞”理論被應用于更廣泛的領域,顯現出很強的解釋力。
美國學者泰勒·考恩(TylerCowen)研究全球化對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影響時認為,市場的“創造性破壞”本身就是一門藝術,在許多不同的類型、風格與媒介中創造出了創新和高質量的作品。⑤劉帆使用該理論對好萊塢大片影響下中國式大片的發生和發展進行了研究,發現好萊塢大片席卷中國市場、擠占中國電影市場份額的同時,也在客觀上對中國電影整體創作觀念、思路和方法進行了創造和建設,使中國式大片得以醞釀。⑥陳凱、劉柏煊在針對美國社區報應對數字化挑戰的轉型策略研究中認為,美國社區報是在探索削減成本、增加盈收、推行“付費墻”制度以及重塑讀者閱讀習慣的“創造性破壞”中尋求生存。⑦
實際上,“創造性破壞”理論所闡釋的要義在于,新事物的快速發展使舊事物面臨被淘汰的危險,但舊事物也可能借由破壞中蘊藏著的創造性獲得意想不到的生機。舊事物遭遇的“創造性破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改變傳統形態適應新趨勢發展的生存邏輯、吸收外來文化賦能新內涵的價值邏輯、變革傳統觀念以重獲用戶的市場邏輯,以此實現困境中突圍。當下,隨著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集群的加速發展,各行各業均面臨著新技術變革所帶來的顛覆性重構,“創造性破壞”成為社會發展的一種現實路徑。出版業亦是如此,如果不想被帶來“創造性破壞”的新技術“破壞”,就要抓住其中的創新機遇,進行產品創新與戰略變革。⑧
三、經典圖書再版實踐中的“創造性破壞”及其價值審視
圖書再版是指對原書內容或形式進行一定修改后重新排版印制。再版圖書是對圖書內容或形式的更新以提高圖書質量,也是對專業知識的傳承和積累,實現了出版資源的再開發。⑨其表面上體現出一種審美需求上的“懷舊”情緒,其背后反映出社會對老一代人作品價值的再認識、再發現。⑩圖書的重印和再版也是打造品牌圖書的關鍵環節。?圖書再版既包含著對原著內容和形式等的客觀傳承,也隱含著出版機構對圖書再認識的主觀改造。對于經典圖書的再版實踐而言,頗受爭議的當代改造是否是一種頗具積極意義的“創造性破壞”,值得重新審視。
1.生存邏輯:標題重編適應注意力經濟
1997年戈德海伯(MichaelH.Goldhaber)在《注意力購買者》一文中正式提出了“注意力經濟”這一概念。他認為,互聯網時代,相對于過剩的信息資源,人們有限的注意力才是稀缺性資源,注意力經濟是“企業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戶或消費者的注意力,通過培養潛在的消費群體,以期獲得最大的未來商業利益的經濟模式”?。自媒體將“注意力經濟”演繹到了極致,“10萬+”成了新的衡量標準,被關注成了首要環節,網絡大號紛紛以“標題黨”和病毒式傳播的方式瘋狂爭奪公眾注意力資源,并創造了一個又一個閱讀神話。
當前,經典圖書再版實踐也常常借鑒自媒體語境中的注意力捕獲經驗,自媒體的一些亂象也隨之蔓延至出版領域,不可避免地對名家名作經典原著造成了較為直觀的“破壞”。如前文所述將經典圖書的篇名加工成“標題黨”,又如腰封上夸大推薦詞,名之為“全國第一”“史上最好”“萬人落淚”“中國人必讀”的噱頭比比皆是,再如封面上使用超大字號凸顯“某某名家推薦”等加以背書。
相對于更為嚴峻的生存和傳承問題而言,經典圖書再版的破壞并非全無是處,其中也不乏“創造性”價值,甚至可以將其看作一次知識平權化的新革命。庫利認為“印刷意味著民主”。然而,廉價的印刷和紙質文化產品促進了大眾文化消費,卻并沒有自然而然帶來想象中的知識自由和平等。人們發現,對于任何知識的傳承傳播來說,讀者都是分層次、分領域的,不同文化水平、社會階層、教育和職業背景以及對媒介的使用和控制能力是影響知識平等獲取的天然屏障。自媒體時代,技術賦權再一次喚醒了人們對民主化傳播的強烈渴望,電子書一度被賦予了知識平權化傳播的烏托邦式想象。但是,數字化媒介難以承載深層次、沉浸式的嚴肅閱讀的功能,普通讀者在忙碌的日常事務和大量的文化產品中也不會因為便捷和廉價而對經典內容形成關注或產生閱讀動力。因此,經典圖書再版形式層面的“創造性破壞”能夠促使原本塵封許久的經典書籍贏得注意力競爭,在當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知識的社會區隔,經典知識的文化功能和社會效益得以最大化。
2.價值邏輯:內容重構迎合需求變遷
1964年,美國傳播學者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Stephenson)提出的“傳播游戲理論”認為傳播本身和受眾的媒介接觸行動都是一種游戲活動,“傳播活動本身就是目的,因為它能給他人帶來快樂”?。因此,用戶需求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媒介的內容提供。在此視角下,閱讀是一種發達的“主觀游戲”,人們通過閱讀謀求自我提升、自我滿足和自我存在,帶有強烈的主觀自發性。
自媒體更好地利用了人們古老的“閱讀游戲規則”,造就了大眾化、碎片化、淺層次的閱讀形態,而對經典閱讀的深層次、高沉浸體驗以及系統性的知識結構獲取方式產生了極大沖擊。讀者需求的變遷導致經典再版的內容重構成為一種極具誘惑的選擇。例如,《論語》自西漢張禹編定以來,一直按照學而篇第一、堯曰篇第二十的順序展開,錢寧重編的《新論語》卻將原有體例完全打亂,不增不減一字一句,卻以現代思維重構經典古籍。以“內編”五篇為例,分為“核心篇”“路徑篇”“實踐篇”“例證篇”“哲思篇”,在每一篇下,邏輯嚴密,自成系統,迎合了當代讀者的閱讀習慣。?
這種對經典圖書內容層面的“破壞”實質上也“創造性”地讓經典知識獲得了跨地域、跨行業、跨迷群的傳播和傳承。黨的十八大以來,推動全民閱讀已經成為黨中央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全民閱讀”已連續5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先后6次被列入國務院立法計劃,全民閱讀已經上升至國家戰略。?全民閱讀的推廣需要激發讀者對高質量經典讀物的閱讀興趣,倘若不考慮不同讀者的閱讀意愿、閱讀能力及自媒體語境下的閱讀需求,勢必會讓普通讀者望而卻步。
以符合現代人閱讀需求的邏輯對經典圖書進行重構,這種內容層面的“創造性破壞”是對經典圖書內容價值的最大化發掘,能夠更好地適應當下不同層次讀者的需求,從而形成經典圖書再版的良性生態。
3.市場邏輯:營銷創新開拓新型市場
專業出版機構正面臨著媒介技術變革和市場需求變化的雙重壓力,隨著互聯網經濟的崛起,圖書營銷的互聯網思維成為影響圖書銷量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尤其自媒體時代知識付費模式的快速興起和發展成熟,誕生了如社群營銷、微博/微信營銷、自出版等諸多營銷范式和出版新模式。專業出版機構及互聯網創業者們對傳統文化的衍生和轉化進行了一系列創新,最大程度迎合了知識付費模式和現代人綜合媒介體驗中的閱讀需求。
自媒體對經典書籍的“破壞性”尤其體現在對原有內容的碎片化再傳播上,其打破了原有的知識結構,建構起了一套新的適應現代人的知識體系,它以實用性和快速閱讀吸收為名,吸引著那些渴望從經典書籍中尋找實用指南或心靈慰藉卻無閑暇時間仔細品讀原著的知識焦慮群體。例如,羅輯思維利用“知識付費+品牌社群”的方式,以“用新技術重新生產知識,為用戶提供單位時間價值最大化的學習解決方案”為宗旨,將經典圖書進行碎片化重新解讀,以提供給用戶實用性的知識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又如樊登讀書會所宣稱的,以文字解讀和視音頻講解的形式,幫助那些沒有時間讀書、不知道讀哪些書和讀書效率低的人群每年吸收50本書的精華內容,吸引著成千上萬的付費會員。
與此同時,新營銷方式還引導現代人嘗試不同媒介形態互文的綜合體驗,充分激發其中的紙質閱讀需求。如,華納兄弟在取得世紀文景版《霍比特人》《魔戒》的譯名使用權后,在新版圖書上市時,同名電影《霍比特人:意外旅程》也在全球同步熱映,助推了新版圖書的銷售。
在新營銷方式推動下,日常生活和經典內容之間建立了空前緊密的聯系,經典知識的需求被廣泛激發。無疑,這種“創造性破壞”蘊含了為經典圖書再版開拓新型市場的可能性,也為專業出版機構業務創新及轉型升級提供了借鑒。
四、自媒體時代經典圖書再版的策略創新路徑
2018年4月由亞馬遜中國攜手新華網發起的全民閱讀大調查的數據顯示,從整體看,經典名著以及國內外文學作品依舊是大眾在內容選擇上的主流。2018年8月國家新聞出版署發布的《2017全國新聞出版業基本情況》顯示,截至2017年年底,重印圖書在品種上首次超過新版圖書,總印數達到新版圖書的2.4倍,再版圖書的市場規模呈現不斷擴大趨勢。?可見,經典圖書再版仍具有巨大的市場空間,而“創造性破壞”是經典圖書再版發展繁榮的一種策略性選擇和現實路徑。如何揚長避短、進一步促使經典圖書的價值最大化,創造新的利基市場,筆者認為專業出版機構可以從以下三方面進行探索:
1.分層分級定位讀者群,差異化吸引閱讀關注
經典圖書經過較長時間的歷史積淀,內在具有普遍的社會價值,具有較大的讀者覆蓋面。但不可否認的是,由于社會階層、知識水平以及讀者品位的不同,對于經典的理解和選擇存在著明顯的社會分層和態度差異。小清新式的“標題黨”容易被文藝青年接受,但會被追求深度閱讀、具有較高知識文化層次和審美能力的讀者排斥。
因此,經典圖書再版的“創造性破壞”首先要考慮的是讀者分層、差別定位,應該考慮根據不同的讀者的閱讀水平進行分層次出版。?除考慮按不同的年齡層次、不同教育水平劃分外,更應考慮按不同實用性價值和審美性價值細化讀者群體,定制化出版針對某一特定群體的書籍。例如,針對兒童群體,除了增加拼音注釋、插圖、延伸閱讀等,內容可以聚焦小故事短篇化,同時配合書名或篇名的少兒化重編;針對青少年群體,可以在文藝化書名的基礎上,結合流行網絡文學熱點進行改編再創作,在內容篇幅和深度上降低閱讀難度,形成對比效應,凸顯經典價值;針對具有較高知識素養的群體,則可以增加名家批注、閱讀心得等豐富原版圖書的文化內涵,以相應新觀點、新角度命名或沿襲經典書名,滿足其更深層精神文化體驗的閱讀需求。
2.重構圖書內容和體例,提升閱讀效率和價值
“創造性破壞”經典圖書的內容完整性具有現實意義。一方面,經典圖書雖然具有巨大的文化精神價值,但其產生都有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時代背景,對于經典圖書的閱讀需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另一方面,經典圖書內容結構完整、篇幅較大且存在部分在特定語境下才能理解的生僻用詞、用語,對生活在自媒體時代快節奏生活中的現代讀者而言閱讀難度頗高。各種雞湯文和暢銷書沖擊并消解著經典圖書的文化精神價值。
經典圖書再版可以在尊重原版作者著作權的前提下,保留基本的框架、編排結構,繼承優質內容。?不僅如此,在“創造性破壞”視角下,經典圖書的再版應大膽創新圖書體系和體例,不再只局限于對某一本書籍內容的多樣化加工,而是根據當代讀者的需求將多本經典的內容進行重新組合。可以按照某一特定主題或以類似文獻綜述的形式進行再次編排,并借鑒再版索引的文獻組織方式,使讀者無須閱讀書籍全部內容便能夠對某一特定話題進行廣泛且深度的研讀。這在滿足讀者效率追求的同時也使經典圖書的價值得到最大化。類似思路在當前古典詩詞的重組再版實踐中效果頗佳。
3.社交化參與讀者互動,用戶共創內容再出版
數字閱讀打破了傳統閱讀的封閉性,延伸了閱讀的內涵和邊界,自由、開放、社交化的閱讀方式對紙質閱讀造成了巨大壓力。近年來,傳統出版機構新媒體融合的積極努力已初見成效,搭建用戶共創的自出版平臺“已有較成熟的經驗,需要強化的是,對于用戶自出版的內容,不能以個性之名簡單聽之任之,而應圍繞普通讀者情感滿足和增強社交兩大需要,提供不同程度的專業化內容生產指導和服務”①。
因此,經典圖書的再版需要借助于新技術、新平臺,以適應自媒體時代讀者閱讀和參與的綜合需求。經典圖書的內容體系無須完全固守,而應將其與新媒體融為一體進行碎片化傳播重組,讓其在社交化新語境中煥發新的生命力。例如,目前有新媒體平臺拆解長篇經典詩集,進行“每日讀詩”的傳播推送,每天在固定時間段推送一篇經典詩,并邀請知名作家、演員、意見領袖等進行朗讀,吸引公眾參與詩篇或文章的解讀并給予一定的獎勵。當整本詩集全部推送完畢后,再對公眾參與的原創內容以及名家的點評、音頻等打包再出版。如此,在原著經典內容基礎上增添了用戶參與的原創內容,提升原著理解度的同時激發了參與者言論出版“成名的想象”,能夠進一步激發讀者的閱讀和參與興趣。
五、討論與思考
傳統閱讀中,人們為了獲得知識和真理而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與作者進行精神交往和對話,讀者往往需要一定的知識儲備和文化素養才能理解文本中的意義和作者所傳遞的見解。經典圖書再版實踐中對形式、內容、營銷等的“創造性破壞”打破了傳統閱讀的封閉性,降低了經典書籍閱讀的知識門檻,促進了經典閱讀回歸和全民閱讀的推廣,讓經典內容重獲市場關注,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但同時也應該警惕,在消費主義文化主導下,閱讀容易蛻變成為通俗化、娛樂化的消費欲求,而讀者則容易退化為“單向度的人”,沉迷于通俗娛樂的洪流,逐漸失去自我批判和獨立思考能力。經典圖書再版的“創造性破壞”不能只是一味迎合讀者的消費欲求,而是要在新的閱讀環境中探索引領新的途徑和方向,否則只會讓經典圖書所具有的思想內涵和知識權威被解構,文化和社會價值被抹殺。
注釋:
①張慶園,宋成.紙質回歸與平臺建構:專業出版機構的新媒體融合與運營探究[J].出版發行研究,2018(10).
②新華日報.沈從文等名家大作書名被改成言情范兒,網友:糟蹋經典![EBA)L].http://k.sina.com.cn/article_3881380517—e7592aa502000g8au.html,2018-11-30.
③萬闋歌.圖書再版何需改名[N].中國藝術報,2012-08-20(006).
④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⑤考恩.創造性破壞:全球化與文化多樣性[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
⑥劉帆.創造性破壞——好萊塢大片影響下中國式大片的發生與發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⑦陳凱,劉柏煊.美國社區報:近五年里的“創造性破壞”[J].新聞記者,2015(05).
⑧黃杰陽.移動互聯時代圖書出版業的環境分析[J].出版發行研究,2012(11):92-94.
⑨薛紅.淺談精品科技圖書再版的價值——以《現代同步發電機勵磁系統設計及應用(第二版)》為例U].科技與出版,2012(12).
⑩漢初.美術圖書出版領域中的“啃老”[J].美術觀察,2010(06).
?曾亞非.圖書再版如何寘正做到圖書品牌的提升與再創[J].編輯之友,2010(11).
?MichaelH.Goldhaber.AttentionShoppers[J].Hotwired,1997(12).
?Stephenson,William.Theplaytheoryofmasscommunication[M].TransactionPublishers,1964.
?胡海迪,LiYuliang.論民國以來《論語》的重編[J].孔學堂,2018,5(02):89-96,197-206.
?劉雪花,陳思文.閱讀立法視野下社會力量參與全民閱讀推廣研究[J].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8(06).
?楊方銘,鄒鑫.“得到”APP運營模式及其對數字出版的啟示[J].出版發行研究,2018(07).
?2017年全國新聞出版業基本情況[J].新聞世界,2018(11):57.
?詹學偉.對經典圖書再版的思考——以《魯迅小說全編/集》的出版狀況為例[J].出版廣角,2012(02).
?陶峰.科技圖書再版著作權主體的合理變更淺議[J].出版發行研究,2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