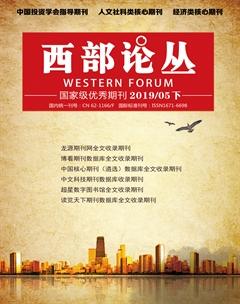電視紀錄片制作的聲畫細節把握
就藝術與現實生活的關系問題而言,紀錄即是一種對原始素材進行檢篩與整理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要在平凡、平實甚而是平淡的日常生活中進行深入、深刻、深邃的心靈體驗并不容易。紀錄片的故事化敘事方式正被越來越多的業內人士和觀眾所認同。這是多年來創作者們為了擺脫中國電視紀錄片收視率下滑、市場冷落的困境,而不斷探索新的表現方式的結果。從前幾年中國電視紀錄片學術獎獲獎片中,可以看到以故事化來表述的紀錄片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很多優秀作品,都顯現出講故事在紀錄片傳播競爭中的力量。
在媒體傳播競爭激烈的今天,實踐總是走在理論的前面,電視媒體尤其如此。但是理論在實踐面前并非束手無策,認真分析研究紀錄片的特性與它的故事化敘述方式,我們就不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認真觀察、研究了國內外同行成功的人文類、社會類、自然類紀錄片之后,我發現了一個新的重要的流行創作手法和規律――紀錄片故事化,即在真實紀錄的前提下,借用電影故事化、電視劇創作中的一些故事化、娛樂化藝術元素,使我們講述的真實的故事對娛樂和資訊豐富的當今觀眾更具吸引力和影響力。落在紀錄片制作過程的實處上,就是最重要的兩種組成要素,聲音和畫面。
聲音,作為視聽媒介的基本物化元素,與畫面一起構成特定的審美時空。電視紀錄片中對人物同期采訪聲的大量運用可以說是突破傳統電影紀錄片的巨大技術躍進。電視的采錄設備為我們提供了同步記錄真實聲畫時空的手段,聲音的全方位傳播使畫面的內涵得到伸延,使人物的情感得到更充分的展現。在《紙殤》的開頭,古老的造紙機器發出的音效與多機位的畫面同步,讓我們感受到原始的造紙技術在現代文明中的那份沉重。
目前,各類型的現場聲效和人物同期聲逐漸取代不必要的冗長解說已成為電視紀錄片的新時尚。而穿插在現場紀實畫面之間的同期訪問談話,直接向觀眾敘述,不僅提供了背景材料,發表了議論,又避免了編導的主觀介人,使作品更加客觀、公正和可信。
留心觀察,可以發現在紀錄片訪談中大量使用的微型無線話筒和吊桿話筒,主持人和被訪對象襯衫上別著的微型無線話筒替代了叫人生厭的“棍棒式”大話筒,使每次采訪(或人眾或人寡)都猶如春天里輕松自然的促膝談心一般透著生活中真實、濃郁的人情氣息。這種無線話筒和吊桿話筒的使用,徹底拆除了攝像機鏡頭前采訪人與采訪對象之間無形的墻。采訪人不再是生硬的話筒架子,而是一個可以平等交流的對象。屏幕上的人際交流更加接近生活狀態下的自然交流,具有良好的效果。
除了同期聲的采錄,紀錄片中利用多軌調音錄音技術記錄生活背景聲、使用數字一體化攝像機的多個聲道在鬧市區的采訪音效記錄等都極大地豐富了聲音在作品中的藝術表現力,為觀眾展開了真實的生活氛圍時空。
實際上,紀錄片中的聲音成分相當復雜,它不僅僅只有解說詞,它還包括:人物同期聲、自然音響、效果音響、音樂,它們在作品中經常和畫面相互配合、相互作用。
人們注意到現在紀錄片創作中,解說的聲音在減少,創作者已經不是事先寫好解說詞然后再按解說詞拍攝畫面了。解說詞在片中的比例已經縮小了,有許多是化為同期聲和字幕。解說詞的寫作和“播讀”也不再那么張揚創作者的主觀感情和態度,而是作為客觀的敘述者為觀眾交代背景、連接內容。所以多數紀錄片的畫外音解說 “讀”出來的感覺不再是“宣傳腔”、“播音腔”,而是追求平實的,客觀的、冷靜的風格。
我們也看到了一些紀錄片通片沒有解說詞的,我在這里并不是在提倡紀錄片通片都不用解說。解說詞為聽而寫,解說詞并不是不可以用來表現概念抽象的內容和創作者的主觀情感,以及對畫面視覺信息起整合作用,但是紀錄片的解說詞和畫面不能夠脫離,他們之間不僅僅是一個相互補充的關系,而且還是一個相互作用、相互加強的關系。在一些政論、歷史、文化題材的電視紀錄片中,對承載了許多信息的畫面而言,更應該突出解說詞的重要性。但是,就綜合的聲效語言表現來說,人物同期聲、自然音響、效果音響、音樂也都是不可缺少的。我們常說傳統的專題片“畫面聲音兩張皮”,傳統的專題片不是沒有聲音,只是它往往是后期播音員配上的解說詞和后期配的音樂或者效果聲,聽起來非常完美,但是完美得不真實。紀錄一個人物的生活,聽不到這個人的聲音、聽不到大自然的聲音能夠說是真實的嗎?一個沒有聲音的人就有可能是啞巴。而全部用“音樂打底”,真實性就大打折扣了。從專題片制作到紀錄片創作,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就是“聲音”受到人們的重視。
在紀錄片的聲效語言,同期聲也許是最重要也最復雜的。
同期聲:即在畫面中可見其聲音來源的聲音,或視頻和音頻同步記錄的現場聲。同期聲實際上包括現場采訪的人聲(即人物同期聲)、現場動物和背景自然音響。
我們在拍攝紀錄片,攝像機的話筒必須永遠開著,哪怕在后期編輯的時候有些同期聲沒有派上用場。紀錄片運用同期聲有什么作用呢?首先,它能夠增強現場的真實感,把觀眾帶入紀錄片所表現的環境和氛圍里去,達到對真實世界的完整復原,其次,它可以增強節目的參與性和可看性,使節目不再是單方面的播音員解說。紀錄片《望長城》的紀實魅力就在于大量使用同期聲。今天的電視觀眾早就不滿足于看到嘴巴在動沒有聽到聲音的畫面,為什么可以讓主人翁說的話非要讓播音員去說呢。同期聲不是背景,同期聲也是解說詞,是表現人物和事跡的重要手段。
紀錄片的同期聲運用必須盡量在技術上保持聲畫同步,以獲得真實的效果。但是,在編輯紀錄片的時候我們有時候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即聲音比畫面早出現,這就是前延聲。還有一種后延聲:即畫面已經轉換仍持續著聲源的聲音。為了不讓同期聲過于冗長,增加畫面的節奏感和信息量,編輯片子就要注意使用前延聲和前延聲。
紀錄片的音樂,實際上是后期配上去的,運用得好,當然能夠抒情表意,紀錄片的音樂絕對不可以一灌到底,因為畫面的節奏是變化的,孤立于畫面以外的音樂,是沒有效果的,或者是反作用的,也會影響作品的真實性的。好的紀錄片的音樂是有聲源的,即畫面上交代出發聲體,如紀錄片《英和白》有許多音樂不是后期加上去的,而是通過畫面上交代出發聲體,自然表達出來的,抒發了作品的感情色彩。紀錄片的音樂運用要慎重,因為音樂是表現主觀的感情,而紀錄片是追求客觀的真實的。
紀錄片聲畫一體化的復合結構,聲音和畫面往往并沒有哪個更重要或誰補充誰的區別,它們都在表達一種真實的物質存在。例如:畫面是田野山村,有狗叫聲、流水聲或者特定的現場自然音響,這些現場效果聲本身并沒有補充山村畫面在表達意義方面的不足,人們之所以大量運用這些聲音,是在利用聲音信息的潛在能力,通過聲音和畫面雙重信息的相互作用,創造出一種真實感和現場感。那種傳統的音樂墊底,一鋪到底的做法,之所以不受同行及觀眾的認可,也并不是因為它沒有補充畫面的不足,而是因為它忽視了聲音傳播信息的功能。
毫無疑問,人們看電視,不僅要“看”,而且要“聽”。
紀錄片的聲效語言構成了電視屏幕的“聲音形象”,它和畫面語言一樣,都是紀錄片創作的一個重要手段,只不過在不同的情境中,它的偏重點有所不同而已,有時候是畫面語言在發揮作用,有時候是聲效語言在發揮作用,紀錄片的聲效語言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進一步研究。
作者簡介:董順剛,男,1985年5月,民族:漢,河北邯鄲人,學士學位,浙江傳媒學院,研究方向:電視攝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