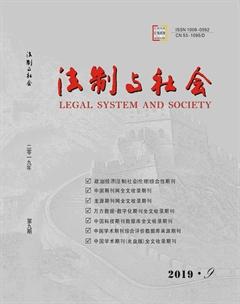侵權審判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問題的研究
張鵬 陶朋
摘 要 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這24個字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本文旨在研究從侵權審判實務中遇到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所體現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關鍵詞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侵權審判 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
作者簡介:張鵬,江蘇省泰興市人民法院道路交通事故審判庭庭長;陶朋,天津市寶坻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助理。
中圖分類號:D92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9.063
從侵權審判中研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要落實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這8個字上。從法治的根本遵循到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從法律的價值追求到社會秩序的運行狀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審判工作實踐中應當踐行和體現的核心內涵。為了深入闡述這一命題,我們從實務中案件量既大又繁瑣的侵權案件,即機動車交通事故侵權糾紛來研究侵權糾紛中所體現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下從三種情形下進行討論:一是機動車與非機動車之間發生事故,雙方均有責任。二是機動車與非機動車(或行人)之間發生事故,機動車方無責,非機動車方(或行人)全責。三是機動車與非機動車之間發生事故,非機動車方(或行人)無責,機動車方全責。
一、雙方責任情形的現實處斷
審判中所依據的責任標準是交警部門出具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而在審判實務中,交警部門出具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有時是交通事故責任雙方妥協的產物,機動車肇事方在發生交通事故后,因為該機動車投保了交強險和商業險,往往為了逃避自身的賠償責任而自認全責,這種自認全責的行為可以由保險公司承擔交通事故的賠償責任,法院在審判時也可以比較容易裁判,而受害方也能夠得到較高的賠償金,三方看似圓滿解決了該起交通事故糾紛。在實務中這是一種較為常見的做法。
然而從這種情形下,我們也不難發現一些看似公平實則不公平的細微之處:法院據以用作裁量標準的重要證據是交警部門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而該責任認定書是當事人合意的結果,合意的潛臺詞是該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包含有妥協的成分,在實務審判中往往看到這樣的協議書,內容是在交警部門的主持下,交通事故受害方不追究肇事方除了保險公司賠償金額外的其他經濟賠償,以此換取肇事方認定全責。事實上也是如此,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件中,不遵守交通規則,任意自由行駛的非機動車導致的交通事故可以說是占據了大多數,而受害方為了爭取更高的經濟補償,同時肇事方也擔心不認全責會導致自身賠償受害方部分損失,故而雙方簽訂如此協議。這種協議可能說從結果上來說雙方都能夠接受,雖然從肇事方和受害方雙方看,是一個好的結果,但是從保險公司角度來看,這兩方合意的結果就是侵害了保險公司的利益。交警部門所作出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實際意義上來說是一份“偽證”,而且是在審判實務中都不嚴格加以質證的“偽證”。
二、非機動車方(行人)全責的賠償責任
以這樣的一個案例來加以說明:2019年5月16日,王某駕駛機動車從美好小區出門右拐時,與駕駛電動自行車的華某發生剮蹭,導致華某受傷倒地,華某駕駛的電動自行車在事故發生后剮蹭到停在小區門口的陳某的小型轎車。很顯然,陳某對這起交通事故并不承擔侵權責任,但是陳某缺應當對華某的受傷承擔交強險責任內的無責賠償責任。
因為根據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關規定,確立了交通事故責任糾紛中的無責賠償制度。即機動車駕駛員與非機動車或行人發生交通事故時,即使機動車駕駛員沒有任何責任,也承擔賠償責任。國家并建立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規定無責賠償從強制保險限額中支付。也就是說:在交強險的賠償范圍內,只要是事故當事人之一,無責任方所在的保險公司也必須得按無責賠償限額給財產受損者或人身受傷者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將風險轉移到保險公司,體現交強險強制保險的優越性,實現對受害者的保險補償。也就是說,哪怕陳某同樣是這起事故的受害方(車被剮蹭),陳某所投保的保險公司也應當對華某進行賠償。
從這一案例我們也能看出立法者在立法時充分考慮到受害者利益,從立法層面為了防止交通事故中非機動車方由于機動車方的撞擊,剮蹭到其他機動車的時候造成二次傷害。雖然該規定對于被剮蹭車輛是不公平的,但是確保了非機動車方能夠得到最基本的保險賠償,維護交通事故中弱勢方的點滴權益,通過“損有余而補不足”這種立法規定以及司法審判的標準,正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立法以及審判實務時具體表現。
三、機動車方全責的保險合同相關問題
以這樣一個案例來討論:2016年5月18日,蔣某醉酒駕駛導致了交通事故的發生,導致行人黃某受傷,且蔣某無力承擔對黃某的經濟賠償,但是蔣某的機動車在某保險公司投保了交強險以及第三者責任險。蔣某的行為顯然已經構成了刑事犯罪,那么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實務審判中是如何裁判肇事方賠償受害方經濟性補償的?有些法院是裁定由肇事方的保險公司從商業險部分對受害方進行經濟補償,但是所依據的理由卻是保險公司在格式合同中未盡到提示義務,這種做法并不妥當。
(一)從合同效力性問題上突破,必然從格式條款提供者責任上入手
從格式條款提供方責任來看,《保險法》第十七條規定:“訂立保險合同,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的,保險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單應當附格式條款,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合同的內容。 對保險合同中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在投保單、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對該條款的內容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確說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第十九條,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中的有關條款無效。保險合同作為典型的格式合同,其中涉及限制投保人權利及義務的條款,必然不包括限制投保人飲酒,就算真的限制了,那也是出于對投保人人身安全的考慮,提示投保人注意該條款與否,不屬于《保險法》第十七條、第十九條規定的格式條款無效情形,并不因此影響合同效力。故從合同的效力性問題上無法使保險人對受害方補償。
(二)以保險合同投保人與實際駕駛人不一致,保險人未對駕駛人起到提示義務為由主張
首先“醉酒駕駛”作為法律明文規定的禁止性行為,已經被列入到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為廣大普遍群眾所熟知。同時機動車駕駛人員在取得駕駛資質時,必然地受到交通管理部門針對性的重點安全教育,清楚地知道醉駕的危險及相關法律后果,故機動車駕駛人員并不因保險人未向其提示就不知“醉酒駕駛”的法律后果,兩者無必然的因果關系。其次,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四)第二條規定表明:即使在簽署商業險保險合同時,保險方盡到了提示義務,也難以保證投保方與發生事故時實際駕駛員是同一人,實際駕駛員也不得以保險人未盡到提示義務為由主張賠償。
以上通過從侵權審判實務中遇到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從而研究出其中所體現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來看,審判中為了保護受害方的權益,法律在公平的角度上都稍微向受害方傾斜了,雖然這種做法于法理上有所欠缺,但是這也是法院在實務中不得已的一種傾斜,最起碼在目前的審判實務的結果上看是好的,注重社會效益,有利于維護社會的穩定。法律需要我們用實踐不斷驗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法院公正地審判,但是如果適當的傾斜能夠給出當事人雙方都滿意的裁判,能夠“拔九牛之一毛”作為弱勢方“救命之稻草”,這種適當的傾斜是值得的,同時,實務中的這種做法也能夠逆向地指導我們改善現有法律的不足之處,注重社會效益,靈活地運用法律,這樣的道路才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指導下的中國法律該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