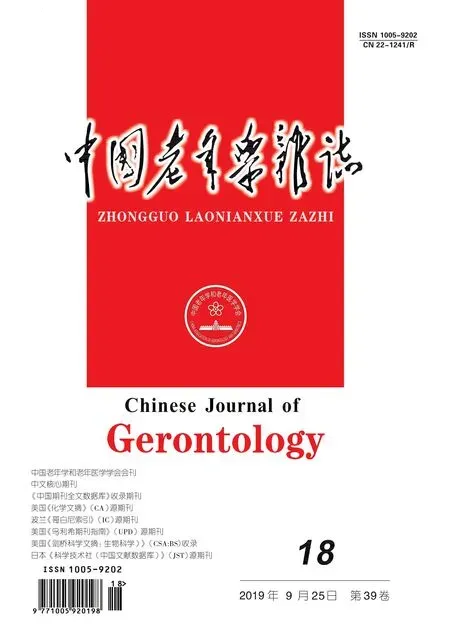營養不良在社區老年人抑郁和衰弱之間的中介作用
劉欣藝 喬曉霞 金雅茹 司華新 王翠麗
(1山東大學護理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2;2北京大學護理學院)
2017年我國60周歲以上的人口達2.4億人,占總人口的17.3%〔1〕。隨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劇,老年人的衰弱問題日益嚴重。有研究將衰弱定義為生理儲備降低和多系統功能失調,從而限制了機體對內外的應激和保持內環境穩定的能力,增加對不良結局的易感性〔2,3〕。在影響老年人衰弱發生的因素研究中,抑郁作為最常見的心理因素得到了廣泛關注,已有研究證實了二者間的相關性〔4,5〕。抑郁是通過何種途徑導致老年人衰弱的發生尚不明確,除了二者間可能存在共同的病理生理機制外,抑郁還可能通過導致老年人身體功能下降、認知功能損傷、睡眠障礙、營養不良等引發衰弱〔6~8〕。其中營養不良在抑郁人群中極為普遍,有研究表明重度抑郁癥患者營養不良的風險是非抑郁癥患者的15.5倍〔9〕。營養不良也是影響衰弱發生發展的一個重要危險因素〔10〕,在衰弱發生早期增加營養攝入可以預防或逆轉衰弱的發生〔11〕。本研究擬分析營養不良在社區老年人抑郁和衰弱間的中介作用。
1 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2018年6~8月,采用多階段分層抽樣方法,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好、中、差)從濟南市抽取3個行政區(歷下區、市中區、天橋區),在每個行政區內抽取7~8個社區作為調研點,共選取22個社區的老年人進行調查。納入標準:①年齡≥60歲;②自愿參加本研究。排除標準:①重度認知功能障礙者;②疾病危重的老年人。本研究共發放問卷938份,回收有效問卷936份(99.8%)。研究對象平均年齡(70.15±6.12)歲,男290人,女646人,有配偶714人,平均受教育年限8.6年,月收入≥1 910元(2018年濟南市月最低工資標準)865人,52人有認知功能障礙,平均患慢性病種類為1.5種。衰弱的老年人35例(3.8%),衰弱前期487例(52.0%),營養不良或營養不良風險者共108例(11.5%),有抑郁癥狀97例(10.4%)。
1.2方法 調查員采用問詢式調查法根據老年人的回答代替其進行真實填寫,填寫完畢后現場收回,之后采用統一的方法進行身體評估(包括體重、握力、步速)。調查工具:①一般資料調查表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年限、婚姻狀況、月收入和患慢性病種類(高血壓、糖尿病、腦卒中、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癌癥)。②認知功能評估:采用簡易認知狀態問卷(SPMSQ)〔12〕評估老年人的認知功能,若SPMSQ判定為重度認知功能障礙者,則停止問卷調查。③老年人抑郁評估:采用老年人抑郁評定量表(GDS-5)〔13〕評估老年人的抑郁癥狀,該量表共5個條目,GDS-5是在GDS-15基礎上設計的,并已證實篩查老年人抑郁的準確性與GDS-15相同〔14〕。GDS-5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癥狀越嚴重,2分及以上者可推斷其存在抑郁癥狀〔13〕。④營養狀況評估:采用由Rubenstein等〔15〕編制、Kaiser等〔16〕修訂的微型營養評價精簡法MNA-SF評估老年人的營養狀況,共6個條目,計分范圍0~14分。得分12~14分為營養狀況正常,≤11分為營養不良或有營養不良的風險。已有研究證實MNA-SF和傳統營養指標相關性較好,且比傳統的微型營養評價法(MNA)耗時短、簡便易行〔17〕。本研究中將營養不良或有營養不良的風險合并稱為營養不良。⑤衰弱評估:Fried身體表型衰弱量表是Fried等〔3〕建立的可用于社區及住院老年人衰弱評估的量表,包括5個指標:(1)體重下降,(2)疲乏,(3)低體力活動,(4)步速緩慢,(5)握力下降,總分0~5分。得分越高說明衰弱越嚴重,0分表示不衰弱,1~2分處于衰弱前期,3分及以上為衰弱。
1.3統計方法 采用SPSS21.0軟件進行描述性分析、方差分析、χ2檢驗、有序和二項式logistic回歸分析。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抑郁、營養不良、衰弱之間的關系,采用Iacobucci〔18〕提出的中介效應檢驗方法——Z檢驗來驗證營養不良在抑郁和衰弱關系中的中介效應。
2 結 果
2.1不同衰弱程度老年人特征比較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衰弱程度較高的老年人有抑郁癥狀及有營養不良風險或營養不良者所占比例更高(P<0.001)。衰弱程度較高的老年人年齡更大(P<0.001)、受教育年限更少(P<0.001)、喪偶者更多(P=0.010)、認知功能障礙率更高(P<0.001)、患慢性病種類更多(P<0.001)。見表1。

表1 不同衰弱程度老年人特征比較〔n(%)〕
2.2老年人營養不良的中介效應分析及檢驗 在調整協變量基礎上,以衰弱為因變量,抑郁為自變量,構建有序logistic回歸模型1;以營養不良為因變量,抑郁為自變量,構建二項式logistic回歸模型2;以衰弱為因變量,同時納入抑郁和營養不良構建有序logistic回歸模型3。結果顯示,抑郁增加了衰弱(OR=3.149,P<0.001)與營養不良(OR=21.632,P<0.001)的發生風險;營養不良增加了衰弱風險(OR=2.377,P=0.001),且減弱了抑郁和衰弱關系強度(OR=2.075,P=0.006)。Z檢驗(Z=3.234,P<0.01)結果顯示營養不良在抑郁和衰弱關系中具有顯著中介作用。見表2。

表2 營養不良在抑郁與衰弱間的中介效應
1)營養不良包含營養不良及有營養不良的風險
3 討 論
本研究顯示,濟南市社區老年人衰弱的發生率為3.8%,低于Wu等〔19〕采用Fried衰弱表型在全國老年人中的調查結果(7%),但與東部地區城市老年人結果(3%)基本一致。這可能與不同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有關,較為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的衰弱發生率低于欠發達的西部地區,城市低于農村。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表明,抑郁不僅能夠直接顯著預測衰弱,還能通過營養不良的中介作用對衰弱產生間接影響。本研究發現,抑郁增加衰弱發生風險,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4~6,20〕。目前關于抑郁導致衰弱發生的機制尚不明確,可能與二者具有共同的病理生理學基礎有關,如氧化應激、慢性炎癥、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軸失調〔21,22〕等。盡管潛在的生理機制不明確,本研究從抑郁的心理學和社會行為學機制探討其間接通過影響營養不良進而導致衰弱的發生。本研究證實抑郁對營養狀況有正向預測作用,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23~26〕。有抑郁的個體可能會產生更多的負性情緒,導致食欲下降、食物和能量攝入不足〔27〕及飲食習慣的改變〔24〕;同時有抑郁的老年人往往會有久坐不動的生活方式〔6〕,進一步影響了老年人的食欲,導致老年人出現體重下降;既往研究〔28〕也顯示,與無抑郁的老年人相比,有抑郁的老年人對于健康飲食的依從性較差,這些都使營養不良的發生風險增加。此外,抑郁和營養不良間可能存在相同的危險因素,例如經濟狀況差、社會支持缺乏等,使二者間存在相關性〔28〕。
本研究結果顯示,有營養不良風險或有營養不良的老年人衰弱發生風險顯著增高,這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29,30〕。營養不良可能通過以下機制影響衰弱發生發展。首先,營養不良可使老年人身體成分發生改變,如脂肪組織減少和去脂體重下降,導致老年人體重下降及肌肉組織減少等,進而使個體出現疲乏、握力下降、步速減慢及低體力活動等,這些癥狀是老年人身體衰弱的重要表現〔31〕。另外,營養不良可表現為體內多種營養素的缺乏,如血清蛋白、維生素和微量元素等〔11〕。這些營養素在衰弱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如血清蛋白缺乏會影響骨骼和肌肉的健康,發生少肌癥,增加骨折和跌倒風險〔32〕;抗氧化作用的維生素缺乏則無法在減少氧化損傷過程中發揮作用〔33〕。因此提高對社區老年人營養狀況的關注,并定期進行營養篩查,可以有效預防或延緩衰弱的發生。
營養不良在抑郁和衰弱關系之間的中介作用提示,在預防或延緩抑郁患者發生衰弱時,尤其要加強對營養狀況的評估和治療。在無法提供心理干預的初級衛生保健場所,初步篩查發現老年人有抑郁癥狀后,除了積極建議老年人及家屬到設有心理門診的綜合醫院或專科醫院就診外,還要提醒家屬密切關注老年人的營養狀況,預防衰弱的發生。
綜上所述,抑郁可通過心理學、社會行為學等多種機制導致營養不良,而營養不良進而通過生理學方面的機制導致衰弱的發生。本研究僅探討了營養不良在抑郁和衰弱之間的中介作用,而其他抑郁伴隨癥狀如認知障礙、睡眠障礙等可能同樣中介了抑郁和衰弱之間的關系,需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