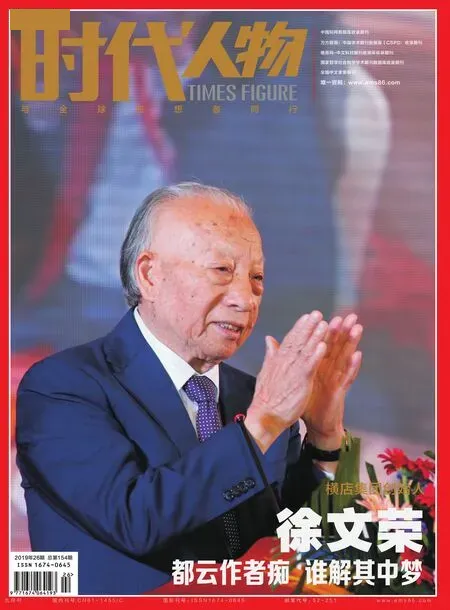論獨裁官對共和國的更新及其限度
——從《論李維》說起
□文|戴龍杰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
獨裁官貌似共和國的天敵,而馬基雅維利則首推獨裁官對于共和國長治久安的重大意義,這種“離經叛道”的論點,在政治策略上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在政治實踐中亦不乏范例作為支撐。就其策略意義而言,馬基雅維利祖述亞里士多德,將共和國類比于人類這樣的有機生命體,出于安全的考慮需要時常改變內在秩序,也即更新[1](P315)。但其迥異之處在于,馬基雅維利關心更“管用”的統治藝術,而非抽象的政治哲學,他贊成:只要共和國出現緊急狀態或重大變革,人民可以授權一人采取行動,也即設立獨裁官,這是共和國利用君權的主要方式[1](P105)。這種對獨裁官的大加贊賞,無疑會讓歷來的共和主義者大驚失色,但深刻地考察其辯護理由,而非在特定偏好驅使下盲目批判,更能客觀地揭示獨裁官與共和國辯證關系的全貌。
數百年來各國共和制在實踐中的紛繁演變,則為理性認識獨裁官的定位提供了正反兩面的參照。一方面,只要馬基雅維利了解民主政治發展史,他就完全可以指出,現代人并沒能找到一個優秀獨裁官的替代者——無論共和國實行何種政體,無論政論家怎樣批駁強大的執行權,國家總要由名稱各異的“首席執行官”來管理[2](P172),并且但凡出現重大危機,這位執行官必有一錘定音的權威,即使在以分權與制衡為政治特色的西方國家,也不乏羅斯福、丘吉爾與戴高樂之例;與此同時,二十世紀臭名昭著的極權主義暴政如納粹政權與斯大林體制,則一再提醒現代人,缺乏合理限度的現代獨裁官將給共和國帶來何等可怕的災難,一個道德敗壞又無限連任的獨裁官,其邪惡遠勝暴君。
歷史污名
“政府必然要么過于強大,危及人民的自由;要么過于軟弱,無法維持自身的生存,一切共和國都有這種內在的致命弱點嗎?[3](P143)”林肯當年在美國內戰時發出的質問,直到今天都沒有過時,其核心論點在于:強大的政府與自由無法在共和國自然兼容。但更準確地說,它是對一個強大以及強勢的政治領袖是否有助于共和國的自由缺乏信心,因為政府的行政權最終都可追溯至該領袖個人的決斷能力上,此人一旦掌權便在整個國家舉足輕重:從羅馬共和國開始,他的典型代表是在緊急關頭根據法律任命、大權獨攬的獨裁官,演進到當代則是經由選舉程序產生、長期執政的,或是根據憲法授權、可在緊急狀態下便宜行事的政治領袖。判斷他們與共和國的關系,首先要從關于國家發展演變的學說史談起。
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國家作為政治共同體常被比之于一個有機的生命體。亞氏將城邦看作自然的產物[4]7,個人和家庭與城邦好比手足與身體的關系[4](P8-9),身體各部分間必須按照一定比例生長,否則必將衰亡,城邦亦同此理[4](P239),特定階層在全國的力量占比可組成民主制、貴族制、君主制及其對應的三個變種政體。亞氏認為,這六種政體水火不容[4](P133-134),隨后提煉出它們共有的專制因素但又不予置評,其中作為專制因素集中體現的獨裁官雛形“aisymnetai”,更是被貶作選舉產生的暴君。及至古羅馬的波里比阿,他總結羅馬共和國政體的歷史變遷,進一步指出:國家同有機體一樣,都會經歷自然的循環,[5](P437)六種政體盡管看似互相對立,卻會在一國之內經歷循環往復的自然演化,所以為了避免政局動蕩,“最好”的政體應同時混合民主制、貴族制與君主制各自的優點[5](P395)。但對于獨裁官在共和國歷史循環中扮演的角色,波里比阿唯秉筆直書其事跡而已,除此以外都是三緘其口、不予置評。后輩對獨裁官的態度深受波里比阿熏陶,比如西塞羅也觀察到波里比阿所說的政體輪回,但認為要預見輪回中的威脅并掌握其方向,獨有偉大公民或神明青睞者才能勝任,而獨裁官是君主制的象征、只會使人民淪為奴隸[6](P69、71),特別是蘇拉——凱撒當政期間的獨裁制,令羅馬完全失去了共和制[7](P69、71);李維則在這個問題上左右為難,一方面,他承認像卡彌盧斯那樣率軍保衛國家、恢復宗教傳統的優秀獨裁官當受人民愛戴[8]209,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忘借人民之口表達強烈的憂懼之情,因為獨裁官權力無限,其身而為人又比權力本身更無情[9](P77、107-109)。總體來看,古羅馬本世代的人們對獨裁官的傾向是:制度上冷落,理論上排斥。

我們不妨這樣推斷,古希臘以來獨裁官之所以背負無數惡名,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增益共和國雖有先例、敗壞共和國亦屢見不鮮,羅馬共和國末期凱撒的所作所為便是典型,他破壞權力平衡后引起的一系列內亂最終把共和國推向帝制。獨裁官的頭銜,從外觀上使人們第一次見到,羅馬有史以來“第一個僭主”實施統治,好像沒有這樣的頭銜凱撒就不可能粉飾自己的僭政。同時,由于劣跡相較之美行,總是更長久地駐足于人們內心,一旦某個獨裁官起了個壞頭,即對共和國投射出長久普遍的陰影,后世便念念不忘獨裁官的暴戾形象,從此對其警惕再三,非迫于無奈必不啟用,甚至刻意不去討論他。再加上設立獨裁官本就是為應急,不可能同執政官、保民官一樣成為常設職務,共和國的權力架構始終沒有認真對待它,這樣一來,也就很難提煉出清晰、穩定的政治教義,以驅使人們相信獨裁官具有特定局勢下更新共和國的獨特作用。
縱然史家有心者如李維,在汗牛充棟的史料里覓得眾多挽救國家于危亡的優秀獨裁官,也還是出于對純粹共和主義的強烈偏好而投鼠忌器。因為從第一任的提圖斯·拉古斯開始,但凡國家深陷內憂外患,獨裁官一經元老院任命即掌全權,人民不得申訴也沒有其他任何幫助(比如兩名執政官當政時,對其中一人不服即可向另一人申訴,既能實現權力制衡也能保護人民),只得認真服從[8](P75-77)。如果沒有六個月的任期限制,沒有元老院預先規定的職責和任務,以及受執政官指定的限制,要想找出獨裁官和一位專制君主的差別,實在太難了[9](P75)。歷史上經由名家前赴后繼的偏好傳承,一代又一代人的口耳相傳,最終生成關于獨裁官的一種固定甚至近乎刻板的印象,這樣看來,前人的憂心忡忡也就情有可原。
更新還是敗壞:獨裁官到底是敵是友?
馬基雅維利說:你們都錯了。
首先,獨裁官的出現與共和國的更新緊密相連。馬基雅維利同波里比阿一樣堅持歷史循環說:同一共和國內,完全可能在歷史的不同階段出現看似截然對立的政體,隨時間推移而彼此轉化。但他對宿命論式的政體循環不感興趣,認為共和國的前途實際上分為三種:中途夭折、被鄰邦征服,或是一種永無止境但有目標的良性循環——返回原初、有益的自我更新[1](P14)。這種更新的動因既非波里比阿篤信不疑的自然規律,亦非普魯塔克或李維念茲在茲的命運,而是機遇,它包括外部事件(如外敵入侵)和內在主動[1](P316)。
外部事件迫使共和國隨機應變,但偶然性太高。馬基雅維利認為,羅馬式的共和國不可能像斯巴達或威尼斯那樣,茍活于自由而狹小的疆域,因為即使不干涉別人也會被別人干涉[1](P260),充滿變數的世界不會總是眷顧共和國,它就不可能總是幸運地走完政體循環全過程。可問題是,李維只給他提供了羅馬共和國這樣一個空前龐大、空前成功的范例,截止到他所存在的近代歐洲,歷史上不再有可供參照的反例,僅僅因為羅馬“多難興邦”,就結果導向地斷言更新未來的共和國也需要借助外敵入侵,失之草率。畢竟從李維的記述來看,羅馬的“多難興邦”實屬意外,有很大的運氣成分甚至所謂神明眷顧,比如卡米盧斯被召回羅馬前,羅馬城堡全靠獻祭給朱諾的鵝群提醒以及馬爾庫斯·曼利烏斯個人的機警,才及時發現并擊退從懸崖悄悄摸上來的高盧人,拋開這種運氣,共和國命運如何將不堪設想[8](P205)。這種機緣能否降臨在疆域相似、處境類同的共和國身上呢?可遇不可求,所以不能由此歸納出普遍適用于未來共和國的道路。耐人尋味的是,馬基雅維利又立刻就拋棄了上述論斷,轉而鼓吹羅馬人化被動為主動的擴張主義,但即使不能稱之為冒險,卻必然產生這種結果:對人民講共和主義,對外邦用帝國主義[1](P261)。不過,馬基雅維利也并沒有一以貫之地推崇對外擴張,比如他在《論李維》第二卷第三十章就指出,法國國王雖有強大的國家,卻要向瑞士納貢,而瑞士共和國存續百年卻并從未對外擴張[1](P302)。
內在主動引起的自我更新,則是更具普遍意義的選擇。它包括規范人們言行的法律,以及樹立良好典范的賢達,前者代表制度的優越,后者仰賴個人的德行[1](P316-317)。但馬基雅維利相信:總的來說,法律所建立的制度會隨時間流逝慢慢被人民遺忘或輕視,最終走向沒落或敗壞,這時就需要一個杰出的公民為其注入活力,所以共和國的兩種內在更新在本質上都要靠個人的力量來實現,他們將以自己的表率,發揮幾乎等同于法律一樣的作用[1](P316-317)。在這群共和國的杰出公民里,獨裁官位列其中,他們應運而生也總是有所作為,何況創設獨裁官這一職位,本身就是共和國制度重大更新——同薩比尼人開戰以及防備三十部族聯盟的需要,第一次催生了羅馬人選舉獨裁官的想法,這在過去沒有先例,它對人民的胸懷和勇氣本就是不小的磨礪。除此以外,獨裁官對彌補共和制度的固有缺陷也有獨到之處。
根據李維的記載,羅馬人向執政官提起的申訴權不得在超過城市一里外適用,所以當公元前460年,執政官普布利斯烏·瓦勒里烏斯為收復失地在城外集合平民武裝時,大家只好聽命,那么以后如果某些別有用心的執政官抓住制度上的漏洞,試圖以此延長自身任期、造成事實上的帝制,共和國就沒有任何辦法,這就讓人們意識到國家需要獨裁官[8](P105)。因為盡管獨裁制下也不存在申訴權,但這樣的嚴苛會平等地適用于獨裁官以外的所有人,包括執政官,而且不同于二十世紀的現代獨裁,古羅馬獨裁官存續的時限有定數,其看似無窮的權力卻不得用于反對人民與共和國,并無條件地優先于執政官,這會讓一切蠢蠢欲動者都聞風喪膽。
按照馬基雅維利的理解,每當共和國在獨裁官的守護下抵擋住外部侵襲和內部腐化,成功地穩固原來的國家制度時,就意味著它穿過坎坷曲折的現狀,重新返回到國家過去的軌道上,最終完成了一次更新。例如,公元前458年執政官彌努基烏斯的軍隊深陷重圍,正在農忙的欽欽納圖斯被元老院委任為獨裁官,他命令所有適齡應征者全副武裝帶上十二根長竿連夜趕到,把長竿豎成柵欄,將敵人團團圍住,使其內外交困[8](P109)。在現存的李維四十五卷羅馬史殘本中,這種卓有成效的反包圍戰術記錄于第三卷第二十八至二十九節處,考慮到它在全書章節的優先位置(李維在書中首度展開共和國軍事行動的各種細節),以及作者一貫刪繁就簡的行文風格(此后再無對類似戰例給予類似篇幅的描寫),可以推定它在共和國軍事史上尚屬首次,其獨創性正符合共和國設立獨裁官的出發點:緊急時刻一人決定勝過多人商議,此人要大權獨攬并能征善戰。這次戰例非常典型地指明,獨裁官在共和國危難之際總是挺身而出,在極短的時間內、盡其所能地調動包括他本人在內的一切智慧和力量,破除國家面臨的各種艱難險阻。
更為重要的是,獨裁制只要運行得當,就是共和政體下以美德教化公民的標桿。當欽欽納圖斯得勝歸來、享受凱旋榮譽后,他在第十六天就交卸了授權六個月的獨裁權,返回田園生活[8](P111)。在這里,獨裁官得到李維罕見的高度贊揚,他極力烘托欽欽納圖斯的不慕名利以針砭時弊,將他視為巨大榮譽和勇敢精神的絕佳范例。半個多世紀后,新任獨裁官卡彌盧斯擊敗高盧人后同樣主動離職,只是元老院請求他繼續守護動蕩的國家,方才作罷[8](P209)。以后四次擔任獨裁官,卡彌盧斯都謹守欽欽納圖斯定下的規矩,這種做法在長久的政治實踐中就逐漸形成共和國的憲法慣例:獨裁官的實際任期并不必然以六個月為限,而是根據國家形勢的具體要求相應地延長或壓縮,并且總的來說傾向于要求獨裁官提前卸任。如此一來,既能保證獨裁官與共和國其他官職的有限任期制實現兼容,又能及時有效地應對各種突發事變,這樣,原初的共和傳統得到了充分尊重,建城以來的統一穩定也得到了堅決維護并且疆域穩步擴大。
誠如馬基雅維利所說,在此過程中,每一個獨裁官都以本人的高度自制發揮著等同于法律的表率作用[1](P318),他們前赴后繼地塑造出有效平衡政治野心與國家穩定的不成文制度。等到共和國末期,蘇拉、凱撒之所以受到西塞羅等共和派的抨擊,正是因為這些政治家受個人野心驅使,破壞了存續百年的優良傳統——強行延長獨裁官任期甚至搞出了終身獨裁。根據林托特的分析,這些末代獨裁官權力之所以如此膨脹,其原因是頻繁的窮兵黷武使國家授權他們長時間率領同一支軍隊,到最后士兵們只效忠于統帥而非祖國,國家暴力機器淪為個人的私產,而這又被公認為是共和國本身走向衰亡的標志[9](P195)。進入二十世紀后的獨裁制,則是在此基礎上變本加厲地賦予單獨一人完整而持續的支配國家全部領域的權力,獨裁制受人唾棄是因為原來的諸多限度被歷史的偶然一一顛覆,而不是因為獨裁官職位本身的惡劣,這一點是有必要澄清的。
防止異化的三重限度:時間、法律、自律
即使獨裁官真的有助于促進共和國的更新,人們不免要問,如何防止這樣的強者為非作歹呢?畢竟根據前面的理解,我們可以想見:個別獨裁官的野蠻行徑極易玷污獨裁官職位本身的意義,導致獨裁官陷入長期的歷史污名,且其特定的名稱與權力外觀也總讓人想起大權獨攬的君主。那么,有效地約束獨裁官使其免于異化,就成為無法回避的重大課題。而通過梳理、歸納李維和馬基雅維利的相關論述,我們可以全面地提煉出防止獨裁官異化的三重限度:時間、法律、自律。
獨裁官的權威需在歷史中形成
自從羅馬人民放逐塔克文以后,帝制下那種世襲罔替的君主權威便不復存在,隨后由選舉產生官職的做法逐漸通行,至于年齡、財產等形式要件之外,受命官職所需滿足的實質要件到底為何,李維的殘卷本語焉不詳,馬基雅維利在《論李維》似乎也有所疏漏。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公元前494年羅馬開啟政治平民化的歷史進程以來,是否出身貴族不再是評定公民層級的絕對標準,本人及其祖先的軍功政績才是他們在公民選舉中贏得支持和擁戴的真正砝碼,甚至貴族也不得不奮發圖強才能與平民齊頭并進[10](P48)。這就意味著,只有在長期的軍事或執政生涯中嶄露頭角、建功立業,才更可能贏得人民的信任并被委以重任。
實際上,在羅馬共和國時期的94位獨裁官中,獨裁官對他們的政治生涯來說,往往只是漫漫征途的里程碑之一。當卸任獨裁官后,他們又會憑借這一期間的優良表現,繼續競逐國家公職[11](P514)。比較典型的例子是,欽欽納圖斯在公元前460年候補執政官,458年臨危受命擔任獨裁官,457年候補執政官,439年又再次出任獨裁官以對付意圖稱王的梅里烏斯,437年擔任獨裁官馬默西努斯的騎兵隊長[12](P39、41、56);而后來當選獨裁官不下五次的卡彌盧斯,最早是在對陣艾奎亞人和沃爾基亞的大戰中一舉成名,他憑借這次戰功和其他榮譽當選為監察官這一極其尊榮的職位,任內又說服未婚男子與戰爭遺孀成親以繁衍城市人口,以此政績出名,其后又兩次當選為保民官,抵御外敵侵擾[13](P38)。
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說,獨裁官首先不是籍籍無名之輩,這些人必定是久經考驗、通過層層篩選而來的能者(元老院與執政官群體中向來人才濟濟),如此方能達至共和國權力的頂峰,同時顧及到將來在共和國的聲譽和歷史地位,他們通常不會偏離原來的制度軌道自行其是,這是約束獨裁官的第一重限度。
獨裁官由法律創設,亦需遵守法律
馬基雅維利推崇獨裁官,但不認為共和國有法外之地[1](P139)。在“大權獨攬”這種權力外觀下,獨裁官仍然受到憲法體制下諸多力量的制約,具體包括:他在財政上依賴元老院撥款、沒有針對公民的司法權、不得主動對外開戰、一切行動全靠民意支持、任期有限等等[14](P128)。如果獨裁官違反法律,獨斷專行,就會面臨控告、被迫辭職——根據李維的記載,公元前363年,盧基烏斯·曼利烏斯因舉行釘釘儀式而被推舉為獨裁官,但在履職完畢后他又強行征兵,準備同赫爾尼克人開戰,不應征入伍者要受到嚴厲懲罰甚至鞭刑,最后在群情激憤下被迫辭職,次年保民官對他提出控告[8](P269)。這就說明,突破法定權限的獨裁官要付出應有的代價。
隨著國家版圖的擴張,特別是第二次布匿戰爭以后,盡管獨裁官開始由人民選舉產生[15](P49),從程序上增強了該職位的正當性,然而單獨一人掌握全部國家權力的局面已不足以應對復雜性急劇增加的政治事務,此時允許獨裁制下執政官、裁判官等人繼續行使之前的職權更加符合現實需要;相應地,獨裁官就愈發受到共和國官僚體制的整體制約,一個巨大變化是:保民官開始享有對獨裁官決定的否決權,伴隨而來的,是獨裁官制度的沒落[16](P298)。
因此,不光羅馬本世代人對獨裁官是杞人憂天,近代以來對獨裁官的諸多描摹都不符合實際情況:盧梭推崇獨裁制,認為獨裁官除不能立法以外無所不能[17](P151);卡爾·施密特強調,獨裁官不受法律約束且有操縱生死的大權[18](P2);而波斯納則干脆直接把羅馬獨裁官同希特勒、斯大林這些現代獨裁者相提并論[[]](P68)。然而正如前述,獨裁官在法律上要受到諸多限制,事實上也并沒有后世所想象的那么不可一世,馬基雅維利更是反復強調,公民若要侵害他人就必須家財萬貫、黨羽如云,而這在一個遵守法紀的共和國是不可能的,所以即使當選獨裁官,不能也不該做損害國家的事,加上其任期有限、人民也并未腐敗,所以他不可能胡作非為[1](P109)。至于共和國后期,為了擴張領土、積聚財富而使軍隊長期處于同一獨裁官指揮下,的確變相助長了獨裁官專斷獨行的氣焰,但這是共和國本身的野心和墮落所致,最后也吞噬了它本身,卻并不能歸結于獨裁官之惡,因為任何一個人處在當時的局勢下,即使不做獨裁官也照樣能黃袍加身。
普遍的公民美德塑造自律的獨裁官
良好的社會風氣,孕育出懂得節制權欲的獨裁官。有別于《君主論》中強烈的非道德傾向,馬基雅維利在《論李維》中出人意料地對共和國的公民道德不吝溢美之詞,而這明顯受到李維《自建城以來》里道德說教的影響。他引述李維對獨裁官欽欽納圖斯事跡熠熠生輝的描述,指出像欽欽納圖斯這樣優秀而稱職的人,只需四個居格拉的土地,就足以養活他——公民以自己的勝利為羅馬帶來財富,同時又保持著自己的貧窮[1](P409-410)。
這種安貧樂道的情況絕非個例,它所折射出的是共和國時期整個羅馬社會普遍盛行的重視榮譽、熱愛國家、節制欲望的公民美德。目睹奧古斯都時代整個國家的道德滑坡,李維曾不無艷羨地追思共和國時代:財富愈少,貪欲愈少,而清貧和節儉竟在那個時代如此長久,從未有哪個國家更偉大,更虔誠,更富有良好的范例[8](P5)。上述評價雖有夸張的嫌疑,卻不乏來自其他史家的佐證。例如,生卒年稍早于李維的撒路斯特,就高度評價共和國時代的公民美德:人們渴求榮譽,卻不吝財富……其良好品質出自本性而非法律,出征即一往無前、悍不畏死,從政則恪守公正、溫和寬容[[]](P14)。帝國時代的塔西佗也坦承,“古代”治理當屬輝煌歷史無疑,當時的羅馬人作為勇氣和聲望的典范名垂后世,而權勢或財富則不在其內[[]](P242)。
一言以蔽之,追求公益、節制私欲是當時深入人心的社會風尚,每個特定的獨裁官都生于斯長于斯,所受的熏陶較之其他公民并沒有差別。那么當他們上臺后,謹慎而非武斷地運用手中的權柄、引領國家航向的同時又保持制度框架的穩定,便是自然而然的慣常做法,因為公正自律的觀念早已融入他們的性格。這種社會環境的培育,是對獨裁官最潛移默化也最堅強有力的約束。
無論對獨裁官秉持何種觀念,他所代表的權力高度集中都是共和國緊急時刻渡過危機的應有之義,從歷史上看這種必然性無法回避。誠如馬基雅維利所言,國家不會永遠在對內或對外的相安無事中獨善其身,局勢異常時須相應地授予突破常規的權力進行針對處理,其集中式的權力外觀應合乎理性地視為共和國必要的自我防御機制或更新方式,而非自我異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共和國不會也不能完全排斥專制因素。以此為著眼點,現代法治國的任務是實現對上述專制因素的有效規范與利用,在更新國家面貌與穩定既有秩序間取得妥善的平衡,以確保常態政治與特殊情勢下國家都能在制度軌道上合理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