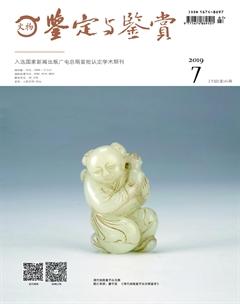淺析高梁河之戰
豆中浩
摘 要:終遼一代,漢官在其政權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高梁河之戰前,遼政權自遼世宗與遼穆宗兩朝陷入中衰危局后,政局不穩,國力衰退。遼景宗繼位后,推行了封建化改革,重用了一批漢族的文臣、良將,積極實施漢化政策,為遼王朝中興做了充足準備。高梁河之戰后,遼政權挫敗了宋政權收復燕云十六州的戰略企圖,國力日益強盛。漢官集團進入遼政權決策機構,積極推進封建化改革,促進了北方的開發和民族大融合。宋、遼高梁河之戰的研究對于了解遼朝漢官集團有重要意義。文章以此戰為例,淺析漢官集團在遼政權的作用。
關鍵詞:高梁河之戰;遼政權;漢官集團
高梁河之戰是宋、遼兩國因爭奪燕云十六州而發生的局部戰爭,此戰亦為兩國第一次正面交鋒。遼國占領的燕云十六州,不僅為其政權提供大量的人口和財富,也提供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天然屏障。因為燕云地區易守難攻的地理優勢,宋王朝在建立之初即希望收復燕云十六州。漆俠指出:“一些強大的王朝如漢唐,其所以能夠同草原民族一爭雄長,一是以長城天險為依托,阻御草原民族牧騎南下,以保障中原地區的安全;二是據有一片草原,繁衍馬匹,編組為騎兵,主動出擊,以機動對機動,以能夠支持長期戰爭的民力為基礎,終于戰勝對手,成為國勢強大之王朝。宋代立國不僅沒有象漢唐那樣具備上述兩個條件,而且長城天險又被契丹占有,國都沐京立處平野,直接暴露在契丹牧騎威脅之下。”[1]對于高梁河之戰的前后過程,宋、遼兩國的史書有不同的記述。仔細研讀史料可知,《遼史》記載更為詳盡。
高梁河之戰,宋軍慘敗。宋人在記述敗因時,竭力避諱宋太宗的指揮不當。宋神宗曾云:“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所奪,從人富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意以簡瘡發云。”[2]學界對于高梁河之戰的論述頗豐,此不贅附。結合史料從遼政權的角度來分析高梁河之戰,漢官集團在此戰中發揮巨大作用。
《遼史》載:“宋兵取河東,侵燕,五院詳穩奚底,統軍蕭討古等敗歸,宋兵圍城,招脅甚急,人懷二心。隆運登城,日夜守御。援軍至,圍解。及戰高梁河,宋兵敗走,隆運邀擊,又破之。”[3]1421-1422耶律隆運即韓德讓,其父韓匡嗣,其祖父韓知古,長期仕于遼朝。高梁河之戰發生時,韓德讓代父為遼留守南京。宋軍圍城,情勢危急,韓德讓日夜守衛遼南京,為遼援軍贏得了時間,堅守城池是擊敗宋軍的重要條件之一。康延壽,康默記之孫。“宋人攻南京,諸將既成列,延壽獨奮擊陣前,敵逐大潰。”[3]1356高梁河之戰前后,馬得臣、劉景這些漢官輔佐韓德讓共同治理南京城。馬得臣,“乾亨初,宋師屢犯邊,命南京副留守”[3]1409。耶律阿保機建立契丹后,網羅大批有才干的漢人為其出謀劃策,對漢族人才求賢若渴。自遼太祖至遼景宗,在漢人協助和獻策下,遼政權的封建化進程不斷加快,結束皇位相爭的不利局面,由世選制向父子相傳制過渡,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爭奪趨于平靜,國力強盛,遼國有足夠的實力與中原政權相抗衡。
1 漢官集團的來源
1.1 戰爭掠奪的漢人
契丹建國前后,本國統治者在依附中原王朝或封建割據的漢政權時,也屢次南下,攻城略地,獲取大量勞動力。被掠奪的漢人不乏有飽學之士,他們把中原地區的儒家文化及先進的治國理念傳播到遼國。例如,韓知古、康默記、王繼忠,先后被劫掠到遼國。韓知古,薊州玉田人,善謀有識量。“太祖平薊時,知古六歲,為淳欽皇后兄欲穩所得。后來嬪,知古從焉,未得省見。”[3]1359韓知古深受遼太祖信任,被授予要職。“總知漢兒司事,兼主諸國禮儀”[3]1359,完善遼政權的禮儀、法度,教化于民,功績卓然。康默記,薊州人,“少為薊州衙校,太祖侵薊州得之,愛其材,隸麾下”[3]1356。這些早期仕遼的漢族官僚對于遼國初期制度建設有重要貢獻,同時擴大了漢族官員在遼政權中的影響力,為漢官集團的發展奠定基礎。
1.2 劃界而得的漢人
燕云十六州位于中原王朝北部,以農業生產為主體,漢族人口占絕對優勢,儒家文化為當地主流思想。自后晉割地給遼后,該處的漢人世家歸入遼國。宋人夏竦曾言:“自幽薊陷敵之余,晉季蒙塵之后,中國器度工巧、衣冠士族,多為犬戎所有。”[4]15以韓、劉、馬、趙為代表的漢族世家大族陷于遼,昌盛于遼一代。韓德讓,《遼史》有云,“重厚有智略,明治體,喜建功立事”,堅守南京,扶持圣宗,率軍伐宋。蕭太后贊曰:“進賢輔政,真大臣之職。”[3]1422趙延壽,與父俱降遼,勤于軍事,多有建樹。太宗對其曾曰,“漢兵皆爾所有,爾宜親往撫慰”[3]1376,深受太宗器重。遼國接管燕云十六州后,為了便于管理當地漢族,任用大量漢族官員。“梁援祖上梁文規”,五代時“官至吏部尚書”。漢族官員施展才能治理燕云十六州,同時也借助遼統治者的信任,培養其家族勢力。遼統治者借助漢人世家治理燕云十六州,同時也在吸收和學習儒家文化。其結果是遼朝封建化程度深化,漢官集團日益壯大和發展。這一過程是相互作用的。
1.3 科舉入仕
高梁河之戰后,宋、遼兩國爆發了幾場短暫的戰爭。隨著《澶淵之盟》的簽訂,終遼一代,兩國沒有發生大規模戰爭。遼圣宗統和六年(988)的“詔開貢舉”使遼朝科舉制逐漸成為全國范圍的制度。據學者統計,“遼代進士目前能確知姓名者205名,其中漢人200名,非漢族進士5名”[5]。漢族士人幾乎代表整個遼代士人。姚景行,“重熙五年,擢進士乙科”[3]1543。玉田韓氏家族是遼政權中具有顯赫地位的世家大族,韓知古為遼國開國功臣之一,仕遼為中書令。玉田韓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在第三代韓德讓時期達到頂峰,“盡管到遼代后期,韓氏家族的勢力呈削弱狀態,但終遼之世,其勢力均是不容忽視的,后期仍是具有一定影響的世家大族”。
2 高梁河之戰前漢官集團發展
遼太祖至遼景宗前期,遼政權中保守派和改革派相互爭斗,遼統治集團對于漢人官僚抱有戒心,漢人不擔任重要的職位,即“軍國大計,漢人不與”[3]1588,但給予足夠的重視。漢官參與到遼政權制度建設中,盧文進“又教契丹以中國”,主要的漢族官員有韓延徽、韓知古等。“太祖初元,庶事草創,凡營都邑,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3]1588韓延徽修筑宮殿,制定禮法,將中原文化的名物典章帶入契丹政治體系,加快遼政權封建化的步伐。韓知古總知漢兒司事,兼主諸國禮儀,成為遼太祖佐命功臣之一,在遼國家制度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早期仕遼的漢族官僚雖未進入遼決策機構,卻為后世漢族官僚的發展壯大奠定基礎。
3 高梁河之戰后漢官集團發展
遼景宗后期至遼興宗,遼政權中改革派占據主導位置,漢族官僚的地位進一步提高。受到重用的漢族官僚已開始進入遼政權的決策機構,擔任要職。遼代漢族官僚集團中,韓德讓地位最為顯赫。《遼史·耶律隆運傳》:“重厚有智略,明治體,喜建功立事。”“在統和間位兼將相,其克敵致勝,進賢輔國,功業茂矣。”[3]1422-1428韓德讓地位顯赫,位極人臣。韓德讓的家族成員大都身居高位,弟弟德威,西南面招討使,“賜劍許便宜行事,領突呂不、迭剌二虬軍”[3]1423;侄兒制心,“太平(1021—1031)年中,歷中京留守,惕隱,南京留守,徙王燕,遷南院大王”[3]1425。遼中后期是遼封建地主、牧主階級快速發展時期,也是漢族和契丹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融合的時期。
綜上所述,漢官集團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與遼朝統治集團合作,共同實現遼國強盛,使遼國快速脫離原始游牧社會形態,社會面貌煥然一新,封建化步伐加快,漢官集團在抵御外來勢力、維護皇權、促進社會穩定和發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客觀上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
參考文獻
[1]漆俠.宋太宗第一次伐遼——高梁河之戰—宋遼戰爭研究之一[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3):1-9.
[2](宋)王铚.默記:卷中[M].北京:中華書局,1981:20.
[3](元)脫脫.遼史[M.]北京:中華書局,2016.
[4](宋)夏辣.文莊集:卷13:計北寇[M].清乾隆抄本:15.
[5]蔣金玲.遼代漢族士人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