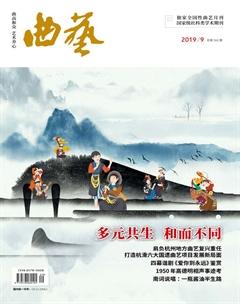融媒時代少數民族曲藝的跨媒介傳播探析
杜曉杰
黨的十九大明確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也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必然要求現實文化建設能夠向著滿足絕大多數人民文化需求的方向努力,也必然要求具有大眾性的文藝形式能夠承擔起更大的責任。在這種形勢下,民族民間曲藝作為扎根基層民眾生活的大眾文藝,理應重新進入大眾文化消費的核心體系,在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發揮應有的職能。而少數民族曲藝作為推動我國多民族國家認同、彰顯多民族國家文化自信的重要載體,更應引起我們的關注。
在新時代語境中,少數民族曲藝要更好地發揮自己作為一般文化消費和民族文化統戰、民族國家認同的職能,就必須與新時代融媒體發展的趨勢實現無縫對接,借助新媒體提升自己的傳播力,在跨媒介傳播中激活自身藝術場域,全面介入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
一、媒介變遷與少數民族曲藝的傳播危機
少數民族曲藝的衰落是當代文化生態中不爭的事實,不僅活躍在媒體上的曲藝形式以漢族的相聲為主,即便在少數民族群體內部,傳統的民族曲藝也在萎縮。探析少數民族曲藝衰落的原因,流行文藝的沖擊、經濟社會的轉型等固然是值得注意的方面,但歸根結底,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媒介變遷在這一過程中發揮的重要影響。換句話說,少數民族曲藝的傳承發展面臨危機,而造成這一危機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媒介環境的變革。
整體而言,人類文化經歷了口頭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和數字傳播四大階段。伴隨互聯網數字體系的不斷完備與鋪展,當代人無疑進入了“數字化生存”的時代。數字傳播的最根本變革,就是從“人制造信息”變為“信息制造人”。由于傳播的便捷性和門檻低,數字傳播時代直接帶來的是信息的爆炸乃至擁堵。尤其是隨著移動終端的大面積普及,人無時無刻不處于信息的圍堵之中,以至于出現“你認為你想看到的真的是自己想看到的”的錯覺。在這樣一個時代,一組信息是否能為人所知,端賴信息是否進入了數字傳播的序列,是否能成為算法推薦的對象。而這兩點,恰恰是少數民族曲藝所欠缺的。
在“兩微一抖”以及各大主流視頻網站搜索曲藝資源,涉及少數民族曲藝的資源不僅數量極少,僅有的一些視頻資源播放量和評論量也低得驚人。而且,存在于數字平臺的少數民族曲藝資源,絕大部分又都是少數民族所在地舉行文藝節目的視頻錄制片段,質量粗糙,形式也較為老舊,完全不符合數字傳播時代對傳播內容的基本要求,被邊緣化也是自然的結果。
從少數民族內部來看,民族曲藝的傳承危機一直存在,不僅傳承人隊伍逐漸縮小,本民族的受眾群體也有所流失。從外部社會層面來看,由于表演語言、形式的特殊性,再加上缺乏現代性技術支持——如短視頻拍攝、字幕、特效等,致使少數民族曲藝無法對外有效傳播,失去了拓展受眾的機能。在內外交困的境地里,少數民族曲藝幾乎成為了傳播孤島,在內卷化的拉墜下生存狀態慢慢惡化。
因此,少數民族曲藝的發展困境,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在媒介變遷中實現內容遷移。要真正解決少數民族曲藝的傳承與發展問題,必須從傳播力重振的角度入手,將少數民族曲藝重新納入當代文化傳播的大體系,助力其實現跨媒介傳播。
二、融媒時代少數民族曲藝的跨媒介傳播策略
在數字技術的強力重塑下,融媒時代的信息接受呈現碎片化、話題性的特點。一方面,為了契合當代信息受眾高強度的工作生活,融媒時代的信息實現了全覆蓋,受眾隨時隨地可以接收移動終端發送的信息。為了不影響受眾工作生活,搶占受眾的閑暇時間,信息的傳播與接受必然呈現碎片化的特征。另一方面,信息爆炸所帶來的信息擁堵,使得信息脫穎而出的難度不斷提高,沒有話題性或“爆點”的信息難以通過大數據算法的遴選推送到用戶面前。所以,短小精悍的話題信息,成為當下信息傳播的主要內容和形式。要介入今天的融媒傳播,少數民族曲藝在傳播理念、傳播內容和傳播手段上都必須進行取舍性的調整,才能實現有效的跨媒介傳播。
首先,在傳播理念上,需要實現從大眾傳播向“表達共同體”傳播的轉變,以適應分眾社會受眾分層的現實。
作為發端于民間的藝術形式,曲藝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是極具“大眾性”①的。尤其是少數民族曲藝,一般與民族創世神話述說、民族歷史文化知識傳遞等功能息息相關,歷來是面向民族群體的絕大部分人群進行說唱的。如壯族蜂鼓的傳統曲目《莫一大王》、瑤族盤王大歌的傳統曲目《唱盤王》《唱魯班》、毛南族排見的傳統曲目《創世歌》等,都是典型代表。少數民族曲藝衰落一個很大的原因也是其大眾性正在收縮,受眾群體在流失。但是,若因此將重回之前層面的“大眾性”作為振興少數民族曲藝的目標,則無異于強人所難。
隨著移動終端的大面積普及和大數據算法的日益完備,一個審美消費的分眾社會已然成型。分眾社會的審美特點,就是審美取向的細分化。原本受到市場經濟沖擊的一體化審美體系,在數字傳播時代進一步土崩瓦解。在移動終端和算法技術的宰治下,受眾的審美日益窄化、固化,大眾性的審美向“表達共同體”的審美遷移。所謂“表達共同體”,是“以新媒體作為一種平臺和載體”,在“價值取向上趨同”“話語體系上”相似的群體②,“粉絲”文化便是其最直接的表征。在表達共同體時代,受眾的偏好集中在某一領域,愿意為自己喜愛的對象花費時間、精力和金錢,對自己不喜歡的對象則熟視無睹。在這樣一個時代,少數民族曲藝的傳承與發展也必須充分認知“表達共同體”理念的確立對大眾審美接受的影響,在傳播受眾的遴定、傳播內容的生產、傳播平臺的選取、傳播手段的整合、傳播效果的評估等方面進行合理的考量。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樣:“我們曾經一直習慣以年齡段劃分人群,如八〇后、九〇后,但到了〇〇后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他們的不同。社會越來越多元,圈子的劃分越來越多、越來越細。此時人群的劃分已從縱向轉為橫向,綜合了興趣、出身、地域等多種因素。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里會有更加廣闊的消費市場,當整個蛋糕越來越大時,每一個小眾的人群也將擁有越來越大的消費能力。”③對少數民族曲藝感興趣的受眾,除了少數民族成員外,還有對傳統文化保有熱情、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保有警覺性的民眾和研究人員。這些人是少數民族曲藝傳播的核心受眾群體,總結這一“表達共同體”的審美需求,從而在傳播內容和手段上進行精準調整,其實就能解決眼下少數民族曲藝的傳承與發展困境。若仍一味強調曲藝的大眾性,要求少數民族曲藝重新成為民族群體文化生活的核心,則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少數民族曲藝的生境。
其次,在傳播內容上,要繼承少數民族曲藝的優秀歷史資源,同時面向新時代的社會生活進行創作,不斷擴充少數民族曲藝的作品儲備,為少數民族曲藝的跨媒介傳播提供豐富的內容支撐。
一方面,要固本培元,加強對少數民族曲藝資源的搜集與整理,不斷擴充少數民族曲藝的內容矩陣,讓傳播受眾深切感知經過歷史沉淀的少數民族曲藝的魅力。少數民族曲藝與少數民族文化關系密切,其經典曲目承載著少數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在藝術上有恒久的感人魅力,是新時代曲藝跨媒介傳播的重要內容。融媒時代的受眾以八〇后、九〇后、〇〇后為主,這些群體雖然極度張揚個性,在審美上求新求變,但對經典的傳統文化也保持著強大的熱情。《經典詠流傳》《國家寶藏》《我在故宮修文物》等綜藝節目、影視節目的熱播,就是典型的例證。抖音上一些傳統曲藝的自媒體號經常發布傳統曲藝節目的片段,從視頻下的留言評論不難發現,大量的年輕人群體被曲藝這一看似“老舊”的藝術形式吸引,深受觸動。目前,少數民族曲藝面臨的一大傳播難題就是傳播內容的匱乏。相較于相聲、數來寶、大鼓等漢民族曲藝,少數民族曲藝的傳統曲目保存與傳承狀況不容樂觀,大量經典曲目已經或瀕臨失傳。少數民族曲藝傳統曲目蘊含著豐厚的少數民族文化,是少數民族先民對世界、人生的審美認知匯總,在藝術形式上也較為成熟,更能引起社會受眾的好奇心與關注度。只有盡可能全面地搜集與整理少數民族曲藝傳統曲目,才能為少數民族曲藝在新時代的跨媒介傳播奠定堅實的基礎。
另一方面,要枝繁葉茂,除了搜集與整理傳統曲目,還應該充分利用少數民族曲藝的藝術形式,面向新時代的社會生活,創編出與當代生活密切相關的新作品,拉近與傳播受眾的接受和審美距離。上文曾提到,融媒時代的信息接受具有話題性的特點,制造話題是推動傳播速度和效率的重要手段。而在話題制造方面,內容與形式的反差性恰恰是最便捷有效的途徑。少數民族曲藝一般都是用較為古老的民族樂器進行伴奏、以陌生化的民族語言和唱腔進行表演,這樣的藝術形式配上當代生活的內容,無疑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很容易成為跨媒介傳播的“爆點”。更何況,“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藝”“文章合為時而著”,文藝的發展只有與社會歷史的當代進展密切相關,才能附著在經濟社會變革的體系之上,不至于被時代拋棄。
回顧我國少數民族曲藝的發展,其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期內繁盛蓬勃的重要原因,就是創作了一大批與社會現實緊密相連的新曲藝。如壯族的末倫新編創了《懷念周總理》《揮淚舉旗又長征》等作品,瑤族的盤王大歌新編創了《計劃生育好》,苗族的果哈新編創了《赤腳醫生斗鬼師》等。這些新作品反映了不同時期的社會現實生活,與黨和國家、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成為了“表達共同體”的重要載體,以曲藝的形式唱出了人民的心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藝術形式。“無論哪一種民族民間藝術,如果只停留在一個水平上,墨守成規,沒有變化,不能隨著時代的演進而發展,那么,它就會在傳承中失去生機與活力,甚至遭到淘汰。”④時移世易,今天的少數民族曲藝也必須打破題材狹窄的桎梏,貼近生活,擁抱生活,在與偉大的現實生活的親密互動中催生出屬于新時代的新作品。
最后,在傳播手段上,要高度重視跨媒介傳播的“跨”媒介性,積極向當下占據強勢話語權的各大眾媒體平臺滲透,盡可能提高少數民族曲藝的的曝光率和“可見度”。
消費社會是“注意力”經濟的社會,一件商品是否進入消費者的視野并被消費者注意到,關系商品銷售的成敗。在信息擁堵的數字媒介時代,同樣存在這樣的注意力定律。當少數民族曲藝未能以相當的頻次出現在各大傳播媒介和平臺之上時,就無法被目標受眾和潛在受眾注意到,自然也無從談起傳播效果。在曲藝的跨媒介傳播方面,相聲是較為成功的典范。綜藝節目《相聲有新人》在電視和網絡上的熱播,直接帶動了小劇場相聲市場的走紅。⑤而網絡、短視頻APP在推動某些相聲偶像的發展方面,也扮演著居功至偉的角色。但是,直到如今,少數民族曲藝尚沒有一個主題性的節目品牌,在電視、電影、網絡、“兩微一抖”APP等平臺和媒介上的出現頻次也極為有限,不僅未能介入流行文藝的傳播機制,更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跨”媒介生存。
其實,包括少數民族曲藝在內的傳統曲藝,本身就具有短小精悍、即興互動等特征,與數字媒介時代信息傳播、接受的特征正相匹配,是跨媒介傳播的絕佳內容。少數民族曲藝的經典曲目,都有一些頗具代表性的片段,長者三五分鐘,短者一兩分鐘,正適合當下短視頻APP的時間容量。少數民族曲藝若能充分利用新媒體平臺的傳播規律,將經典曲目以傳統或創新的手段遷移至新媒體平臺,就必定能在目標受眾群體中產生有“爆點”的傳播效果,并借助流行文藝和跨媒介傳播的傳播特性,不斷延展受眾群體,從而實現“生活化保護”的目標。
三、融媒時代少數民族曲藝跨媒介傳播的價值和意義
對一個多民族國家來說,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從來不僅僅是一項文化工作,更是與多民族國家認同的政治統戰工作緊密相關的。社會主義發展進入新時代,除了經濟上的表征外,政治上的一大表征就是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構建,文化上的一大表征就是文化自信的不斷凸顯。少數民族曲藝的跨媒介傳播,正可以從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構建和文化自信彰顯的層面助力新時代的發展。
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層面上說,少數民族曲藝的跨媒介傳播從內部激活了少數民族曲藝的場域體系,豐富了少數民族文化的活態傳承,從文藝層面推動了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將少數民族曲藝納入跨媒介傳播的數字傳播體系,從根本上提振少數民族曲藝的場域自立能力,對彰顯新時代社會主義中國處理民族文化藝術問題的決心和魄力、進一步提升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建構,都有著重要的政治和戰略意義。對包括少數民族曲藝在內的少數民族文化藝術的保護與發展問題,只有上升到民族命運共同體建構的層面進行審視,才能真正意識到其價值和重要性,也才能制定更具切實性和針對性的方針政策。
從文化自信彰顯的層面上說,少數民族曲藝的跨媒介傳播踐行著講好中國故事的時代使命,弘揚了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藝術傳統,傳播了中華文藝的動人魅力。系統而全面地加強對少數民族曲藝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并將經典曲目納入跨媒介的數字化傳播體系之中,讓更多的中華兒女領略少數民族曲藝的風采與神韻,無疑是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大力弘揚;而在跨媒介傳播的數字化時代,借助少數民族曲藝的傳統藝術形式,謳歌新時代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新成績和在這一過程中涌現的新人新事,對在后現代語境中面向全球講述當代中國、建構美麗中國的國際形象,同樣有著不容小覷的重要意義。
新時代是文化自信的時代,是民族命運共同體建構的時代,也是媒體融合不斷向縱深發展的時代。作為少數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少數民族曲藝不僅有著寶貴的文化、藝術價值,更是新時代文化自信確立和民族命運共同體建構的重要參與力量。少數民族曲藝要參與這一偉大進程,就必須緊跟新時代媒體融合的趨勢,通過深挖經典與編創新作,借助跨媒介傳播的強大輻射力,重振自身藝術場域,在新時代的文藝繁榮中實現活態的保護與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