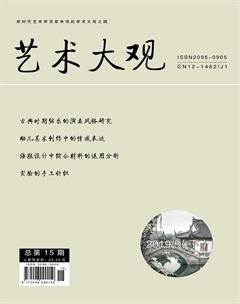淺談古風文化中的道學文化
梁溱玥?劉智峰
摘要:“古風”一詞的原始釋義是指古人質樸淳古的習尚、氣度和文風,而今卻有了更為寬泛的定義。在現代轟轟烈烈的文化浪潮中,以傳統文化為基調,結合中國古典詩詞歌賦等,形成的比較完備的音樂、文學、繪畫等藝術形式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我姑且將它們統稱為“古風文化”,因為“文化”這個詞含義廣泛,能較好地涵蓋這一藝術派別的所有內容,而且它的確能夠被稱為一種新型的文化,的確是大眾的精神產物,的確對社會意識形態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
然而古風圈并不只是年輕一輩的專屬領域,古風也并不只是年輕一輩的娛樂選擇,畢竟20世紀金庸與古龍的武俠小說,至今還受到中年人的喜愛。擴大了說,古風文化的興起可上溯到那個時代,只是后續一直沒有得到許多發展而已。隨著如今古風在藝術領域的擴展,又隨著網絡自媒體的蒸蒸日上,它的內容、形式、風格逐漸定型,展現出了一些趨同的特征,即我在本文主要想談論的問題:它與道學文化的關系。
關鍵詞:古風文化;道學文化;文化發展
一、古風文化里的道學色彩
眾所周知的是,儒學在我國封建歷史上長期占有正統地位,是中華民族精神品格的主要來源,對中華民族有著最為深遠的影響。我們的一言一行、道德觀念、價值觀念都植根于此。因而按理來論,不管是出于對古代背景的還原,還是內心理念的驅使,古風文化中都應有儒家深深的烙印。
事實卻不盡其然。我并未在古風歌曲、古風小說、古風繪畫里找到太多反映積極入仕、崇尚仁禮、學優則仕等主題思想的作品,甚至類似儒士的角色也創作得很少。例如,古風小說喜歡寫仙俠故事,主人公或擁有仗劍走天涯的俠客精神或有名士的仙風道骨,且道長這一形象絕對比儒士這一形象出現的多。就算是非背景架空的故事,有天子,有王侯將相,亦有布衣平民的世界里,寫瀟灑王侯或風流俠客的也比寫儒生學子的多。再者,古風繪畫中,除卻描繪皇家風云的,以道士降妖或行走江湖為主題的漫畫比比皆是。長發披散、豐神俊朗,或持簫,或佩劍,或撫琴的角色也更為人喜歡。雖然自有正史以來至清朝之前,華夏男子都是束發的,只有在魏晉時期出現過一些由于不滿世俗而放蕩不羈的文人而已。由此看來,作者們為了擺脫史書典籍此類“貴族文學”對古代真實社會的限定,采用架空手法,自行設定背景;通過變更衣冠品貌,自行改造審美,以符合現代人對古人的幻想。經過改造后的古風文化,便不是對古代社會的還原,而成了對現代人構想的表現。這種構想,或與華夏民族意識中注入的道學思維有一定相關性。
當然,并不排除儒家思想在古風文化中留有痕跡,但這種痕跡并不與道學色彩相沖突,因為道學色彩更多充當的是道具、布景、演員配置等“拍攝手段”,儒家精神的痕跡則更多地體現在角色本身的性格和理想上,其源于植根于作者內心的民族素養,如:愛國、仁愛、忠孝、濟世之志等。作為先秦諸子中影響力最大的兩家,道家與儒家互相吸納。外儒內道是我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特點,正如林語堂所說:“道家及儒家是中國人靈魂的兩面。”因此事實上,在古風文化中,二者都不可避免地得到了展現。
文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層原因。文化發展的動因來源于人類的精神,文化產品乃是人類心靈智慧之光的外在形式。道家文化和儒家不同,它的學說是從人體本身的修煉工程中體驗出 來的,認為人身是一個“小宇宙”,是自然界 “大宇宙”的縮影,人體和宇宙的運行規律既可治身,又可治國,因而是一種天人同構、身國一理、取法自然的文化。幾千年來,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既相互分立又相互補充,形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道學文化中既蘊藏著死而復生的活力,又具有包羅萬象、海納百川的品格。古風文藝作品中,與道學最有相關性的是仙俠類作品。此類作品構建修仙、妖鬼等古代架空世界,以法術、劍術等為道具展開故事,本就與道教所主張的頗有淵源。道教主張修行,包含有符咒、驅邪、伏魔、降妖、消災、兵法、神仙術、辟谷等術法,作者們爭相效仿將此賦予角色,創造出道家理論中的修真界。道學滲透在古風作品里,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這一點都是不可否認的。
二、現代人的心理
有人說古風文化的興起是源于現代人對古代世界的一種猜想(或念想),每一段古風又是一個故事,讓人在浮躁的現代社會中尋求一片寧靜的空間。還有人說古風文學的興起,是現代人的覺醒,也是心靈深處的回歸。這樣的評價沒有錯。我想古風文化的興起,是因為中國人一直都有一種崇古的情懷,起先可能是出于對禮法的遵循,到后世應該就演變成了一種文化自覺。正如一位碩士研究生的論文中所說:“二十一世紀,伴隨民眾民族意識和文化本位意識的覺醒而產生的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對本土文化,高度一致的共尊共信之心,使新文化運動之后國人對古代文化的景仰復燃成為必然。
然而,古風文化的興起并不必然導致其與道學文化產生瓜葛,這應從社會層面分析。哲學上闡釋文化與政治經濟的辯證關系時說道,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經濟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反作用于一定的經濟政治。就如二十世紀初期因為戰爭、工業化節奏、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現代主義文學流派興起,集中反映了人們的緊張、焦躁、失望和精神困惑一樣,古風文化中道學色彩的出現亦與社會心理有一定的因果關系。
知乎上有人評道:“古風就像一個容器,裝了很多現代社會無處安放的東西。這個詞里面,古是逃避今用的。”邵燕君老師也在《“正能量”是網絡文學的“正常態”》一文中分析道“網絡文學發展的這些年,中國正處于社會結構和價值形態的重大轉型期。”社會發展和科技發展使得人與人之間生存空間的競爭不斷加劇,同時也加劇了社會生存環境的不穩定性。曾看過一篇文章,作者寫道中產階級的焦慮來源于他們社會地位的不穩定。對于已入職人群來說,大多數人經受不住一場重大疾病的打擊,就業崗位的減少使他們擔憂失業,巨大的教育支出等使他們小心翼翼生活。對于在校人群來說,學歷是他們日后謀生的敲門磚,甚至是跨越階層的跳板,學業上的競爭亦是青年人的常態。其次,現代人“自我主義”不斷滋長,對自身情感和生活品質的關注加重了焦慮,迫切需要精神出口。此時,埋藏在精神血脈里的道家思維被喚醒,既憧憬在現實世界中返璞歸真、從容徐緩地生活,又希望在幻想世界里過把用仙法武功等彌補現實不足的癮。這便與道學的理念不謀而合了。
而促使道學和古風文化結合的,其一是道學本身帶有的文化特征。道家學派起源于黃老,流行于清以前的封建時期,與古風文化熱衷的古代社會是同時期的。且道學氣質古樸自然,以拂塵、道士袍為標志的充滿古意的文化特征使之被置于古代世界才不至突兀,反使人物和故事更顯神秘飄逸。
其二是修仙、出世等活動無法獲得現世認同。雖然生活在壓力之下,但沒有現代人真的愿意放棄現有生活去追尋虛無縹緲的理想生活。而且現代社會的聯系之緊密,使人的社會性進一步加強,現代人無法完全脫離社會生存。這便決定了出生在現代背景下是被否決的。再者,我國現代社會是承認物質第一性的社會,加之現代人更加理性現實,修仙的“梗”放諸現世就充滿違和,顯得十分不合邏輯。
于是,在一個傳說可編造杜撰的時代下,結合二者本身的同時期性,古風文化與道學文化的糾葛便應運而生了。總之道學文化包括究天人之際的自然學說,察古今之變的歷史學說,窮性命之源的生命學說,集中了自然、社會和人體生命的智慧,必將給21世紀的人類帶來希望。
古風文化在社會上的爭議很多,不管是“學院派”(真偽難辨,但可肯定有一定學識基礎)的嘲諷,還是古風熱愛人士的推崇,不可否認的是古風文化正在步步擴展,并被社會各界更多的人知道。我們不可能一味回復到真正的古代文化,亦不可能完全拋棄古典,保持這顆堅持本來、熱愛本土的心,在主流價值觀的范圍內發展大眾的古風文化,未嘗不是一件值得鼓勵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