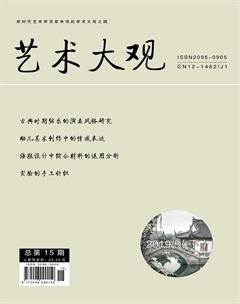《一出好戲》電影結構主義解讀
摘要:電影《一出好戲》講述了一個群體,不同階層的人同時被困在荒島上,體現出不同人性的故事。“反抗—適應—沉淪—改變”這一敘事結構概括了《一出好戲》中大多數人的情節發展。通過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分析,能夠使觀眾更加清楚地看到電影的脈絡發展。多條敘事線索既相互獨立,又彼此依存,從而引發觀眾對人性更深層次的思考。
關鍵詞:結構主義;敘事結構;二元對立
結構主義主要是通過科學的手法對文學、電影等其他學科進行分析,一是注重作品的整體性,二是注重共時性和歷時性。任何事物都是即復雜多樣,又統一存在。使用二元對立的方法進行分析,能更好地深挖表面之下的內在結構,使得觀眾更深刻的了解到導演想表達出的觀點。
一、《一出好戲》敘事結構分析
《一出好戲》從2010年出現萌芽到正式上映,共歷時八年。作為黃渤導演的第一部處女作,并不同于其他導演處女作一樣,試圖極力展現導演自身個性化元素,而是將自己多年的經歷和思考通過寓言體的手法真誠地展現出來,雖然不能堪稱完美,但絕對是近乎完美。
(一)三種階級的對立和更替
一個巨浪將參與團建的公司成員和導游小王一起帶到一個荒島上。這些人里有自命不凡的張總,有見風使舵的老潘,有低調逆襲的馬進,有純潔到黑化的小興,有粗暴領導的小王,有為了生存可以出賣身體的美女,有小人得志的保安等等。經過導演的精心設計,通過長篇幅的表現,各種各樣的角色通過不同的語言特色和身體行為將不同階層的人表現得淋漓盡致。整個在荒島生存的這段日子里共出現了三個領導階級。城市里的人突然被擱置在荒島上誰能讓大家活著,誰就是領導。具有一定野外生存經驗的導游小王在大家的一致推薦下成了第一任領導。由于整個生存狀態趨向回歸原始,小王開始野蠻暴力執法,獨斷專橫,像極了原始社會。矛盾的發展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張總在外出找食物的路上發現了一艘有物資的廢船,隨著張總對新資源的發現,開始出現市場經濟,紙牌代表貨幣,出現了貨幣交易的現象。萬事發展都會遵循生命周期理論,隨著張總控制經濟,保全自己的地位到達一定程度時,人們對此刻的環境開始出現不滿,兩個階級之間長期積累的矛盾終于最大程度地爆發。事情發展到一定極限,必然會出現改變,馬進的第三個階級出現了,一個追求和平并帶給人希望的階級。大家開始接受馬進和小興的領導,前兩個階級也化干戈為玉帛,大家開始幸福的生活在這里。
(二)所有人的“反抗—適應—沉淪—改變”
困在荒島上的三十個人,有著自己不同的選擇,有的人去做領導,有的人試圖離開,有的人逃避“規則”。根據結構主義的整體性特點進行分析,劇中人物從一開始到荒島上的反抗,再到適應各個階級的領導,最后以為外面的世界消失了,是地球上僅有的幸存者,徹底放棄回家的念頭,再到最后通過馬進的引導找到了大船,回到現實社會。張總從進入到荒島的反抗一直維持到對小王領導的反抗,直到自己可以領導別人,轉變生存模式。最后失去領導地位的時候,開始沉淪,直到最后被改變,甚至成為被改變導火索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小興從最開始單純的天使到最后黑化成掌管全局的惡魔,再到回到現實世界出現選擇性失憶,也是體現出反抗、適應、沉淪和改變。大家外在情況雖有不同,但內核都是遵循這個規律。
二、二元對立分析
二元對立在結構主義中,透過表面看深層次的結構。分析敘事結構之后,通過二元對立的手法分析影片《一出好戲》深層次蘊含的意義。《一出好戲》中體現出三組對立的文本結構。分別是階級的上層和下層,物質上的富有和貧窮,社會上的身份與認同。戲劇性又像是中獎似的劇情推動著所有“對立”的形成。從影片開始,張總上車,就會讓人感覺人已到全可以出發,馬進和小興在后面追趕則是第一次出現社會身份被認同的程度。張總通過紙牌進行商品交換,當其他物資減少,魚變得不值錢時,張總為了保持自己的絕大優勢,偷偷地更換著市場的規則,馬進和小興拿魚來換屋子是物質上貧富差異最大的時刻。
三、總結
綜上所述,“反抗—適應—沉淪—改變”的敘事結構不僅僅貫穿在馬進的故事發展脈絡里,同時在滲透到其他的角色上,這就構成了《一出好戲》最顯著的固定語法,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使得我們透過表面去看隱藏在表面之下更深層次的結構。《一出好戲》同時融入導演更多的思考,涉及領域廣泛,將人類的進化進行了一定的闡釋,同時對人性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在荒島上并沒有完全的對與錯,而是根據人們的需要,一個新的生存法則會代替舊的生存法則。結構主義由淺入深,最終涉及社會矛盾的根本問題—階級矛盾。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使我們在看 《一出好戲》這部電影時,擁有了更廣闊的視野和更深入的視角,分析出更多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東西。
參考文獻:
[1]陳曉偉.論結構主義敘事學的發展及其對電影敘事學的影響
[J].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04):55-58.
[2]陳桂琴.國內敘事學研究發展述評[J].外語學刊,
2010(06):139-141.
作者簡介:苗嬌嬌,河北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