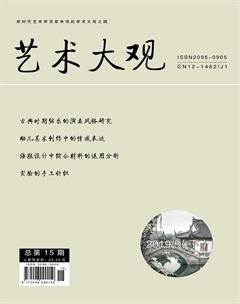淺論影視中的“空間”
鄭南溪
摘要:本文主要從視覺與聽覺兩個方面闡釋人對“空間”的知覺,進而探討影視中由“視”與“聽”構建的“影視空間”。旨在通過對影視空間構成的還原,揭示影視空間“無限可能性”的本源,以此呼喚一種“互動”而非“沉浸”的創作及觀看之道。
關鍵詞:現象學還原;視域;視覺;聽覺
在影視制作的過程中,自劇本撰寫的第一步起,就常會出現“場”“內景”“外景”這類專用術語,它們直指了影視中“空間”的特定概念。
影視中的空間,通常指情境發生的地點、場所,它們透過屏幕這張“視網膜”向觀者呈現影視中事件發生的具體環境,并使觀者信以為與真。這是因為這個經由屏幕呈現的空間,與人們置身現實的世界一模一樣。比如 “場”的不同會顯示地點的變化,“外景”中彎曲的街道會在視線盡頭消失,“內景”中方正的辦公室總向遠處收縮。就這樣,屏幕中的世界被分解為一個個與現實對應的實體空間。觀眾因為總是相信那些“眼見為實”的事物,于是也相信了這些實體空間,以及其中的情境,從而于不知不覺中沉浸其中。
被觀眾如此認識的影視空間,不僅暗指了“空間”即是可分出“內”與“外”的地點、場所這種可以被看的、被分類的客觀的實體,還被認作是一切影視情境發生的首要條件。實際上,這是對影視空間片面化的理解,這種理解,會造成對影視藝術的內涵和外延解釋的狹隘化認識,使無論創作者或觀者的視野隨之而被局限化。在生活被媒體充滿的當今,只有將這類思維定勢破除,還原影視藝術之構成方式,方能幫助人們從根本上認識與把握影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類媒體,從而能夠不僅限于在影視時空模擬的現實中沉浸,也能夠認識影視時空所展現的廣闊意義領域。
由于在通過視與聽來“造物”的影視藝術中,眼睛和耳朵發揮了重要的知覺作用,故本文將從視覺及聽覺出發,探討影視中“空間”原初的構成。
一、視覺對空間的感知之于影視
視覺即眼睛的知覺能力。二十世紀初德國哲學家胡塞爾在他的現象學中,以視覺為起點,分析了人對空間的知覺問題。這位哲學家用一種現象學還原的方法,將事物的諸多物質特性加括號懸隔,而探究其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在對空間的現象學還原中,他將空間還原為意向活動的意向相關項,即一種“空間意識”,而那些與空間有關的事物則成為在這一意向相關項上的顯現[1]。這種“空間意識”首先與人對事物的感知有關。由此,胡塞爾從視覺、觸覺這些知覺問題出發,提出了“視域”和“動感”的理論以分析空間意識的構成,并進一步探討了“視域”的無限可能性特征這一核心課題[2]。這里,所說的 “視域”(horizon)與人眼有限的視覺有關,因而“是一種與主體有關的能力”[3]。“眼動感系統”可以使人產生“空間感”,但無法使“客觀的空間”在視域中被把握。而加入了“行走”的總的身體動感系統,使視域得以“轉向”,并面向無限的可能性敞開。事物及空間的諸面就在這樣的視域中“共現”,成為“空間意識”這一意向相關項上的顯現[2]胡塞爾的“視域”“動感”理論,為我們還原影視空間的構成提供了一個思路,其所言之“視域”,與影視這一“看”的藝術密切相關,而“動感”又與攝影機的運動關系緊密。因此,我們可以從這兩個理論出發,澄清影視空間的構成問題。
首先,“視域”理論將笛卡爾提出的將空間幾何化、對象化的“廣延”(長短、高低、遠近)空間觀反過來,以身體為坐標而展開了[2]。在影視制作中,這個坐標原點也是眼睛:在不同方位角度拍攝對象,可呈現不同透視效果的畫面,如此產生“仰視鏡頭”和“俯視鏡頭”等;攝像機與被攝體距離不同,會呈現出不一樣的“景別”,如遠景、全景、近景、特寫等。這些“鏡頭”之所以能固定下來的并逐漸成了為人熟悉的“鏡頭語言”,正是因為它們完全符合人眼對于事物及空間的知覺方式。
具體說來,人眼的構造使視覺能以透視性顯示方式將感覺定位在觀看對象上;假設身體靜止,當單眼球轉動時,人眼視域中事物和空間的二維平面(形狀、遠近、大小)便隨之逐漸膨脹或壓縮,形成 “二維流形”,“單眼動感系統”如此即可把握一種二維流形的平面。在影視制作中,“搖”這一運鏡方式,可以被直接看作整個“單眼動感系統”。因為影視制作中的“搖”,指的是攝影機位置(機位)固定不變,以其基座(如腳架等)為軸心,鏡頭向左右橫掃、上下豎搖,或繞圈轉動。這正如當人的身體和頭部保持不動時,眼球的轉動方式。若將“幀數”等技術因素(即現象學還原中應被置入括號中的“物質因素”)“懸置”,那么搖鏡時畫面被呈現的過程,亦即“二維流形”在“單眼動感系統”中形成的過程。
與“單眼動感系統”相對應,當雙眼共同成像時,“雙眼動感系統”使得事物和空間在視域中形成“前景-背景”這樣的層級結構,這種層級結構能夠讓人產生“縱深”的錯覺,從而覺得“立體”。比如感知物體表面的“凹凸”,可以形成“前景-背景”的縱深立體感。影視制作中的“景深”一詞,具體地說明了“縱深”這一第三維度的非客觀性。光學透鏡可以產生不同焦點,而利用焦點的變化可以產生不同清晰范圍。如此,畫面便得以呈現出不同的虛實層次以區隔“前景”與“背景”,而當觀眾觀看這樣的畫面時,也就產生了“深度感”。而事實上,這種因“前景”和“背景”而生的“深度感”產生于已經事先預設了三維性的空間之中,而缺少“縱深”這一維度的“三維空間”便只是一種“擬三維”的視域體驗,是一種“空間感”。
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在“眼動感系統”的視域中只能透視性的呈現二維平面及其“二維流形”,而第三維的“深度”只是“前景-背景”這種層級結構在視覺中映射后使人產生的錯覺。換言之,在人眼視域中的“三維空間”也只是一種“擬三維”的準立體空間[4]。
為了進一步闡明包括“縱深”這一第三維度的整體空間意識是如何構成的,胡塞爾提出“身體動感系統”理論。他認為隨著身體的運動(包括頭部轉動、行走等),人眼視域也面向未知的、無限的世界,不斷變化。當人“轉向”人眼視域之外時,就能把握之前事物與空間被遮蔽的部分;身體不斷轉向,諸面也不斷以“二維流形”的方式在視域中顯現;最終,它們會以“共現”的形式在視域中被把握,而在身體的運動過程中,“縱深”這一維度也就被人體把握了[2]。然而,對“縱深”這樣的理解,是將“空間第三維度”的客觀性先行的置于動感和視域體驗中,這于“懸隔”事物物質性的現象學還原方法相悖。再者,在觸覺方面,“深度”也無法通過觸摸而被感知。在某種程度上,通過觸覺而得的“深”可以被看作二維透視在前后方向上的展開[4]。比如,從未見過球體的盲人,通過觸摸會把球體描述成平面展開的橢圓球面[5]。
雖然“動感系統”理論未能說明“縱深”這一空間維度的形成,但它將原來的人眼視域與身體動感系統結合,而面向無限可能性敞開,使“視域”成為一種帶有“不確定的可確定性”的“視域意識”[6]。影視制作中“推”“拉”“移”“跟”這幾種運鏡方式,即是讓人眼視域在各個方向上位移運動。運動不停,新的事物及空間也隨之不斷呈現出來。影視中不經剪輯的“長鏡頭”的魅力也在于此——隨著鏡頭運動的運動,綿延不絕的世界不斷顯示、更新。這正如加入了身體動感系統的觀看的視域(即人眼視域),觀者彼時不再坐在屏幕的彼岸觀看實體化的對象空間,而仿佛親身參與進“動感系統”,主動尋找著影視世界中無限的可能性。
至此,可以說,由各種“鏡頭”組成的影視,正好最為具體的印證了胡塞爾對空間意識的分析。即:在影視中“看”到的“空間”,是對“空間感”或“空間意識”“視域意識”的模擬,而并非“客觀空間”的再現。具體來說,這種“空間意識”首先是以人眼為坐標展開的;在影視中,攝影機作為眼睛,事物及空間向其呈現為各種角度和景別的鏡頭;在“單眼動感系統”“雙眼動感系統”的共同作用下它又呈現出具有透視結構的“二維流形”,以及用“前景-背景”這樣的層級結構模擬的立體感——前者通過“搖”的運鏡顯示,后者通過畫面景深呈現。因為“身體動感系統”的加入,“視域”也不再局限于人眼,而面向具有無限可能性的世界敞開,成為一種“視域意識”。相應的,影視中“推、拉、移、跟”這四種運鏡方式,展現出隨“動感”而來的,時刻變換、具有無限可能性的視域性。
二、聽覺對空間的感知之于影視
人耳同樣具有一定的空間知覺能力,所以語言、音效和音樂等聲音元素也同樣作用于影視空間或“空間感”的構建。但需要強調的是,聽覺對空間的感知是有局限性的,必須與視覺“雙眼動感系統”相配合,才能準確的形構出生活中為人熟悉的“空間感”。這一特點提示我們,聲音必須結合畫面才能強化影視中的“擬三維”空間。而聽覺對空間感知的局限,既與聽覺器官的生理結構分不開,也為感知影視空間的無限可能性創造了條件。
首先是人的耳朵的位置。生物學研究表明,雙耳于頭部兩側的位置差異,使人可以憑借聲波到達雙耳的響度差、相位差、時間差來定位聲源,判斷人體與聲源的相對距離及方向[7]。由于響度差,雙耳接收到的來自遠處的聲音音量小于近處的,人憑此知覺“遠近”。在影視制作中,常利用人耳感知距離的能力以強調相對位置關系。比如,當畫面中出現掠過人群的飛機時,便出現“小-漸強-漸弱”的機械聲,以此強化飛機由遠而近,再由近而遠相反的空間距離。如果聲音是恒定的,觀眾會做出“還有另一架飛機在盤旋”的判斷,但是卻無法像視覺一樣,準確把握飛機的方位信息。
其次是人耳耳廓的構造。人耳耳廓的構造能幫助人利用聲波的相位差把握方向,得到指示聲源方位及運動軌跡的“方向向量”[8]。正是利用了人耳耳廓的這一功能性特點,在當代影院和影視制作中,便常采用“環繞聲”技術,通過LCRS(左中右環繞聲)多聲道系統,模擬聲波的差異,以表現影視中聲源的方位及其運動方向 [8]。
再次是人耳對低頻類聲音存在著難辨其來源的識別局限。由于低頻聲音在空間中分布比較一致,人耳難以對發出低頻聲音的聲源定位,這時就會導致聽覺方向感的喪失。但是在影視制作中,可以利用方向感的缺失,使觀眾更加融入聲音之中[8],從而產生置身畫面情景的錯覺。例如在電影《英國病人》中,一種“遙遠的呼喚聲”經常出現,不仔細聽,觀眾幾乎難以察覺。而事實上,這種聲音是故意使用低頻混音處理,讓聲源方位消失,從而使觀眾誤認為這是環繞在他們身邊的真實聲音,由此不斷在暗中影響觀眾,將觀眾拉入影像中那個遙遠的世界。
可以看出,與視覺相比,聽覺雖不能準確把握事物和空間性質,但確能在聲學上獲得某些空間感;而這種既成的聲學的空間感,反過來亦會直接影響人對空間的知覺反應。在這個層面上,影視中的聲音相較于圖像而更具創造性。這種創造性或與前文所涉及的“視域性”有關:與眼睛總是被遮蔽的視線范圍相比,聽覺更有“穿透力”。人不能直接看見事物和空間的整體,比如人眼看不見的“背面”,只有依靠身體的“動感”繞到 “后面”,開啟新視域。聽覺則不然——聲音在空氣中可以通過各類介質,穿透固體,所以聽覺并不會被“遮蔽”。因此,聲音本身即有“無限可確定性”的視域性,而這種視域性在視覺中需要結合“動感系統”才得以實現。
然而,同樣因為聲音這種線性的、一維的“穿透力”,故而聽覺無法像視覺那樣,直接形構事物和空間的二維平面。即便如此,人常能結合自己的聽覺經驗來判斷事物和空間性質:不同場所的大小、形狀等性質都會影響聲音的傳播;身處這些環境中的人,在用“看”形構這些空間性質的同時,也“聽見”在其中傳播的不一樣的聲音特質(音質、音色等);這些聲音與環境的聯系,久而久之便讓人形成了某些聽覺記憶,直至只憑聲音特質就能辨識出相關環境。這種聽覺經驗對影視空間感的塑造而言同樣十分重要。比如,空曠的大教堂會產生來自四壁的回聲,在影視聲音設計中也常利用混響、回聲等來強調這種空間的特質;而音樂廳、宇宙飛船等的空間具有吸聲的、沒有回音的特質,相應的,在影視制作中就需要用消音等混響效果來模擬這種特殊的“安靜”[8]。結合混音中混響、回聲等表現出來的聲學空間,即可使觀眾得以感知多層次的、“立體”的聲音空間,而這種聲學空間又與視覺對空間的感知經驗有著不可否認的關系。
關于聽覺與視覺對空間的感知,布萊恩·穆爾(Brian Moore)①所做的實驗為我們提供了更多設想:他將人置于四面布滿條紋的旋轉的空間內,同時播放來自四面八方的聲音。旋轉停止后,遮住被試者眼睛,再次播放同樣的聲音,并使播放的聲源方向固定,而此時被試者所感覺到的聲音依舊來自四面八方[8]。這個試驗說明:當人只能靠耳朵辨識空間的時候,人會主動將之前所接收的視覺信息與聲音結合,從而生成新的、不一定“符合實際”的空間感。這種不符實際的空音感直接地“誤導”著人的聽覺感受,使之產生新的空間感。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聽覺只能產生“距離”“方向”這種線性的、一維的空間知覺,而不能像人眼視域一樣把握“空間諸面”,所以在形構影視中的空間感時,聲音通常只起到輔助作用,需要配合相應的畫面才能加強“空間感”。但是僅憑一維的事物及空間信息,聽覺仍可幫助人判斷事物及空間大小、形狀等性質。這是因為聽覺雖然對空間的知覺具有非直接性,但是,聽覺可以在更廣闊的天地里調動回憶、想象等體驗,使人產生更加豐富的空間感受。不僅如此,視、聽覺的結合,還會令這種豐富的空間感受產生另外的變化。此外,聽覺可以直接穿透屏障,從這個層面上說,它又具有視覺不能直接擁有的“無限性”;或者說,聽覺先天的具有“無限可能性”這一“視域性”特征。
將視覺與聽覺對事物及空間的感知原理結合,我們可知:影視藝術中空間的建構,絕不僅是實體場所的再現,而是對于空間意識及“無限可確定性”的視域意識的再現。在影視中,由攝像機代替人眼,音響代替人耳,模擬出人對事物及空間的感知方式,再現了人的空間意識。這種“空間意識”因其與現實中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極其相似,更使人難免沉浸于一種“虛幻的真實”中。所以,影視工作者更應該用盡其所能,還原影視空間及其再現的視域意識的“無限可能性”本原,如利用豐富長鏡頭和聲音設計等,在屏幕內營造一種向觀者敞開的,可以與觀者共建意義的,影視時空。
參考文獻:
[1]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增補版)[M].北京:商務印書
館,2016:361-374.
[2]單斌.空間與視域——從胡塞爾空間現象學的視角看[J].安
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39(06):44-9.
[3]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增補版)[M].北京:商務印
書館,2016:232.
[4]方向紅.遮蔽與阻抗:對空間的發生現象學構想[J].南京師大
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7(02):26-33.
[5]V.Morash,A.E.C.Pensky,A.U.Alfaro &A.McKerracher,“A Re
view of Haptic Spatial Abilities in the Blind”,Spatial
Cognition &? Computation,vol.12,2012,pp.2—91.
[6]Cf. Ulrich Claesges,Edmund Husserls Theorie der
Raumkonstitution,Den Haag,Martinus Nijhoff,964,S.121.
[7]Kalat,J.W.生物心理學[M].人民郵電出版社,2012.
[8]Sonnenschein.D聲音設計:電影中的語言、音樂和音響表
現力[M].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