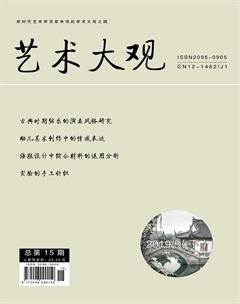哲人的詩情
朱志宇
曾有人說,哲學是理性思維的對象,詩是直覺情感的產物。實際上,這種分際說并沒有摸到他們的本質。
真、善、美圓滿融于哲學之境,也同和于詩。真理之所以為真,也必定圓善,自然也是至美。故真、善、美貫于意境之中。可哲學,亦可詩。
以《詩經》三百篇為例,詩詞中有樸實純真者,有繁華茂盛者,有嘉善賦理者,洋洋大觀,“郁郁乎于文”,不一而足。
首篇,《國風·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句歡快活潑、淋漓盡致地將真善美熔于一爐,讓人吟誦風詠而手不釋卷。
《詩經》305首詩都是孔子撫琴而一一歌之,所刪減而成。就雅俗、韻律、修辭都渾然天成,立一切文學境界之冠。自此以后,“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成為中國文學之魂。也是詩與哲學完美融合的最高典范。
宋代理學大師朱熹,解《五經》,釋《四書》,廣學博文。正可謂哲理深厚,道德高尚,修養純潔。其詩作也妙不可勝。例如: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
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閑識得東風面,
萬紫千紅總是春。
Kasuga
Victory finds the surabaya beach,
The boundless scene is new.
I know Dongfeng noodles at leisure,
It's always spring.
觀書有感
半畝方塘一鑒開,
天光云影共徘徊。
問渠哪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還有《勸學詩》中“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等。既哲理又詩境,絕句一出,無不沁人心脾,感人至深。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以“境界”為詩眼點評詩詞,“隔與不隔”是詩詞曼妙的分界線。朱熹的情、景、理、喻融合為一,全然不隔,其妙佳之境絕不輸于李唐盛世。
按說,文人騷客吟詩弄畫盡情合理。出家僧人以生死為重,參禪頓悟,應當遠離詩情畫意。
其實不然。唐代詩人賈島早年出家為僧,號無本,因善作詩被韓愈發現,而數數嘉勵之。詩句如《宿山寺》“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云。絕頂人來少,高松鶴不群。”《題李凝幽居》中“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也都禪意濃濃,超凡脫俗。
尤其是六祖慧能大師菩提偈: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雖說是偈,但勝似詩。既彰顯非凡修行境界,又妙理動人,成千古絕唱。
其后尚有貫休、齊己、皎然、憨山等等。
有一《無盡藏》詩,不知作者為誰,傳說是一比丘尼所作,詩韻與境界俱佳:
終日尋春不見春,
芒鞋踏破嶺頭云。
歸來我把梅花嗅,
春在枝頭已十分。
每當境界神思冥合一處時,便能靈光閃耀,絕妙佳句便從心中自然流出,成為神來之筆,故可遇而不可求也。
古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著有諸多對話作品,都是哲學思辨的高峰。其邏輯嚴密、辯證清晰、思想深奧,成就了西方哲學上的一座座高峰。他年輕時是頗有抱負的詩人,寫過酒神頌、詩的遐想和悲劇,陳中梅先生在《柏拉圖詩學和藝術思想研究》中評價說:
柏拉圖對詩和藝術(及技藝)的論述散見在各篇對話里,入點不同,詳簡不一,有時立論謹慎,有時潑墨如云,雖然很少形成一統到底的中心,但往往深入淺出,匠心獨運,于平凡之處兀顯新奇。[1](陳中梅《柏拉圖詩學和藝術思想研究》,商務印書館,第9頁)。
亞里士多德是詩評名著《詩學》的作者,他的詩藝理論在十九世紀以前一直被西方學者視為金科玉律,由此可見,詩與哲學關系非同一般。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黃克劍先生一輩子致力于中西方哲學研究,用力之深,貫通之廣,令學人為之欽佩。在其新書《學以致道》中常常流露佳妙詩作,請看:
紅柳
寂寞沙錘生柳榛,
綠衣紫莖絕涯垠。
根深唯接天山水。
風勁方知大漠魂。
沙棗(桂香柳)
銀枝翠葉起沙荒,
素蕊輕妝貽桂香。
不看天山千仞雪。
錯將北國做南鄉。
望江南·春游
春未了,云斷月如鉤。曲柳但為漁火舞,暮江常伴笛聲流,煙浦幾洄游?
猶記得,趁水放輕舟。四野夭喬攜萬籟,一湖瀲滟弄千柔,詩酒亦仙儔。
有人評價:詩是神賜的“愉悅”,詩是技巧的“產兒”,詩是哲學的對手,詩是尋求真理的手段。
此說以王國維先生眼光境界論,猶有隔膜。應看成:詩哲非技巧,詩哲無相對,詩哲寓真意,詩哲通性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