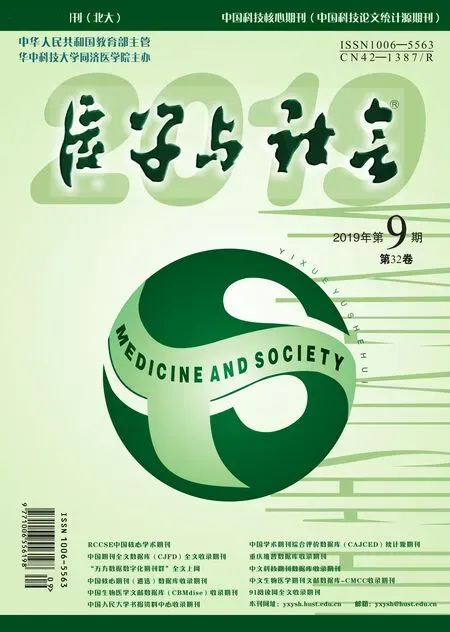慢性病健康賦權的概念分析
劉琪 李春玉 金錦珍 劉晨紅 李伊傲
延邊大學護理學院,延吉,133000
慢性病已成為影響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1],控制慢性病的重要措施之一是提高患者疾病自我管理能力的健康賦權(Health empowerment)。目前慢性病健康賦權已成為歐美國家慢病管理的核心策略,并在醫療護理中廣泛應用[2-3]。但慢性病健康賦權的概念界定不清、缺乏系統分析和深入探討。本文借助Rodgers演化概念分析法對慢性病健康賦權的概念及其內涵進行分析,為深層次理解慢性病健康賦權、多方位探討其影響因素和干預方法提供參考。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文獻分析方法
根據Rodgers演化概念分析法,在選定概念及相關表達式后進行系統文獻檢索;確定該概念的應用領域和相近概念;歸納概念屬性后分析先決條件與后果,為概念發展提出建議。該方法通過系統檢索可提高選定文獻的代表性,分析隨時間推移概念的發展變化[4]。
1.2 文獻檢索
對Web of science-SCI、Wiley、PubMed、知網及萬方等數據庫,通過檢索關鍵詞“慢性病”(Chronic diseases)、“健康賦權”(Health empowerment)精確匹配,檢索時限為建庫至2019年1月。中文檢索關鍵詞為 “授權”、“賦權”、“賦能”、“增能”等,檢索詞擴大為“健康授權”、“健康賦權”、“健康賦能”、“健康增能”進一步檢索。本文檢索到4153條引文,較多為慢性病健康賦權現狀水平、變量相關及部分干預性研究,提及慢性病健康賦權的文獻較多,但直接研究其屬性內涵的文獻相對較少。文獻納入標準以慢性病健康賦權為主要研究內容,涉及慢性病健康賦權概念屬性、先決條件、影響因素、結局及測評的文獻。閱讀后保留42篇,其中英文30篇,中文8篇,2篇博士學位論文和2篇碩士學位論文,符合Rodgers概念分析文獻數要求。
2 概念分析
2.1 慢性病健康賦權概念的起源
賦權源于社會意識形態領域自助、自立的概念。1978年WHO《阿拉木圖宣言》提出健康賦權后受到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領域的關注,2001年英國將其作為慢性病患者衛生保健服務標準[2]。此后,慢性病健康賦權被應用到慢性病人群的研究。
2.2 慢性病健康賦權的屬性
綜合不同時期健康賦權理論和不同領域對慢性病健康賦權的界定,慢性病健康賦權有以下5個屬性:
2.2.1 控制疾病的目標與責任。慢性病健康賦權鼓勵患者將慢性病管理的最終目標由治愈疾病轉為控制疾病,接納自我帶病狀態并自理自立從而達到內在健康。患者在照顧家人和心系社會的責任感驅使下實現內在的健康目標[5-6]。
2.2.2 獲取健康知識的能力。慢性病健康賦權強調患者在具備健康相關知識的基礎上獲得掌控疾病、改變環境的能力[7],調動患者主觀能動性去獲得健康知識、激發個人能力。也有學者將慢性病健康賦權看做是連接健康知識與個人能力的橋梁[8]。
2.2.3 自主參與健康決策的過程。早期研究將慢性病健康賦權理解為改善疾病的健康結局而形成的一種積極的合作護患關系[9]。結合羅杰斯整體人學說和紐曼健康意識拓展論的觀點,慢性病健康賦權是患者自主參與到健康決策制定的過程[10]。
2.2.4 提升自我效能的結果。慢性病健康賦權不僅是醫務工作者為患者提供有針對性的健康教育、健康咨詢和以患者為中心的服務過程,也是患者通過上述過程達到提升自我效能的結果[11]。
2.2.5 賦權他人的意愿。慢性病健康賦權強調在提升個人健康知識與能力的基礎上病友之間的互動作用,患者通過賦權過程提升知識與能力,與同伴分享疾病管理經驗[12-13]。
2.3 慢性病健康賦權的先決條件和影響因素
自主的選擇、適應不良行為和解決問題的動機是慢性病健康賦權的先決條件。影響因素包括內在因素(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文化程度、自我效能、感知控制等)和外在因素(醫療報銷比例、居住地、護患關系信任度、健康決策參與度等)[14]。也有學者將其分為個人因素(如健康素養)和社會因素(如社會支持)[15]。Cattaneo認為社會環境影響慢性病健康賦權的整個過程[11]。因此慢性病健康賦權的干預可從個人因素和社會因素出發,將重點放在患者的社會環境。
2.4 慢性病健康賦權的結果與意義
慢性病健康賦權可增強患者自我效能,提升自我決策能力、促進健康行為,感到有希望、被鼓勵及有方向感,能主動尋求健康資源。慢性病健康賦權使患者知足常樂并在疾病和衰老中尋求快樂的人生意義[6]。
Fotoukian將慢性病健康賦權定義為患者積極開發和利用知識與能力、培養信心、獲得自我發展與自我滿足、提升自我意識感和自我效能感,從而控制疾病、管理生活和促進健康的過程[16]。我國慢性病健康賦權的概念不盡相同,楊陽等提出慢性病健康賦權是患者在內在責任感和外在支持系統的共同作用下,積極掌握知識和技能,逐漸管理自我和賦權他人,重建自我的過程[17]。也有認為現代慢性病健康賦權更加重視以患者為中心的自身賦權過程和結果[18]。國內的定義更強調病友間的支持交流互動以及親情的作用(圖1)。
2.5 慢性病健康賦權的同、近義詞
健康賦權的同、近義詞有健康授權和健康賦能。健康賦權與健康授權相近,但授權和賦權含義不同,授權指授予被授權者應有的權力去完成某項工作,賦權則指賦予被賦權者權力的同時賦予其責任,激發其內在潛能實現目標,健康賦權是成功的健康授權[19]。健康賦權與健康賦能相近,但賦權是過程,賦能則是一種和健康相關的心理社會結果,被賦權者在被賦予權利之后是能力增加[20]。有效的慢病管理應是在賦予患者權利后不斷激發其健康責任,使其利用知識提高能力,控制疾病促進健康,健康賦權更符合現在慢性病管理要求。

圖1 慢性病健康賦權概念框架
2.6 慢性病健康賦權的測評指標
現有的慢性病健康賦權測評主要針對單一慢性病和特定人群,如糖尿病健康賦權量表(DES)測量糖尿病患者自我控制、自我效能、參與決策、壓力管理、情緒調整、自我激發、社會支持、解決問題的水平[21]。老年人健康賦權量表(EHES)是在DES基礎上修訂而成,旨在測量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健康賦權水平,與其他工具同用可反映老年慢性病賦權水平[22]。患者健康賦權量表(CES),將住院的慢性病患者視為整體,測評其控制疾病的信心、護患關系、社會支持、患者權利認知水平、對疾病的控制感和同伴支持水平[23]。慢性病患者賦權量表(LTCES),測量慢性病患者對疾病的態度、自我管理、自我認知、知識獲取、參與決策與賦權他人的能力[24]。上述量表結構嚴謹、涵蓋面廣,國外大樣本應用有良好的信、效度,但國內尚未廣泛使用。
2.7 慢性病健康賦權的實證分析
護患雙方共同參與、積極傾聽、獲取健康知識及形成健康行為是慢性病健康賦權的過程。Bridgers增加“賦權病友”,并在實踐中應用。如應用于心臟康復高級執業護士對冠脈移植術后患者及家屬進行全面評估,提出家庭鍛煉計劃及個性化指導(患者積極傾聽),護士了解患者及家屬的意見(護士積極傾聽)。復診時護士再次了解其家庭鍛煉計劃實施情況(積極傾聽與傳授個性化健康知識)。患者應用所學疾病相關知識完成康復計劃并與護士溝通。患者在12周內完成了健康目標,做出自我健康決策并與病友分享疾病管理知識[25]。
3 小結
《中國防治慢性病中長期規劃(2017—2025年)》強調個人健康責任,指出慢性病管理應注重患者自我管理和參與決策,而慢性病健康賦權恰好符合這一策略性框架。不同區域、國家及文化的差異使得目前學界對慢性病健康賦權的定義和理解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厘清慢性病健康賦權的概念內涵至關重要。通過借助Rodgers演化概念分析法分析慢性病健康賦權的先決條件和影響因素、結果與意義、測評指標并對近義詞辨析和實證分析,了解其具有控制疾病的目標與責任;獲取健康知識的能力;自主參與健康決策的過程;提升自我效能的結果和賦權他人的意愿。目前對慢性病健康賦權的內涵缺乏深入分析,在今后的研究中,可采用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相結合,深層次多方位探究慢性病健康賦權的內涵,從患者的真實感受出發,使慢病管理能夠真正做到以患者為中心,賦予其參與疾病治療決策的權利。干預時要充分考慮多方因素,注意規避因賦權不當產生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