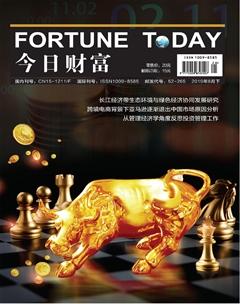從博弈論角度看中國環境污染治理難題
李瀟鴻
環境是人類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源。當前,我國以環境換發展的惡性后果日益顯現,全國大氣、水資源受到嚴重污染。近年來,在國家的不斷努力下,我國生態環境質量實現了一定改善,但仍無法根治,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緊迫性、反復性、長期性問題依然存在。本文從博弈論角度對中國環境污染治理難題進行分析,主要涉及企業和政府兩類主體,通過設計兩個博弈方之間的博弈模型來對中國環境治理難的問題做出解釋。
一、企業之間的博弈分析
假設:
(一)政府不采取監管,企業出于利益最大化原則選擇是否排污。
(二)假設環境污染會影響企業產量和質量,當環境受到污染時,企業的產量與質量降低,當環境質量提高時,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收益增加。
(三)假設不排污企業治理環境污染帶來的收益增量大于其治理成本,即治理環境為企業帶來的利潤大于零。
(四)環境中只有兩家企業1和2,且相互競爭,生產規模及排污水平相當,生產的產品同質。若兩家企業均排污,則兩家企業利潤均為R0;否則,兩家企業利潤均為R,治理企業的治理成本為C;若一家排污,一家不排污,則排污企業利潤為A,不排污企業的利潤為B。有A>R>R0>B。
從中可以看出,不管企業2選擇什么,企業1的利益最大化選擇都是排污,相反也是如此,即“排污”為企業1與企業2的占優策略。在沒有政府監管或政府監管不力的情況下,兩家企業都會選擇排污,即最后得到納什均衡為(排污,排污),陷入了囚徒困境。
由此可見,由于環境資源是典型的公共資源,由于環境資源成本難以有效體現在排污企業的經營成本中,難以計量,同時,排污引起外部不經濟,環境成本一般由社會大眾承擔,因此導致,在企業家作為“理性人”時,企業紛紛選擇排放污染,當總排放量超過環境的最大承載量時,環境無法自主緩解,最終造成環境破壞。即公共資源容易在各參與人之間形成利益沖突以及個體與集體之間的沖突,造成“公地悲劇”。
二、企業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分析
假設:
(一)假設環境只有一家企業,且R與Q有關,企業排污時利潤為R1(Q1)。政府稅收與企業產量有關,為T1(Q1);企業不排污時利潤為R2(Q2)(未扣除治理成本),政府稅收為T2(Q2)。由于企業治理環境污染會增加成本,進而影響其產量水平,有Q1>Q2,進而R1> R2, T1> T2。
(二)政府監管成本為X,企業治理成本為C,假設若企業排污,被查到后罰款為F。
(三)企業排污會影響周圍的居民,使其聲譽受損。政府監管不力或者與企業合謀,則同樣聲譽受損。假設聲譽成本較小,在這里可忽略不計。
(四)滿足,F>X,且F>C。
由支付矩陣可知,當政府選擇監管時,企業選擇不排污,當政府選擇不監管時,企業選擇排污,即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不存在純策略納什均衡,因此,需要進一步采用混合策略來確定最終的策略組合。
由于政府的財力,人力有限,無法做到一直監管,因此,設政府進行監管的概率為p,則政府不監管的概率為1-p,設企業排污的概率為q,則企業不排污的概率為1-q。有:
p(R1-F)+(1-p)R1=p(R2-C)+(1-p)( R2-C)
q(T1-X+F)+(1-q)( T2-X)=qT1+(1-q)T2
求解,可得p=(R1-R2+C)/F,q=X/F。
此即政府與企業在實現混合策略納什均衡時的概率。以p0表示政府進行監管的概率,q0表示企業排污的概率。則有,當p 納什均衡時的概率取決于企業排污與不排污時的利潤,企業治理成本,企業罰款金額以及政府的監管成本。當企業排污時的利潤越大,不排污時的利潤越小,企業治理成本越大時,或政府的懲罰力度越小,監管成本越大時,企業就越傾向于排污。 三、企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博弈分析 (一)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的博弈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將財權與事權逐步下放到地方,地方政府具有自主管理的權利,一些公務可以自己做決定。并且,每年的稅收也不必全部上交中央,地方掌握了部分事權與財政權。同時,中央政府對同一級地方政府官員的提拔是通過考核地方GDP的大小來進行的。一些地方官員為了得到提拔,就會在中央下達的指標之上擴大指標,層層遞進,到最后一級官員時,指標通常已被放大了很多,這也就是為何我國能夠保持30年來的高GDP增長率的原因之一。 雖然,中央對地方的績效考核方式有效地激勵了我國的經濟增長,但也有其不足之處。地方與中央進行決策時,都有兩種方式,中央政府對下達的命令的執行程度的監督與不監督,地方面對中央的命令的消極執行與積極執行。 由于中央對地方的考核方式是通過GDP總值進行,因此,各個地方官員會想方設法的增加地區GDP。每個地方政府都是“理性人”,為獲得 GDP政績、財稅收入和私人收益而追求經濟增長,地方官員對當地一些貢獻GDP大的污染企業降低環境準入門檻,同時在中央監督不力的情況下,也可能會和企業進行合謀或接受企業的賄賂,對此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甚至暗中幫助,來達到雙方的利益最大化。在這種情況下,面對環境惡化,每個地方政府都不想第一個退步,先退步的人,GDP總值小于其他地方政府,在政績考核時處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地方政府都不會退步,導致環境越來越惡化。 根據以上分析,下面對企業、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的博弈進行分析。 (二)企業、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三方之間的博弈分析 假設三個博弈主體都是“理性人”。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則在GDP績效考核制度的前提下,在執行中央政策與地方政府經濟利益之間尋找平衡點;而中央政府則是著眼于長期,以社會福利最大化,實現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因此,對地方政府來說,短期內,追求的是GDP最大化,與企業的目標一致,在面對中央政府的環境污染監管方面,地方政府與企業有可能達成合謀。 假設: 1.企業在正常達標情況下,收益為R,地方政府收益為I。 2.企業與政府合謀時,企業收益增加△R,地方政府收益增加△I。 3.中央政府監管成本為C。 4.當污染企業被查處時,罰款為F,對地方政府的處罰為G。 從中可以看出,只有當G+F>C時,中央政府才會選擇監管,而對于企業和地方政府來說,只要合謀帶來的利益增量大于罰款數額,則企業和地方政府就會合謀。所以,只有上述條件滿足時,策略(合謀,監管)才會發生。 由于信息不完全,三方博弈主體無從正確判斷其他博弈方下一步將要選取的策略,而是只能根據其掌握的信息量來判斷對方所采取的各種策略的概率,并由此判斷其他博弈方所應采取的博弈行為。 假設,中央政府監管的概率為q,不監管的概率為1-q,其中監管成功的概率為r,不成功的概率為1-r,企業與地方政府合謀的概率為p,不合謀的概率為1-p,則有 (R+△R-F)qr+(R+△R)q(1-r)+(R+△R)(1-q)=Rqr+Rq(1-r)+R(1-q) (I+△I-G)qr+(I+△I)q(1-r)+(I+△I)(1-q)=Iqr+Iq(1-r)+I(1-q) (G+F-C)pr+(-C)p(1-r)+(-C)(1-p)r+(-C)(1-p)(1-r)=0 求解,可得:q(企業)=△R/Fr,q(地方政府)=△I/Gr,p=C/[(F+G)r] 此即發生(合謀,監管)策略的概率要求。當中央政府監管的概率q> q(企業)時,企業選擇與地方政府合謀,當q> q(地方政府)時,地方政府選擇與企業合謀,當q大于兩者中的最大值時,企業與地方政府都希望與對方合謀,否則,則相反。當p> p*時,則中央政府選擇監管,否則,選擇不監管。 從中可以看出,發生(合謀,監管)的概率與地方政府罰款以及企業罰款有關,G,F越小,地方政府與企業越容易發生合謀。同時,地方政府與企業合謀的概率與中央政府監管的成功率r,監管成本C也有關,與r呈負相關關系,與C呈正相關的關系。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政府若想減少或避免企業與地方政府的合謀,應降低監管的成本,提高監管的效率以及加大對地方政府與企業合謀的懲罰力度。 四、結語 環境作為公共資源,其使用與消費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競爭關系以及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個人的最優不一定能夠帶來集體的最優,因此,一旦處理不好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就容易發生“公地悲劇”的現象。對此,政府應該制定科學合理的制度,建立良好的道德規范,協調好個體與集體在環境資源利用上的利益沖突,才能避免“公地悲劇”,使得集體利益達到最大化。 在環境污染治理問題中,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以及企業、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的博弈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過建立模型,求解出了發生混合策略納什均衡時相應的概率大小。從中可以看出,我國環境污染治理難的原因是由于對環境法規和制度實施情況的監督不力,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目標并不總是完全一致而造成的,特別是分稅制改革以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各自的財政利益,地方政府官員的提拔制度依據GDP政績。對此,中央政府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勵制度,調整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保障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利益目標與政策目標的一致性,完善環境法規與制度,改善各地方政府之間的不良競爭,來達到避免企業和地方政府合謀行為的發生,有效治理環境污染,提高環境質量水平的目的。(作者單位:河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