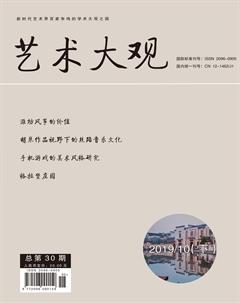陜西寶雞隴縣閻家庵村“血社火”田野調查
摘要:閻家庵村“血社火”作為陜西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以說明性的舞蹈動作敘述情節,并有著神秘恐怖的面部妝容。這種獨特的民俗文化符號,具有很深的研究價值。本文從整體儀式出發,對血社火舞蹈形態進行田野調查。
關鍵詞:閻家庵村;血社火;舞蹈形態
閻家庵村血社火主要在春節期間以及廟會期間表演,是正月十五必演的活動,由于晚上表演,被當地人還稱為夜社火。血社火有著專門的表演場地,在閻家庵村山下的廟前演出,是全村位置最高的地方。閻家庵村血社火傳承人分別是:閆春林、武德田、梁栓虎,三人有著血緣關系,同時也是血社火表演的主要演員,再加上自己的子女,以及村上的孩子來進行社火表演。
一、“血社火”的儀式內容
閻家庵村的村廟有前后兩間,廟里分別供奉著關公、九天圣母以及三大菩薩等神靈。祭神儀式是血社火的重要部分,表演之前要先去廟里祭拜。祭神儀式始終伴隨著鼓與镲的聲音,血社火的表演人員戴好妝飾來到廟前,依次上香叩拜。隨后,鞭炮聲響起,所有表演人員排為一列,在前后廟前的兩塊場地上,分別逆時針繞場地游走三圈,來驅趕鬼怪以及邪祟。最終演員走向廟門前,開始血社火表演。
血社火運用肢體語言來表現固定的情節。演述關羽仗義護送兩位皇嫂;黑虎趙公明魂會三霄娘娘;梁山英雄三次攻打祝家莊成功的故事內容。以《三打祝家莊》的故事為主要,表達懲惡揚善的主題思想,具有深刻的教化意義。舞蹈配合著獨特唱腔,以及統一的樂器節奏。在三打祝家莊的故事結束后,進入廟門前臨時搭建的小密室中。通過快速化妝,形成演員逼真又恐怖的面部形象,給人視覺沖擊。演員由密室這邊進去后片刻便從另一邊出來,由此也被當地稱為“快活”。外人不能看化妝的過程,十分神秘,只傳男不傳女。社火將要表演完的時候,村民們會在表演場地的后面用柏朵和樹干燒起火堆。從火堆上跳過,有祛病消災的用途,也更把全場的氣氛推到高潮。
二、“血社火”的舞蹈形態
血社火運用陜西社火臉譜,臉譜有固定的紋飾,臉譜也象征著固定的人物。服裝與戲曲的服飾接近,借助輕盈的助服裝增添飄逸的形象感。血社火的舞蹈風格剛柔并濟,將女子的輕柔與男子的陽剛巧妙地融為一體,其動作以說明性動作為主,通過肢體語言來表現故事情節,使整個儀式活動生動形象。舞蹈動作始終伴隨著器樂或念唱,以動靜相結合的方式貫穿在整個表演過程中。
(一)表演動作
血社火的演員腳下常用碎步,圍繞演出場地跑動,配合道具來表現出趕路、跟隨等說明性動作。腳下動作飄逸,轉身時上肢滑動披風,營造飄逸的舞蹈形象。以原地轉圈的動作,來變換場圖,并通過后退碎步來變換位置。血社火的故事情節使其具有大量表現搏斗的舞蹈動作,通過手中棍、矛之類的道具,配合轉繞道具、武打、跳躍以及轉圈等動作,表現出演員在打斗中身懷絕技、武功高強的形象。演員在打斗中兩人一對,巧妙地運用相互穿插,通過正背兩面、交替對打的輪流方式,實現場圖的流動。并且在其中還有托舉動作,快速跳蹲以及旋子、飛腳等跳躍動作,來渲染爭斗激烈的場景。二次化妝后通過游走,雙手叉腰的動作,將恐怖形象展現出來。
(二)表演音樂與道具
血社火表演始終伴隨著鼓與镲聲,演奏樂器由兩鼓兩镲組成的。中間會穿插著曲調,是隴縣地區的隴州小調,以清唱的形式歌唱,因隴縣處于三省的交界位置,有著民族交融的風格曲調。血社火中的隴州小調歌詞具有隨機性,歌詞中有著大量“哎”“嘿”“呦”等襯詞,從而加強歌詞與曲調的流暢性與節奏性。小調的歌詞內容以酬神為主。歌詞具有濃厚的祀神色彩,具有祈求諸神顯靈的意蘊。
血社火表演中的道具十分豐富,有大量象征人物身份的工具同時,還運用棍、刀、矛與鏈枷棍的道具加以舞蹈動作,來表現出激烈的武打場面。在三打祝家莊情節中,演員手拿著一些鐮刀、斧頭、錐子、剪子等九種農耕用品為道具,對扮演祝家莊人的演員進行追逐,表現追殺的場景。最后演員進行第二次化妝,將這些道具置于面部或頭部,裝扮成恐怖的形象。這些道具絕大部分來自故事情節的需要,并且充分利用著農耕用具。
(三)表演場圖
血社火的場圖多以圓弧形線條為主,通過橫排隊形的相互穿插,人數的增減變化而形成不同的場圖變化。整個表演由于是四周都圍繞著觀眾的圍場子形式,所以舞蹈多重復,四面依次分別表演。表演情節中,常以主要情角色節來帶領隊伍變化場圖,多采用圓形或八字圓等流動場圖,演員之間通過隊形變化相互交流,形成對打等動作。隨著人數、位置與方向的變化,場圖之間也相互轉換,使血社火的場圖也不斷地改變,表演場景十分豐富。
生態與文化創造出民俗活動,并孕育了民間舞蹈。閻家庵村“血社火”具有綜合性的歌舞表演形式,特定的情節與場地,通過血社火的舞蹈形態,可窺探其蘊藏的文化觀念。
參考文獻:
[1]巫允明.中國原生態舞蹈文化[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0.
[2]樸永光.舞蹈文化概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2018.
[3]吳國棟.民族音樂學概論[M].上海:人民音樂出版社,2012.
作者簡介:田龐華,陜西師范大學音樂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