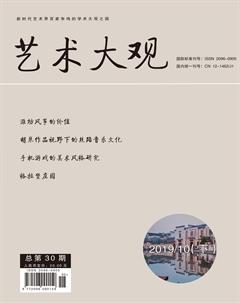地方政府視角下的非遺保護實踐
姚思晴 李兆玉 趙涵 王曦 黃周潔
摘要:地方政府作為國家非遺政策的具體執行者和地方非遺手藝人的密切聯系者,在非遺保護工作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從對山東高密聶家莊實際調查的基礎出發,希望以“高密聶家莊泥塑”為例,展現地方政府在非遺保護中的政策舉措和存在的部分問題。
關鍵詞:聶家莊泥塑;非物質文化遺產;地方政府
在2005年出臺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中強調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原則需做到“政府主導”,這表明各級政府是非遺保護工作中一個密切相關的參與主體。
山東高密的聶家莊泥塑自2008年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后,關于其藝術特征、現狀調查及生產性保護等問題學界已有一定結論,但在關于聶家莊泥塑在非遺保護工作中地方政府所起的推動作用及不足之處的研究卻仍存在空白,所以本文旨在通過實地的走訪調查,對山東省地方政府有關聶家莊泥塑非遺工作的開展進行總結與反思。
一、山東地方政府在非遺保護的行動
如何科學、合理地保護和傳承是非遺在“后申遺時代”所必須解決的問題,同時這兩項工作在地方上開展地成功與否也是決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否能從冷冰冰的名錄中“活過來”,重新煥發生機的關鍵。[1]
“地方”這一概念在本文中主要是指中級地方政府與基層地方政府,也就是涉及“聶家莊泥塑”非遺保護工作的四個地方政府主體:山東省政府、濰坊市政府、高密市政府、姜莊鎮政府。
(一)保護政策的制定
自2011年國家頒布《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以來,山東省及省內各城市政府根據國家方針政策及法律法規的要求,結合本地實際情況有意識地建立和完善非遺相關的配套地方性保護體系。
其中,山東省政府于2015年出臺了《山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條例》。與《非遺保護法》相比,《非遺條例》更加明確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的工作內容及具體要求并對國家頒布的條例進行有效的補充細化。[2]除此之外,山東省政府還創造性地提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豐富、文化生態保存完整的村、鎮,省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門可以命名為文化生態名村、名鎮”①,希望對非物質文化遺產豐富的特定區域實行整體性保護,比如聶家莊泥塑所在的“高密市聶家莊村”就入選首批山東省十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特色村(社區)。
此外,濰坊市政府依托區域內的“濰水文化生態保護區”在2018年末制定了《濰水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管理辦法》及《濰坊市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認定與管理辦法(試行)》兩項規定。這兩項規定中有如設立“濰水文化宣傳月”,利用特色節慶活動和公眾教育平臺集中宣傳濰水文化,鼓勵對濰水文化進行專題性研究并形成學術成果,非遺項目推行“一項一策”保護措施等帶有“濰水文化”烙印的具體舉措,以期最大限度發揮地方特色,構建良好的濰水文化生態環境。
(二)四級非遺名錄體系的完善
在“政府主導”的要求下,全國范圍內構建起國家、省、市、縣(區)四級非遺名錄體系,即“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同時還有與之相匹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清單”。
山東省政府注重非物質文化名錄體系及傳承人保護機制的建設,依據國家規定建立了國家、省、市、縣四級非遺名錄體系,并對境域內有歷史、有價值、有特色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進行普查,將瀕臨滅絕且傳承困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優先列入四級體系中。其中山東高密聶家莊泥塑已分別入選國家第二批,省、市、縣第一批非遺名錄。
值得一提的是,山東省政府在非物質文化遺產領域提出“六個一”保護行動的同時,針對代表性傳承人開展“五個一”扶持計劃。[3]由于省級及以上的代表性傳承人數量較少,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六個一”保護行動與“五個一”扶持計劃主要圍繞代表性項目傳承人這一主體開展。以聶家莊泥塑為例,山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于2012年7月授牌成立以國家級傳承人聶希蔚命名的“聶希蔚泥塑傳習所”,其占地面積100多平方米,以此為據點常年展覽泥塑作品并接受學徒前來學習。
(三)生產性保護原則的落實
近年來,山東省政府采取積極有效的政策開展省內非遺生產性保護工作,帶動非遺項目與社會、個人組織對接,大力扶持、引導非遺生產性保護基地的建設,截至目前已有東阿阿膠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企業被文化和旅游部命名為國家級非遺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省級非遺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也有德州扒雞集團等共68個。高密市紅高粱民間文化藝術有限公司作為其中一個省級非遺生產性示范基地,圍繞高密市現有的文化資源,集中投資建設了包括姜莊民藝民俗村、紅高粱影視城等一批工程項目,為聶家莊泥塑的創作、展出、銷售等環節開拓了新的渠道。
二、地方政府非遺保護中的不足
(一)非遺政策與實際行動不對應
為響應國家和上級政府的號召,滿足非遺傳承人的藝術創作需要,山東高密市政府制定出臺了一系列規范性文件,其中明確了發展市內重點非遺項目(聶家莊泥塑、高密剪紙)的各項要求及任務計劃。但當走訪聶家莊村從事泥塑制作的手藝人問及當地政府有提供什么幫助抑或是有組織什么活動時,一位泥塑手藝人回答道:“加入了高密文聯后,高密文聯平時沒有組織什么活動,也沒有提供幫助。”面對同樣的問題,市級傳承人張清先也坦言“沒有受到什么幫助,政府不太照顧”。在這些簡單的一言兩語背后,實際上暴露了國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方針政策最終并無多少有效成分轉化為支持聶家莊當地的非遺傳承人繼續產出創作上。至于外出參展等宣傳聶家莊泥塑的機會的獲得,則更有顯著差異。以聶臣希、聶鵬一家為例,一年內受邀參加各類文化活動的次數平均為2至3次,而其他傳承人獲得的機會相對較少,甚至會因參展攤位價格過高導致入不敷出主動選擇不參會。在不考慮制作手藝精湛與否這一前提下,參展次數多的手藝人獲得展示的機會越來越多,經濟收入、創作熱情、制作規模也隨之高漲,反之大部分手藝人則因缺失參展機會和缺乏經濟補貼陷入無人問津的境地。
(二)保護示范場所不完善
高密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陳列廳和高密市博物館民俗廳是高密市內與聶家莊泥塑相關的博物館類保護示范場所。經筆者走訪發現,相較之下高密非物質文化遺產陳列廳內容更為豐富,但展品的輔助講解僅會在有學生研學團體、領導參觀等集體式參觀時才配備,若只是當地民眾或外來散客參觀則只能自行參觀。而高密市博物館民俗廳內的聶家莊泥塑比較就更為簡陋,只有展廳一角擺設寥寥數件泥老虎。總體而言,聶家莊泥塑盡管是一個國家級的非遺項目,但在其所在城市內的民俗文化博覽館中存在感占比較小,相關的展品也大多是雷同的泥老虎、泥娃娃,展示形式單一。至于另一類保護示范場所——傳習所,聶家莊內圍繞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共設有聶希蔚的“聶希蔚泥塑傳習所”和聶臣希的“聶家莊泥塑傳習所”。為考究其開展的實際狀況,筆者采訪聶希蔚和聶臣希發現,在傳習所創辦之初,曾斷斷續續有零丁幾人前來短時間地拜師學藝、交流經驗,但近幾年更多演變為社會實踐或游學活動的形式,即由學校組織五六個學生前來參觀展覽、體驗制作流程。以上的現狀反映了聶家莊內的泥塑傳習所并未實現政府擬通過聶家莊泥塑傳習所讓大眾認識非遺,了解非遺,最終積極參與非遺保護與傳承中的構想,實際上它的傳承仍未擺脫以“親緣傳承”“地緣傳承”為主的傳承模式;而傳習所到底是作為培訓傳承人的平臺抑或是大中小學生游研學基地也不得而知。
(三)生產性保護效果不理想
地方政府牽頭的對聶家莊泥塑實施的生產性保護政策成效也并不顯著,高密市紅高粱民間文化藝術有限公司這一省級非遺生產性示范基地和國有獨資企業高密市紅高粱集團旗下產業是將高密市的文化品牌轉化為經濟效益的重要渠道。但在這些攬括高密市內各類特色民俗文化的企業里,聶家莊泥塑在其中并不顯眼,哪怕紅高粱藝博園就設在聶家莊村村頭,聶臣希卻稱“里面屬于泥塑的展廳其實很小,東西也挺少”,聶鵬更是將紅高粱藝博園描述為一個與非遺關系不大的景點。而紅高粱集團本身在聶家莊泥塑產業鏈中更多扮演的是一個提供平臺和對接客戶的角色,據盛杰丈夫介紹:在與紅高粱集團合作的過程中,他們主要負責調查消費者喜好并在此基礎上完成紋樣造型設計,紅高粱集團方面則承擔打樣、生產、投入市場等工序。可盛杰一家與紅高粱集團置換資源與平臺的合作模式在聶家莊中并不多見,大部分的泥塑手藝人仍十年如一日地忽略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堅持“個體批量生產—熟客打包收購—市場散裝銷售”的傳統思維獲得微薄利潤。
三、結束語
自2008年聶家莊泥塑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以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完善、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建立、各級各類宣傳活動的開展,山東省地方政府圍繞其開展的各項保護工作總體步入正軌。但實地深入聶家莊調查后發現地方政府工作的落地效果實際與理想目標仍存在很大一段的距離,具體體現在非遺政策與實際行動不對應、保護示范場所不完善、生產性保護效果不理想等方面。因此,各地非遺保護單位要到人民群眾中去,根據各項行動的實際開展狀況及時調整行動計劃,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提供動力,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堅定傳播者,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
參考文獻:
[1]段友文,鄭月.“后申遺時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社會參與[J].文化遺產,2015(5):1-10+157.
[2]王云慶.山東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及傳承人立檔保護研究[D].山東大學,2017.
[3]李國琳.推進非遺保護傳承體系建設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J].人文天下,2015(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