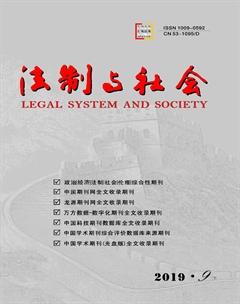我國非全日制用工立法完善對策研究
摘 要 盡管非全日制用工相關規定在《勞動合同法》中所占篇幅不大,但并不能否認這一用工形式的重要性。如果以傾斜保護勞動者權益的勞動立法理念為標準檢討我國非全日制立法內容,則會發現,相關制度設計方面存在需要完善之處。未來,我國應以傾斜保護理念為指導,在非全日制用工適用范圍,合同形式要求,以及解雇保護等方面做出必要調整,以更好地保護非全日制工人的勞動權益。
關鍵詞 非全日制用工 立法 制度設計
基金項目: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項目“非典型勞動關系的法律規制研究”,項目編號:13E001;大慶師范學院基金項目“我國勞務派遣法律規制研究”,項目編號:12RW03。
作者簡介:章輝,大慶師范學院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經濟法、勞動法。
中圖分類號:D9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9.258
一、我國非全日制用工市場發展歷程
非全日制用工市場是勞動力市場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在滿足企業多元化用工需求和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回顧我國非全日制用工市場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可以看出,既有國際背景因素的推動,同時也是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從國際上看,非典型用工市場的產生和成長是勞動彈性化發展的直接結果,而非全日制用工在非典型用工市場中占有很大比重。時間回溯到20世紀70年代末,資本主義主要國家在經歷了戰后黃金發展期之后,因為滯漲的出現而深陷泥潭,勞動彈性化則是被作為破除危機的手段之一而推出。在這一背景下,非全日制工數量劇增,占據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不斷攀升,這是一個正在全球范圍內發生的普遍現象。 加入WTO之后,中國經濟日益全球化,大量企業更是廣泛參與國際競爭,以獲得更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面對國際范圍的勞動法放松管制和勞動彈性化發展趨勢,國內企業也陸續進行了相應的用工政策調整,以因應國際市場競爭需要。這是我國非典型用工市場產生和發展的背景,同時也是動力之一。當然,我國非全日制用工市場的蓬勃發展更是有著深刻的國內背景。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經濟體制轉軌,迄今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很多人為此付出了“代價”,下崗失業就是代價之一。毫無疑問,這群人中的相當一部分進入了非全日制用工市場。非全日制用工市場已然成為勞動力市場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非全日制勞動者權益保護問題,也日益引起廣泛關注,并成為立法規范對象。
二、我國非全日制用工立法存在的問題
(一)非全日制用工未能貫徹書面合同要求
我國《勞動合同法》第10條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但是該法第69條又以例外規定的方式允許非全日制勞動用工采用口頭協議明確雙方權利義務關系。表面上看,除了一般性明確書面勞動合同的重要性和嚴肅性,也考慮了非全日制用工的復雜性和靈活性要求,似乎并無問題。但是正如學者所憂慮的那樣“口頭合同的遵守和履行往往有賴于合同意識和誠信意識的廣泛建立,這恐怕正是勞動關系雙方當事人所缺乏的。” 關于勞動合同形式,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問題的意見》要求,一般以書面形式訂立,一個月以下期限的,可以訂立口頭勞動合同。這樣的柔性措辭,加之勞動力市場勞資雙方懸殊的實力差距,出現大量的口頭協議并由此產生勞動爭議也就“順理成章”了。《勞動合同法》頒布實施后的司法實踐也表明,不訂立書面合同會給非全日制勞動者帶來維權困難。勞動者無書面合同難以證明自己與用人單位形成勞動關系,即使證明了勞動關系,也難以證明雙方約定的權利義務。 實際上,即使就全日制用工而言,不少用人單位對于書面勞動合同的簽訂都不甚積極,而允許非全日制用工采用口頭協議,其結果可想而知。
(二)非全日制用工適用范圍過大
事實上,與全日制用工相比,非全日制用工只是勞動關系的另類表達,二者之間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然而,根據我國《勞動合同法》的相關規定,非全日制用工具有兩個顯著特性,即協議的口頭性和協議解除的即時性。據此,從用工單位的立場看,在非全日制用工滿足生產經營需要的前提下,與全日制雇傭相比,非全日制用工既可以節約勞動合同的締約成本,也可以降低勞動合同的解約成本。這也是《勞動合同法》出臺以來,非全日制用工數量劇增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如果非全日制用工范圍明確,勞動者權益得以周延保護,非全日制用工數量的增加不應受到批判,但令人遺憾的是,前提并不成立。考察我國《勞動合同法》可知,同為非典型用工方式,勞務派遣規范更加細致,尤其是明確規定了勞務派遣的適用范圍。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非全日制用工適用范圍則完全未設防,令人費解。《勞動合同法》僅以區區五個條文對非全日制用工做出了規范,只是以日工作時數和周工作時數為標準回答了什么是非全日制用工,而對用工的特殊性和勞動者具體權益維護則缺乏關照。這就造成了非全日制用工范圍實際上的不當擴大,可以說,很多用工單位基于用工成本考慮,濫用了非全日制這一用工形式,這也對勞動力市場秩序維護和勞動者權益保護構成了威脅。
(三)解雇保護力度不足
根據《勞動合同法》的相關規定,非全日制用工環境下,雙方當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隨時通知對方終止用工。于用人單位而言,無需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這就意味著,用人單位有權以零成本的方式隨時解除與非全日制勞動者簽訂的勞動合同,而不論該合同是口頭協議或者書面合同。盡管該法也規定,非全日制勞動者可以和兩個以上用人單位建立非全日制勞動關系,然而考慮到勞動力市場的實際以及勞動者的時間和精力的有限性,勞動者面臨的解雇風險和壓力是巨大的。非全日制下法律賦予用人單位的即時解除合同權利,與全日制勞動關系下用人單位勞動合同解除權受到嚴格限制形成了巨大反差。如果再考慮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下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給付之差,社會公眾只會認為非全日之用工確實“低人一等”,這顯然不是立法者的初衷。雖然理論上說非全日制勞動者也可以即時解除勞動合同,似乎很公平,但是考慮到勞動者本身的弱勢,這種公平徒具形式意義,實質上對勞動者極不公平。社會經濟發展到今天,用人單位的彈性化用工需求應該得到滿足,用人單位壓縮用工成本也無可厚非,但是如果過分犧牲勞動者的就業穩定性和勞動權益,不僅損害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也無助于用人單位實現長遠利益,最終結果將不是雙贏,而是雙輸。
三、我國非全日制用工立法的完善對策
(一)大力推行書面合同
關于非全日制用工的合同形式,在《勞動合同法》頒布之前,從中央到地方,態度并不一致,總體上有三種選擇。(1)允許采用書面或者口頭形式訂立勞動合同,例如《上海市勞動合同條例》規定,訂立非全日制勞動合同可以采用書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其他形式。(2)原則性要求采用書面合同形式,例如《關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問題的意見》、《深圳市非全日制用工的若干規定》和《江蘇省勞動合同條例》等文件均作出類似規定。(3)應當采用書面合同,例如《北京市非全日制就業管理若干問題的通知》規定,用人單位與非全日制從業人員自用工之日起以書面形式訂立非全日制勞動合同。由此可見,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是多數地方的共同選擇,原因也很簡單,因為書面勞動合同對于明確雙方權利義務關系,更好地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具有積極作用。因此,在考慮確定非全日制勞動合同形式時,應考慮非全日制工作的特點,其與一般全日制工作相比,更趨個別化與復雜化,為避免勞資雙方僅以口頭約定容易造成爭議,宜就工作內容、工資的給付、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等內容以書面明確訂立。
(二)縮小非全日制用工適用范圍
應該承認的是,確有少數勞動者綜合考慮工作和生活需要,主動選擇了非全日制工作方式,然而絕大多數的非全日制勞動者則是出于無奈。近十年來,非全日制用工數量激增,與立法上的缺失不無關系。基于我國勞動者整體保護水平相對較低、非典型勞動關系勞動者保護強度更弱的前提,以及勞動者介入非全日制用工關系更多屬于被動選擇的現實,有必要認真思考用人單位在滿足何種實質條件的情況下,有權以非全日制用工替代全職用工。誠然,這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但是富有建設意義,因為如果對于適用范圍沒有任何限制,于全職勞動者而言同樣會感受到相當的壓力——用人單位很可能將全日制勞動者轉化為非全日制勞動者。而非全日制用工方式的不當擴張及其對傳統勞動關系的威脅,顯然擾亂了勞動力市場的健康秩序,也影響到了勞動者對職業安定性的合理期待。目前,已經有學者開始關注非全日制用工的適用范圍。有學者認為:“對于非全日用工的適用不能放任,法律應當適當地設限,僅容許其在一定條件下采用。” 盡管這一提法在操作層面還有問題需要進一步明確,但方向無疑是正確的。
(三)完善解雇保護制度
從嚴限制用人單位的勞動合同解除權,已經成為各國勞動法律制度的通行做法。就非全日制用工而言,我國現有的解雇制度可以用三個詞來描述,即零成本、即時性和任意性,非全日制勞動者幾乎毫無權利可言。事實上,即使考慮非全日制用工制度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勞動力市場和用人單位的彈性化用工需求,這樣的結果也是不公平的。非全日制用工更多是市場選擇的產物,但如果放任用人單位自由行使勞動合同解除權,對勞動者而言則是危險和不責任的。根據國際勞工組織《非全日工作公約》第7條和第8條的規定,雖然允許存在特定的例外情形,但是非全日制工人應該受到解雇制度的適當保護。以這一精神為指導,我國《勞動合同法》為典型勞動關系設計的合同解除制度應該原則性適用于非全日制工人,操作層面需要注意的是,具有金錢給付內容的條款可以參照“可比全日制工人”執行,例如經濟補償金或者經濟賠償金的計算可以全日制工人應得金額為計算依據,按相應比例扣減。未來完善非全日制解雇保護方面還應關注如下幾點:首先,鑒于非全日制用工本身也存在無固定期限合同、固定期限合同和短期合同(例如1個月以下)之實際可能,解雇保護的強度可以遞減。其次,用人單位除滿足法定事由之外無權單方解除勞動合同,否則按違約處理,但期限很短的非全日制勞動合同可以作為例外。最后,《勞動合同法》只在職業培訓和競業限制兩個特定情形下允許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適用于勞動者的違約金,但并未禁止約定由用人單位支付違約金的情形,因此,如果用人單位與非全日制勞動者有此約定,應為有效。
注釋:
田野.非全日制用工法律規制的幾點思考[J].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2):27.
姜穎.勞動合同法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59.
李坤剛,喬安麗.我國非全日制用工制度完善研究[J].江淮論壇,2015(2):89.
田野.非典型勞動關系的法律規制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