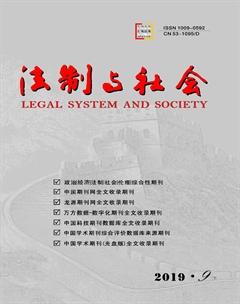近代中國租界法律制度及影響
摘 要 鴉片戰爭后,上海建立第一個英租界。租界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但客觀上起了試驗田的作用,為近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進行了預演和選擇。本文從比較租界與華界的法律制度入手,研究租界法律制度的影響,最后通過查閱文獻資料,研究外國人對租界法制的態度及看法,以期對租界法制有更全面的了解。
關鍵詞 租界法制 域外影響 評價
作者簡介:趙章宇,北京郵電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網絡法。
中圖分類號:D9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9.355
一、租界與華界法制比較
近代中國租界的法制現代化開始于19世紀40年代,半個多世紀后華界才逐步進入法制現代化。進入20世紀后,華界也開始學習和借鑒租界的法律制度,改變傳統法制,在法制改革之前,華界適用的仍是中國傳統法律制度。
(一)法治理念上的差異
租界法是現代法治,體現的是人人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現代法治理念。比如1854年上海土地章程的規定:不管是華人還是洋人要在租界內開設酒館賣酒都要先經過領事的批準,未經領事批準,任何人不得在租界內開店賣酒。
在20世紀之前的華界,仍適用傳統法制,體現的是德治、等級、不公平的理念。德治強調人的權威,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人治,在人治下,人人平等的理念受到沖擊。比如唐律中明確規定:“奴婢賤人,律比畜產”,“類同資財”。在《儀禮·喪服傳》中明確提出父為子天,夫為妻天,體現了封建等級制度的理念。
(二)法律形式和結構的差異
在法律形式上,租界使用最多的是章程,其次是通告。章程是租界的主要法律形式,內容豐富,體系完整,如上海租界1854年《土地章程》、1893年《工部書信館章程》、1866年《公董局組織章程》。以《公共租界工部局中式新房建造章程》為例,該章程規定的內容涉及房屋定義、設計圖紙、申請書、費用、測量員現場檢查的權利、特殊房屋、層數、加高地基、庭院地面和通道、廁所設施、墻壁、隔火墻、材料等多個方面。每一方面的規定也頗為詳細。
在華界,律是最主要的法律形式,例其次。《大清律例》是當時華界的主要法典。律作為一種法律形式,在中國社會具有很長的歷史,最早的律是商鞅制定的秦律。例發展至宋朝時比較成熟。律和例主要是為了滿足刑事法律需要而制定的,關于民事、行政等方面的規定較少。
在法律結構上,租界以條、款為主。比如上海租界的《公共租界工部局治安章程》,該章程一共有25款。此外,根據內容不同,每款下設條數也不同。《大清例律》包括七部分,“名例律”相當于總則,吏、戶、禮、兵、工、刑六律相當于分則,在正文里沒有明確詳細的條標,閱讀較為不便。
(三)法律語言的差異
租界和華界使用的法制語言也不同。租界法已開始采用現代法制語言,如1885年上海公共租界頒布的《巡捕房章程》,第十七項第一條規定了原告就被告原則,原被告都是中國人的經濟糾紛案件,應當由被告居住地方的會審公廨管轄。“原告”“被告”就是現代法語對訴訟當事人的稱呼。
與此同時,華界使用的是本土語言。如《大清律例》中規定:“婦人有犯奸盜不孝者各依律決罰其余有犯笞杖并徒流充軍雜犯死罪該決杖一百者與命婦官員正妻俱準納贖”。“笞杖”“徒流”“杖一百”就是中國傳統法制語言。“五刑”“十惡”“八議”等也是中國本土語言。
(四)審判制度的差異
租界推行的是現代審判制度,在會審公廨內進行司法審判。會審公廨制度涉及諸多方面,包括:法官和陪審員的選舉、原告和被告的資格、公訴人、代理人和辯護人的權利義務、翻譯人員的職責以及庭審程序等。
清末,有人描述傳統庭審的場景:嚴刑酷法下,地位又不平等,當事人心情很難傳達,案件隱情往往被忽視,而且斷案主要依據證人證言,主觀意識太強,難以發現案件實情。在中國傳統審判制度下,刑訊和冤獄屢見不鮮。
(五)律師制度的差異
律師制度來自西方,當時聘請的律師也多是外國律師。20世紀初,律師在上海租界庭審中廣泛出現:華人與洋人之間的案件數量顯著增多,不論是在領事公堂還是會審公廨,不管是華人控訴洋人的案件還是洋人控訴華人的案件,律師都在其中大放異彩。庭審中,律師的影響顯著提升。無論案件大小,當事人闡述事件經過,律師辯論是非對錯,法官審訊而依公判案,律師的出現是對司法公正的極大促進。
以前的中國只有“訟師”。關于中國古代的訟師,黃六鴻在其書中這樣寫道:“被告抄入手,乃請刀筆訟師,又照原詞多方破調,騁應敵之虛情,壓先功之勁勢。”訟師的主要職責是幫當事人撰寫起訴被告或應答的文書、將庭審的順序以及需要仔細的部分告訴當事人,訟師與律師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到清朝,訟師活動受到了政府苛刻的打壓。在清政府看來,如果沒有訟師,官府審理案件的數量會減少很多,審理的速度更快,效率更高而且街坊之間也會更為友善。雖然不可能根絕訟師活動,但清政府的限令訴訟活動確實起到了打壓作用。
二、 租界法制的域外影響
租界法制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不能一概而論。一方面,它使中國受西方侵略的程度更深,中國司法主權不斷喪失被掠奪;另一方面,它推動了西方先進法律制度在中國的傳播,對中國傳統法律制度造成了巨大的沖擊。這種影響不僅在租界內產生,還波及到華界。
(一)法律制度的傳播
以1903年在上海發生的蘇報案為例,章士釗等人在蘇報上發表多篇評論,宣傳革命思潮,但因蘇報坐落在上海公共租界內,租界當局要求清政府對蘇報有關人員的審理必須在租界內進行,即清政府必須在租界內以原告身份對章士釗等人提起訴訟,第一次,清政府與幾名文弱書生在一個普通法院展開一場特殊的訴訟。
在中國法制史上,會審公廨是一個具有復雜色彩的詞匯。一方面,會審公廨體現了強者對弱者的欺凌,是列強在中國治外法權的延伸,是國家在法制方面自主管理權被掠奪的結果。另一方面,會審公廨仿佛一扇窗,讓國人看到另一種法律制度及理念,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觀看者和參與者的法律意識,激發著一代又一代人追求先進法治。
同時可以看出,會審公廨所帶來的西方法律制度不僅對租界內人們造成影響,還影響到了租界外的人們包括清政府及官員。像在蘇報案的庭審中,清政府就聘請了外國律師打官司。在以往清政府的衙門中不被允許發生的許多事情,如被告不下跪,直呼皇帝名諱,重復宣讀謀反言論,這些都在清政府參與的庭審中實實在在的發生了。西方法律制度的引入對日后華界法律制度的建設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清朝一御史透過西方法律制度看到中國執法權與司法權不分的缺陷,在向皇帝上奏的奏折中提出:大清應向中國租界學習,將司法獨立于行政。這也成為當時推動華界法制體制改革的一份重要力量。
(二)法制意識的增強
1873年發生在上海的楊月樓案,是清朝末年四大具有傳奇色彩的案件之一,不同于其他三樁命案,楊月樓案是婚姻案。能與其他三案并列為清末四大奇案,楊月樓案主要奇在三點:一是婚姻當事人、雙方母親、甚至知悉此案的民眾都知道清朝法律不允許良民和賤民兩性結合的規定,但楊月樓和韋阿寶依然在雙方母親都認可的情況下下聘禮訂婚;二是楊月樓案實際上是典型的良賤為婚案,但上海縣令卻將其判為“誘拐罪”,且刑罰過重,典型的輕罪重判;三是本案在全國范圍引起轟動,上至慈禧太后,下至普通百姓,都關注本案。
在楊月樓案之前,上海也存在良賤為婚的事例,卻不像本案一樣鬧得舉國皆知。因為西方法律思想最先從租界傳入,對當時華界的影響較小,封建等級制度仍根固于人心,若發生本案,人們大多會支持進行嚴懲。此外,官方不嚴格依照《大清律例》進行判罰也有深層次的社會原因。在楊月樓案發生前,受西方法律文化影響,上海存在很多良賤為婚的案例,所以本案中民眾對楊月樓與韋阿寶的婚姻并沒有明顯的否定態度。可是良賤禁婚這一規定存在的基礎是封建等級制度,這一規定被否定,其實是對封建等級制度的否定。而本案在《申報》等多家紙媒的關注下,鬧得沸沸揚揚,官方對楊月樓案的判罰不僅是對本案,更是對這一類案件的態度。透過楊月樓案,不難看出西方法律文化對傳統法律思想的沖擊,以及在這一沖擊下,現代法律思想蓬勃發展。
(三)推動華界法制進步
租界適用租界法,華界適用華界法,兩種性質不同的法律并非完全沒有交流。比如在上海,同一個城市,不僅有本土的華界法,還有移植來的租界法,一條河阻隔不了人們的來往,也同樣阻隔不了兩種法律的相互影響。華界法對租界法也有影響,比如現代警政機關都稱為“警察局”,但在上海租界,使用的名稱卻是“巡捕房”,這名稱就借鑒了清朝的“巡捕營”這一機構的名稱,為了方便華人使用,故把行政執法機關稱為“巡捕房”。但總體來說,在法律制度上,華界對租界雖有影響,但租界對華界影響更甚。
上海華界與上海租界緊緊相鄰,最易受到租界法的影響。例如最直觀的感受,城市規劃與管理。上海租界內實行的是現代的城市管理制度,街容整潔,干凈有序。在20世紀初,上海華界開始借鑒上海租界城市規劃與管理的做法,建立的機構“上海南市馬路工程局”“開埠工程總局”“馬路工程善后局”等都借鑒了“工部局”的名稱,其職能對城市規劃與建設的各領域覆蓋也頗為全面,“戶籍管理、門牌編排、地產登記、捐稅收支、平抑米價、查禁鴉片、違警事件及一般民刑案件的受理等等”,也與“工部局”相類似。
三、外國人對租界法制的態度
租界法制是在近代中國特定背景下產生的,人們對它的感情色彩也比較豐富。有人強調它開了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先河,也有人專注于它對中國司法主權的侵害。隨著接觸資料越來越多,我們可以參考外國對近代中國租界法制的態度,以對租界法制有更加客觀全面的評價。
(一)對租界法制的評價
上海英租界建立不到20年,英國就在上海設立了駐華法院。美國也不甘落后,20世紀初在上海建立了享有領事裁判權的美國法院。1906年,美國通過了《設立美國駐華法院并限定其管轄權的法案》,以該法案為基礎,美國在上海租界內設立了駐華法院。在談及設立駐華法院的初衷時,美駐滬總領事說道:中國審判案件的傳統深刻體現了“人治”的色彩,法官審理案件并不嚴格追求證據的真實性以及認定案件事實的合理性,往往依據個人感覺,作出的判決帶有濃烈的主觀色彩。這是中國審判領域的慣例,帶有極大的缺陷,但是清政府審判者深受審判傳統的影響,而且審判者自身素質的高低也會影響案件審理的公正。英國政府發現了這個弊端自然不能坐視不管,而且在中國設立英國法院有利于提高英國在中國乃至亞洲的地位,提高英國在世界的影響力。可見,外國在租界設立法院,雖然其根本目的是擴大自身影響,獲取并維護在華利益,但其言行無不道出外國人對中國傳統法律制度及租界法律制度的否定。
在司法活動中,也存在很多嚴重問題,以法租界為例。巡捕房在法租界兼有執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的職能,是維護社會治安的中流砥柱。巡捕房地位舉足輕重,但其組織管理卻十分松散。巡捕房職員中有不少幫派分子,比較出名的有黃金榮、程子卿等,背景復雜,魚龍混雜。當租界內出現涉及華人的案件,而巡捕房又不好直接出面解決時,巡捕房就可以借助幫派的力量,用不正當手段解決問題。外國人也見證了租界內不少這樣的違法事件,并且說這樣的行為在租界剛適用現代法制的時候屢見不鮮。
(二)租界內外國人的法律行為
19世紀50年代,西方律師制度傳入中國,但中國本土此前并不具有律師制度,因此律師制度在租界甫一落地,所有律師都是外籍律師。律師最先在上海租界進行活動,但是人數稀少,后來隨著西方法律制度在中國影響的進一步擴大,這一群體也日益壯大,并且在人們生活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租界內律師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擔任法律顧問,提供法律意見。如1876年,工部局準備在租界內設立性病醫院,制定了方案并準備公布。關于該方案,董事會總董特地去尋問了時任工部局法律顧問連厘的意見。連厘從合法權力和道德兩方面進行考量,提出與董事會不同的意見,并被董事會采納。工部局時常會與租界居民發生矛盾和沖突,每當此時,同樣會向法律顧問尋求幫助以解決問題。據《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記載:“1863年6月,工部局聘用律師,律師每年的費用為100兩銀子……到1899年,工部局法律顧問的年薪增至2500兩,另外還發給出庭酬金。”這些數據表明,法律顧問在工部局的地位日益提高,成效顯著。
但租界內外國人并非都奉公守法,一些違法行為屢見不鮮。最典型的就是外國領事違反明文規定,肆意干涉審判,使規定得不到切實的實施,如1905年發生在上海的“黎黃氏案”。黎黃氏丈夫在四川為官,因病去世,黎黃氏的公公時任廣幫董事,特請同鄉送黎黃氏母子帶著靈柩回廣東。黎黃氏帶著孩子、婢女(有買賣契約為證)乘坐班輪途徑上海時,在碼頭被拘捕,以“拐盜罪”被押至會審公廨受審。當時,關絅之擔任租界內會審公廨的主審官,他經過審理認為黎黃氏不是拐匪,證據不足,拐騙罪不能成立。但參加陪審的英國副領事德為門認為,按照英國的法律與習慣,黎黃氏的拐盜罪應當成立,因此他堅決要求拘押黎黃氏。中外官員為此爭執許久。德為門甚至公然喝令西捕進入公堂搶人,黎黃氏最終被押于捕房西牢。
這起案件充分體現了外國領事強權政治,無視租界法律規定,將會審公廨看做自己的審判機構,肆意妄為。會審公廨也正如他們所說,成為“由外國人控制下的會審公廨”。比如:純屬華人的案件理應由中國主審官獨審,不需要外國領事陪審,但是他們憑借強權,不僅強行陪審,還時常妄下判決,與中國法官產生矛盾和沖突;中國法官的任命應當由中國政府自行決斷,外國領事卻強加干涉,此外,還干涉罪犯的傳提與判決的執行等。法國駐滬總領事拉達曾說過:“依照我的看法,它(指領事裁判權)十分適合我國在上海的僑民。他們人數不多,但是所從事的商業活動卻很重要。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我們應積極地支持他們,對抗人數眾多、資金雄厚的敵人,而不能處處加于掣肘。”言下之意就是,為了保護本國國民的利益,領事會做出有利于本國國民的判決。
四、結語
租界的產生有著獨特的社會背景因素,中國人與殖民者之間政治權利和地位不平等,植入租界的西方法律制度實際上更偏重保護外國國民利益,這些都成為租界司法有失偏頗的重要原因。租界有些法律規定形同虛設,有些在實行中奉行的是雙重標準,對華人與洋人區別對待。正如保羅·科恩所言:移入租界的西方法制終是浮于表面之物,不可能直接讓中國實現根本性的法制改革,中國真要實現法制的現代化,還有賴于全民法制意識的覺醒。實現真正的法律變革,必須正確看待法律在社會中的地位、法律的作用、法律的價值和法律制度本身。雖然租界法制帶來的作用有限,但不置可否,它打開了國人看往世界的窗,為法制改革提供了學習藍本及前車之鑒。
參考文獻:
[1]費成康.中國租界史[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47頁.
[2]王紅梅.會審公廨司法審判權的“攫取”與“讓渡”——會審公廨移交上海總商會調處民商事糾紛的分析[J].甘肅社會科學,2011(1),第153-157頁.
[3]陳同.略論近代上海外籍律師的法律活動及影響[J].史林,2005(3),第20-38頁.
[4]盧瑋.近代上海法律歷史文獻整理與狀態研究——以當代滬上四個圖書館藏調研為基礎[J].河北法學,2013(8),第152-157頁.
[5]王立民.中國租界法制研究的檢視與思考——以近30余年來的研究為中心[J].當代法學,2012(4),第134-145頁.
[6]江立云.中國租界立法制度初探[J].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4,12(3),第53-58頁.
[7]李寧.清末四大奇案之楊月樓案研究[D].鄭州大學,2016年,第6-27頁.
[8]胡震.清末民初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法權之變遷(1911-1912)[J].史學月刊,2006(4),第51-56頁.
[9]王振偉.上海法租界司法制度與實踐之探析[D].華中科技大學,2010年,第6-15頁.
[10]李洋.美國駐華法院研究[D].華東政法大學,2014年.第171-182頁.
[11]楊帆,于兆波.會審公廨與中國法制進步——以一名美國律師的記錄為視角[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1(6),第19-22頁.
[12]姚遠.“合作政策”與上海公共租界的誕生[J].歷史教學問題,2015(4),第102-1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