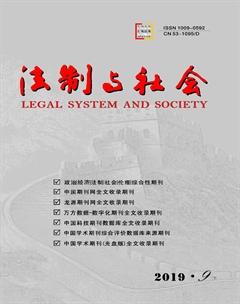幫人取錢后暗中隱匿部分現金并實施欺騙而將現金據為己有的定性分析
摘 要 隨著現代經濟生活財產占有方式的多樣化,侵犯財產罪的表現形式也日益復雜。侵占罪、詐騙罪、盜竊罪中排除權利人對財物的占有支配關系不能僅從形式上判斷,而應根據各自的本質特征評價:侵占罪的本質特征在于對非本人財物由獨立性“合法持有”轉化為“非法占有”;詐騙罪的本質特征在于“騙取財物”,即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手段使財物權利人陷于或維持認識錯誤而處分財物最終排除權利人對財物的占有支配關系轉由行為人或第三人非法占有;盜竊罪的本質特征在于“竊取財物”,即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竊取”手段排除財物占有人、支配人對財物的占有支配關系平和轉化為行為人或第三人非法占有。
關鍵詞 侵占 詐騙 盜竊 占有 支配
作者簡介:常子吉,河南省南陽市臥龍區人民檢察院檢察二部助理檢察官。
中圖分類號:D92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9.268
一、基本案情
2018年9月26日,河南省南陽市臥龍區某鄉75歲的王某收到在外地工作的兒子為其郵寄的二萬元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匯票,因其不懂匯票如何取款,便請本村的張某幫忙。9月28日,二人一起到鎮上的一家郵政儲蓄銀行營業所,在門前王某將匯票和本人的身份證交于張某并在營業所門外等候,張某獨自一人前往取款窗口將二萬元全部取出,但在大廳內張某暗自將其中一萬元裝入自己的內衣口袋,出大廳見王某后,張某把一萬元交于王某并對王某謊稱:“在此處的營業所僅能取出一萬元現金,另一萬元須到其他郵政儲蓄銀行營業所方能取出。”緊接著,張某佯裝接電話有急事為由乘機離開。2018年12月,王某查詢銀行得知匯票記載的二萬元已全部被取走,便向張某追問,張某承認此款由其持有但多次推諉不予歸還,王某遂報案,該案案發。
二、爭議觀點
對張某幫王某取出匯票記載的二萬元后暗自隱匿一萬元并對王某實施欺騙最終將一萬元據為己有的行為如何定性,爭議頗大,主要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張某的行為構成侵占罪。理由是張某將代為保管的王某的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拒不退還。
第二種觀點認為:張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理由是張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了代王某僅取出匯票記載的二萬元中一萬元的事實、隱瞞了私自隱匿另一萬元的真相,致使王某上當受騙損失一萬元而被張某長期非法占有。
第三種觀點:張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理由是張某先暗自隱匿其取出的匯票記載的為王某所有的一萬元,后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將該一萬元非法占為己有。但張某的欺騙行為是實現其隱匿財物的暗中狀態不被發覺和非法占有王某財物的必經階段和必要手段,張某的全部行為是暗中排除王某對財物事實性的占有支配關系而轉由本人非法占有,這符合盜竊罪“竊取財物”的本質特征。
三、個人意見
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張某幫王某在郵政儲蓄銀行營業所取出匯票記載的二萬元后暗自隱匿一萬元又采取欺騙的方法據為己有的行為應定性為盜竊罪。
(一)張某的行為不成立侵占罪
侵占罪是指將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或他人的遺忘物、埋藏物占為己有,拒不退還,數額較大的行為。該罪的行為對象分為兩種:一種是保管物;一種是遺忘物、埋藏物。本案中,王某基于對張某的信任而委托張某到鎮郵政儲蓄銀行營業所取出匯票記載的二萬元,張某基于委托授權在銀行營業所柜臺窗口取出了全部錢款。整個過程的自始至終王某既未明示也未默示張某保管該款的全部或其中的任何一部分,按王某的本意和一般的社會觀念可以推定:王某是欲讓張某將匯票記載的二萬元全部取出后在最短的時間內安全交于本人。雖然從營業所柜臺取出二萬元后到出大廳見王某之前這一短暫時間內張某有暫時持有和管理所取錢款的權利,但這并不等于張某具有保管的權利和義務。另外,按法律規定和一般社會觀念,全部的二萬元現金系委托事項所指向的對象,任何一部分均都不能被認作為已由張某代為保管,因此,張某取出的二萬元現金不屬于保管物。并且,二萬元現金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不可能被王某所遺忘,即不可能是遺忘物,更非埋藏物。因此,張某在郵政儲蓄銀行營業所代王某取出的二萬元或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均不屬于保管物、遺忘物和埋藏物,張某占有的對象不屬于侵占罪的犯罪對象。
其次,侵占罪的本質特征是行為人將本人合法持有的非本人財物由“合法持有”轉為“非法占有”。本案中,張某取出二萬元后有義務及時向王某如實報告委托取款的完成情況,更有義務將所取的全部錢款盡快在最合適的地點安全轉交于王某,張某無權對代取款項的任何部分長期占為己有。以一般的社會觀念推定:自張某從柜臺取出二萬元的那一時刻起,王某對全部二萬元現金就具有事實性的支配關系。張某在營業廳內暗自隱匿一萬元,出大廳后以本次在本處僅取出一萬元的虛假事實欺騙王某進而將一萬元據為己有,該藏匿行為、欺騙行為、長期不歸還行為均違反了誠實信用的民事活動原則及《合同法》第404條 “受托人處理委托事務取得的財產應當及時轉交于委托人”的規定。在取出全部錢款后的短暫時間內,雖然現金尚未被王某直接占有而由張某臨時持有,但因王某對全部錢款具有事實性的支配關系,張某對現金僅為臨時性輔助占有,臨時性輔助占有不等于獨立的“合法持有”,在社會觀念上,張某對現金不具有占有權。在無法律規定和雙方約定的情況下,張某通過暗自隱匿和虛構事實的欺騙方法將一萬元據為己有,此時張某對一萬元現金的持有已不再具有合法性而具有非法性。即從張某取出二萬元現金到隱匿其中一萬元再到欺騙王某進而將一萬元長期據為己有的整個過程看,張某對王某所有的財物由“占有輔助”到“非法持有” 再轉化“非法占有”;僅從張某暗自隱匿王某所有的一萬元到以欺騙方法實現對該一萬元的長期占有這一環節看,張某對王某的財物由 “非法持有”轉化為“非法占有”。不論是從整個過程還是從局部環節來看,張某的行為不符合對非本人財物由獨立性“合法持有”不法轉化為“非法占有”的侵占罪的本質特征。
張某的行為對象和行為特征與侵占罪均不符合,故張某幫王某取出二萬元后暗自隱匿一萬元又以欺騙的手段據為己有的行為不成立侵占罪。
(二)張某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
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公私財物的行為。從靜態上看,詐騙罪的行為人主觀上是故意且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手段是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結果是行為人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財物而致被害人損失財產;本質特征是“騙取財物”,即行為人采取背離客觀事實的言行使財物的占有權人陷于或維持認識錯誤而 “自愿”將財物轉移給行為人或第三人占有。本案中,王某基于信任委托張某取錢而將匯票交于張某,張某從銀行取出全部現金之前并未對王某實施欺騙行為,在大廳門前王某將匯票交于張某只是二萬元現金記載體的轉移,財物本身并未發生轉移。因此,該交付匯票的過程既無欺騙行為,也未發生財產轉移。張某取出二萬元后暗自隱匿一萬元又實施欺騙而將一萬元據為己有的這一過程雖有欺騙行為,但張某對王某的欺騙不以直接獲取一萬元為首要目標,而是為了維持其藏匿財物行為的暗中狀態不被王某覺察所采取的必要手段,該過程雖然存在張某對王某的欺騙,但一萬元現金的轉移不是由張某的欺騙行為所引起,即張某雖實施欺騙但并未因欺騙獲取財物。
王某向張某交付匯票的過程中張某既未實施欺騙也未取得財物、王某的一萬元現金被轉移占有的過程中張某雖實施了欺騙但并未因欺騙獲取財物,這不符合詐騙罪“騙取財物” 的本質特征。
從動態上看,一個完整的詐騙過程包括以下不可分割的環節:行為人實施欺騙行為(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財物的權利人因欺騙陷于或維持認識錯誤而 “自愿” 將財物轉移占有、行為人或第三人獲得財物導致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以上各環節之間必須是引起和被引起的因果關系,否則不成立詐騙罪。若行為人雖實施虛構和隱瞞行為,但財物權利人并未因欺騙陷于或維持認識錯誤而將財物轉移占有,即財物被轉移占有并非是因行為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所引起,則不能將行為人的欺騙行為認定為詐騙犯罪。
案例中,張某取出二萬元現金后臨時起意產生了非法占有一萬元的目的,為此其實施了暗中隱匿和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行為,從而最終獲取對一萬元的長期非法占有導致王某遭受相應財產損失。從表象上看,這種欺騙行為與詐騙犯罪極其相似,但從因果關系看,張某虛構的本次僅取出一萬元現金和隱瞞的另一萬元現金尚未被取出的虛假事實并未引起王某自愿將一萬元無償轉移給張某長期占有,因為王某認識錯誤的內容只能是:此次張某在本郵政銀行營業所只取出一萬元,另一萬元尚未取出仍由王某本人實際支配控制,只是須到其他郵政銀行儲蓄所方能取出。基于此,王某不可能也從未主動做出無償轉移本人全部或部分現金給張某的行為。因此,一萬元現金被轉移由張某長期占有并非是因張某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所引起,即財物占有權的轉移和欺騙行為之間無引起和被引起的必然因果關系,這不符合詐騙罪構成環節的因果關系。
張某獲取財物的過程不符合詐騙罪“騙財”的本質特征,張某將一萬元現金據為己有的過程也不符合詐騙犯罪構成環節之間的因果關系,故張某的行為不成立詐騙罪。
(三)張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
盜竊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竊取他人占有的數額較大的財物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扒竊的行為。
首先,盜竊罪的行為人主觀是故意且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本案中張某暗自隱匿代王某取出匯票記載的本屬于王某所有的一萬元現金后又以欺騙的手段據為己有、被追要時推諉不還,張某主觀上當然是故意且以非法占為己有為目的。
其次,盜竊罪的行為方式是“竊取”。“竊”的字面意思是“暗中”“以不正當手段取得”;“取”的字面意思是“拿”“獲得”;因此,“竊取”的字面意思就是“暗中以不正當手段獲得”,即行為人采取不被發覺的方式以不正當手段獲得。“不被發覺”是行為人的自我意識,是行為人自認為不被人知曉,至少不被財物占有權人發現和覺察,而且這種不為人知的自我意識貫穿于竊取行為的始終。“暗中”表明行為人對財物及對財物的權利人均未實施強制手段,“竊取”行為具有平和性。
本案中張某為獲取王某所有的一萬元先將一萬元現金暗中隱匿于自己的內衣口袋,后以謊言相欺,最后推諉拖延不予歸還。張某暗自隱匿現金的行為是張某自認為不可能被王某發覺,事實上最初王某果真未察覺,這完全符合盜竊罪“竊取”的行為特點。后張某對王某實施欺騙的目的是欲讓王某相信在此處的郵政儲蓄銀行營業所本次只取出一萬元現金,其余的一萬元仍由王某支配和控制,在銀行營業廳門口王某已確信如此。這導致王某當時和此后較長時間內不能知曉張某藏匿現金的事實,因此,張某欺騙王某的目的是欲使其隱匿行為的暗中狀態長期化,是其竊取財物后繼續維持非法占有狀態不被王某所知曉,故張某的欺騙行為是“竊取”行為的延續和補充,是最終完成“竊取他人財物” 的必經階段和必要手段,該欺騙行為并未引起王某作出轉移財產占有的處分行為,也未侵犯新的法益或增加“竊取”行為的侵害范圍,因此,張某的欺騙行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而是被“竊取”行為所吸收,不能另行評價為詐騙罪,也不能評價為侵占罪,故張某實施的全部行為僅能評價為盜竊罪一罪。
再次,盜竊罪的本質特征是違反財物占有人、支配人的意思,將不在行為人支配范圍內的他人財物以竊取的手段平和地轉變為本人或者第三人占有。“占有”是對物事實性的支配控制關系,既包括完全占有和不完全占有,也包括對物直接控制的直接占有和具有返還請求權的間接占有,還包括臨時性的短暫占有和長期性、永久性占有等。在物理空間范圍內由權利人控制支配的物由權利人占有,在權利人所處的空間范圍之外依據一般的社會觀念推定由權利人支配控制的物也由權利人占有。
本案中,匯票記載的二萬元在取出之前由王某事實支配與控制,王某對該財物具有返還請求權,二萬元現金由郵政儲蓄銀行直接占有,由王某間接占有;張某取出后未交給王某之前由張某臨時輔助占有,此時王某對該二萬元也具有返還請求權,二萬元現金仍由王某事實性間接占有。案例中張某暗自隱匿所取二萬元現金中的一萬元又以謊言欺騙王某從而將一萬元占為己有且不予歸還,該行為實質是違反王某的本意以竊取的方法排除王某對一萬元的事實性占有支配關系平和地轉變為由張某長期完全直接占有,這仍是以竊取的手段和平地轉移財產的占有支配關系,完全符合盜竊罪的本質特征。
最后,從盜竊罪與侵占罪、詐騙罪的區別來看,張某的行為不成立侵占罪、詐騙罪而成立盜竊罪。
其一,盜竊罪和侵占罪的主要區別在于作為犯罪對象的財物是否已經由犯罪行為人先行占有以及行為人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實施非法占有行為的時間不同。行為人對非本人財物先合法占有后非法據為己有為侵占,行為人對非本人財物先以非法占有目的實施“竊取”后轉化為本人或第三人占有則為盜竊。案例中,從張某在銀行柜臺取出王某的二萬元現金到出大廳見王某的這一短暫時間內,表面上張某雖持有二萬元現金,但依據社會觀念,王某對二萬元具有事實性的占有支配關系,是現金的實際占有人,張某只是財物的占有輔助者而不是占有者,全部現金或其中的任何一部分未被張某先行獨立占有。在大廳內張某暗自隱匿一萬元后又以欺騙的手段據為己有的這一環節,張某先以非法占有目的實施“竊取”后以欺騙方法據為己有。總之,縱觀張某行為的全過程,張某對王某的財物并非是先合法占有后非法據為己有,而是先以非法占有目的實施“竊取”后以欺騙的方法據為己有,因此,對張某的整個行為不能評價為侵占罪而應認定為盜竊罪。
其二,盜竊罪和詐騙罪的主要區別在于各自的本質特征和被害人的認識因素不同。在本質特征方面,盜竊罪是“竊取財物”,詐騙罪是“騙取財物”。當財物已處于行為人占有時,二罪區分的關鍵在于:若行為人以不正當的手段暗中排除權利人對財物的占有支配關系從而建立新的占有支配關系為盜竊;若行為人采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手段導致財物占有權人主動處分財物從而改變占有支配關系則為詐騙。如前所述,案例中王某失去本人事實性占有支配的一萬元而轉由張某長期直接占有,根本原因是張某實施竊取行為所致而非張某編造的謊言所造成,故張某的行為不符合詐騙罪“騙財”的本質特征,而符合盜竊罪“竊財”的本質特征。在認識因素方面,通常情況下,盜竊罪的被害人是在不明知的情況下失去對財物的占有,詐騙罪的被騙人是在明知甚至參與轉移占有的情況下失去對財物的支配與控制。本案中,在取款之前王某主動將匯票交于張某只是二萬元記載體發生了轉移,現金的全部或部分并未轉移。此環節張某明知和參與的只是匯票本身的轉移而非現金的轉移;二萬元現金被取出后,張某先暗自隱匿一萬元后實施欺騙行為,該一萬元被轉移占有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不為王某所知。因此,從張某取出二萬元現金到最終將其隱匿的一萬元現金據為己有的全過程,王某始終未做出參與轉移財物占有的任何行為。張某欺騙行為的實質是其完成盜竊既遂后以虛假言行實施的掩藏行為。總之,王某對一萬元失去占有既非明知也從未參與,這不符合詐騙罪被騙人“明知”的認識因素而符合盜竊罪被害人“不明知”的認識因素。故從被害人的認識因素看,張某的行為不成立詐騙罪而成立盜竊罪。
總之,張某幫王某取出匯票記載的二萬元后暗中隱匿一萬元并對王某實施欺騙從而將一萬元長期占為己有的行為應定性為盜竊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