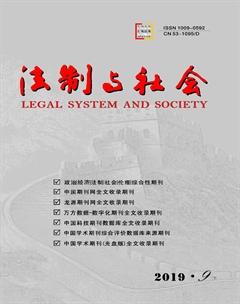受虐兒童法律保障研究
摘 要 我國是聯合國《兒童權利保護公約》的締約國,對防治兒童遭受虐待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目前,我國在一般法律規定和兒童權益立法中均存在有關受虐兒童的禁止性規定。受虐兒童的相關法律制度有強制報告制度、告誡制度、安置救助制度以及監護人變更制度等。根據現有制度可發現我國對于受虐兒童的法律保障體系存在不足,如現有兒童虐待防治的立法不夠完善,對虐待兒童行為沒有明確界定等。結合我國現狀,為有效減少虐童事件的發生,我國應當明確界定兒童虐待范圍、建立處理虐童案件的專門機構,完善兒童收養與寄養制度等。
關鍵詞 虐待兒童 法律保障 兒童權益
作者簡介:陳靜,華北理工大學,碩士,研究方向: 民商法。
中圖分類號:D92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9.339
一、我國受虐兒童法律保障部分重要制度
目前我國《反家庭暴力法》中對于兒童遭受虐待進行了相關的法律規定,主要是對兒童遭受來自家庭的暴力予以規制。反家庭暴力法不僅強調預防為主,尊重受害人真實意愿,特殊保護等五項原則 ,而且對家庭成員虐待兒童的報告制度、對施虐者的告誡制度、臨時安置救助制度以及監護人變更制度等都有所規定,對于兒童權益的保護至關重要。
(一)強制報告制度
我國的《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四條和第三十五條共同對家庭人員虐待兒童的強制報告制度進行了規定,報告主體包括幼兒園、醫療機構、居民和村民委員會、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等,受理報告的機關為我國公安機關。若發現虐童事件后未盡到報告義務,應依法給予處分。也就是說,法律規定應當報告的主體對于發現受虐兒童的事件,其報告行為為責任和義務,而不是權利。強制報告制度僅要求發現兒童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程度,即應當報案,明顯的擴大了報告程度的要求,對虐待兒童的行為盡早干預,防止事情惡化,促進虐待兒童干預體制的完善。
(二)告誡制度
《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六條和第十七條規定了兒童遭受家庭暴力時的告誡制度,這是此法的創新之處。當家庭暴力沒有造成嚴重后果時,其所造成的后果也達不到治安管理處罰的程度,公安機關則應當對施虐者給予一定程度的批評教育或者出具告誡書。告誡書的內容應當全面具體,對施虐者的身份信息、兒童遭受虐待的事實、對施虐者禁止實施虐待等內容均應體現在出具的告誡書上。公安機關出具的告誡書,應送達基層自治組織,即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等,由基層自治組織對施虐者、兒童及其監護人進行查訪工作,保護受害人。《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條明確了告誡書的證據效力,以認定家庭暴力的事實。
(三)安置救助制度
當兒童在家庭中遭受家庭成員虐待,身體受到嚴重傷害,或者面臨人身安全威脅時,可以通過公權力的介入將兒童從危險狀態中解救出來。根據《反家庭暴力法》的規定,兒童遭受虐待后,公安機關有義務幫助受虐兒童脫離危險境地,包括通知并協助民政部門將受虐兒童安置到臨時救助機構,為受虐兒童提供臨時的生活幫助,法律援助機構也應當依法為遭受虐待的兒童提供法律援助。
(四)監護人變更制度
我國的《反家庭暴力法》中規定了受虐兒童的監護人變更制度。實踐中,兒童在家庭虐待中遭受的大多數暴力來源于其監護人,兒童在遭受其監護人虐待后,兒童的近親屬、居民委員會、縣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等有關人員或者單位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依法撤銷監護人的監護資格,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兒童具體情況另行指定受虐兒童的監護人,使兒童脫離原監護人,以保障兒童的健康安全。在《民法總則》中,明確規定了學校、醫療機構、婦女聯合會、殘疾人聯合會、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等對受虐兒童的監護人變更請求有同樣的申請資格,這就意味著擴大了有權申請主體的范圍。當然,受虐兒童相應的撫養費用其被撤銷監護資格的原監護人仍然需要繼續負擔。
二、我國受虐兒童法律保障的不足
(一)對虐待兒童行為沒有明確界定
對于兒童虐待,世界各國均存在最低共識。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國際兒童福利聯合會(IUCW)均對虐待兒童行為進行了明確規定,日本在《兒童虐待防止法》中對虐待兒童的范圍進行了明確界定,美國大部分州對于兒童虐待也進行了具體界定。雖然對于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群體對于兒童遭受虐待的界定范圍有不同的理解,但大部分國家均從兒童利益最大化出發,明確界定了兒童受虐的范圍。與之相比,我國對于受虐兒童的定義并沒有明確性規定,這就使諸多虐童的行為沒有被明確的指出,兒童遭受虐待認定困難,很難將兒童從危險境地中解救出來。
(二)缺少兒童虐待防治的專門性法律保護
《兒童權利公約》中規定:“締約國承擔確保兒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需的保護和照料,考慮到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任何對其負有法律責任的個人權利和義務,并為此采取一切適當的立法和行政措施”。 我國為《兒童權利公約》締約國,但同美國和日本等締約國相比,我國未制定針對受虐兒童法律保障的專門性法律,我國主要的兒童受虐保障制度包含在《反家庭暴力法》中,但《反家庭暴力法》只針對家庭暴力,并屬于對婦女、老人的附屬性規定,缺乏針對性。在《憲法》《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義務教育法》等其他法律法規中也分散著部分有關兒童虐待的相關規定。在我國,兒童遭受虐待后,在報告、受理、調查及處理這一系列過程中,并無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規予以指引,這給我國的虐待兒童防治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不便。
(三)專門調查與處理機構和制度的缺失
我國缺少針對兒童虐待的專門處理機構,也缺少專門的調查與處理制度。目前我國有不少對于兒童保護的部門、組織,比如國務院婦兒工委、教育部、民政部、公安機關、共青團以及婦聯等,但職責過于分散,缺乏主責部門協調,對兒童的保護工作碎片化,無法提供一系列連續性和專門化的服務,各機構之間缺乏聯系與協調,容易出現監管空白的情況,不利于對兒童保護的信息進行整合。我國目前兒童遭受虐待的調查和處理機關為公安機關,但公安機關并非專門的調查與處理機關,其警力本身有限,無法做到日常監管,并且針對兒童遭受虐待并沒有專門的調查處理流程,也無專門處理兒童案件的工作人員,這就導致虐童事件接到舉報后,不能及時的對加害人與受虐兒童進行調查,且兒童相對于婦女、老人來說更加脆弱,自我保護意識較差,就會使兒童遭受虐待后不能及時的得到救助,因此,設立針對受虐兒童專門調查處理機關與制度至關重要。
三、完善我國虐待兒童法律保障的對策建議
(一)明確界定兒童虐待的范圍
當前,各國對兒童虐待均存在最低限度的共識。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國際兒童福利聯合會(IUCW)對兒童遭受虐待的范圍均進行了界定。日本在《兒童虐待防止法》中對于兒童虐待也有明確的界定。對兒童的虐待有多種,對兒童的忽視和情感虐待在世界范圍內均屬于虐待行為,但我國現有法律只對兒童遭受身體虐待和性虐待有所規制,對于精神虐待和忽視并沒有明確的規定,當兒童遭受忽視和精神虐待后,沒有可執行的制度保障。結合部分域外國家對兒童虐待的綜合理解和我國現實情況,對兒童虐待行為的界定可包含以下要素:(1)兒童年齡應為18周歲以下;(2)虐待的類型應包括:身體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與忽視。明確界定兒童虐待的范圍,可使得行政機關的調查及介入等更為明確,對虐待兒童的行為也能得到更好的規制。
(二)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對受虐兒童進行專章保護
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美國的《兒童虐待預防和處理法案》和《兒童保護方案》以及日本的《兒童虐待防治法》均為針對兒童設立的對于兒童免遭虐待權的保護。《兒童權利公約》中規定,各國家在制定法律或者實施其他一切有關兒童的行為,都必須考慮兒童的最大利益。這一原則是對兒童權利的保護、避免兒童遭受虐待的最有利原則。健全的立法是對于兒童權益的根本保障,針對我國不存在兒童虐待的專門性法律保護問題,可以將分散的有關兒童保護的法律法規整合起來,對兒童虐待的定義、強制報告制度、調查處理程序、保護組織、政府參與等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中作出具體規定,以對受虐兒童進行專章保護,也可使相關機構和人員在處理兒童虐待案件時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三)建立處理虐童案件的專門機構
20世紀60年代以來,各國包括機關單位和社會公益組織相繼成立了專門處理和預防兒童虐待的組織或者機構,主要服務于接受兒童行為的報告,開展和調查以及虐待兒童保護所等。在美國,聯邦政府衛生與公共服務部設有兒童與家庭局,各級州政府設有專職的兒童保護服務機構,主要的調查機構即是社會服務機構,在大多數州,社會調查機構被要求在接到兒童遭受虐待的報告后24小時內展開調查,對虐待家庭開展工作。從前文可知,目前我國的公安機關、民政部門、共青團和婦聯等雖然承擔一定保護兒童的職責,但是沒有主責機關的協調,所發揮的作用相對有限,這種“多頭保護”的模式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兒童保護工作的邊緣化、兒童保護工作的碎片化等,因此,設立專門的兒童虐待處理的專門機構對兒童遭受虐待的防治至關重要。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可以在我國設立專職的兒童保護機構,在國務院設立兒童保護委員會,作為部級單位,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市、縣級政府設立相應級別的兒童保護委員會,將分散于婦工委、民政部、婦聯等各機構有關兒童權益保護的職權歸攏起來,由兒童專門委員會統一行使。為兒童提供專門的保護,能夠避免兒童受到“二次傷害”,使兒童能夠在健康的環境中成長。
注釋:
即對家庭暴力零容忍的原則;共同責任原則;預防為主,教育矯治和懲處相結合的原則;特殊保護的原則;尊重受害人意愿,保護當事人隱私的原則。
《兒童權利公約》第三條第2款:締約國承擔確保兒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需的保護和照料,考慮到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任何對其負有法律責任的個人權利和義務,并為此采取一切適當的立法和行政措施。
參考文獻:
[1]喬東平.虐待兒童:全球性問題的中國式詮釋[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2]于占國.我國防治兒童虐待法律制度的建立與完善[J].法制博覽,2015(11).
[3]吳鵬飛.我國兒童虐待防治法律制度的完善[J].法學雜志,2012(10).
[4]劉向寧.當務之急和制度構建:從南京虐童案看兒童虐待強制報告[J].中國青年研究,2015(9).
[5]張桂云,韓伯靳,趙晉.從“南京虐童案”看兒童權益保護措施的完善[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6(3).
[6]錢曉峰.兒童虐待國家干預機制的構建[J].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4(6).
[7]李本燦.虐童的刑法規制及兒童福利體系的構建[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8]裴斐.完善兒童虐待防治法律問題研究[J].當代青年研究,2013(6).
[9]何劍.論“虐童”行為的刑法規制[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3(2).
[10]胡巧絨.美國兒童虐待法律保護體系介紹以及對我國的啟示[J].青少年犯罪問題,2011(5).
[11]韓文婷.簡述國外刑法關于虐待行為的規定[J].法制與社會,20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