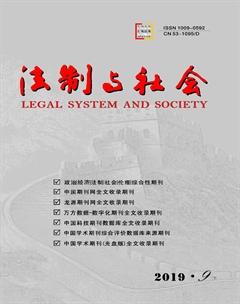人工智能生成物在著作權法下的定性問題研究
吳宇琪 王黎
摘 要 對人工智能生成物在著作權法下的定性問題研究,應該意識到當今社會是人工智能呈現噴涌性發展態勢的時期,但其相關知識產權的定性與保護仍存在較大漏洞。若想要得到《著作權法》的承認與保護,關鍵在于探討人工智能能否作為其保護的特體。所以,應該對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獨創性進行分析。同時,是否為智力成果也是成為客體與否的必要要件之一,本文通過剖析人工智能生成過程的技術角度和私法原則角度論述此問題。
關鍵詞 人工智能生成物 獨創性 智力成果 鄰接權
基金項目:“雙一流”建設專項(2019國創)項目代碼:GK000002000819122。
作者簡介:吳宇琪、王黎,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法學系本科生。
中圖分類號:D923.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9.342
一、問題的提出
2016年末至2017年初,谷歌“阿爾法狗”以60勝0負戰勝數名圍棋界高手,讓社會各界見識到人工智能的威力。目前中國人工智能領域已經覆蓋工業機器人、服務機器人、智能硬件等軟件與服務層,智能客服、商業智能等軟件與服務層,視覺識別、機器學習等技術層,數據資源、計算平臺等基礎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出現更是將人工智能技術延伸到一個更“人化”的領域,2009年柯普發布了由人工智能機器“EIM”創作的第一張音樂專輯《明由暗生》,到2017年5月,微軟(亞洲)互聯網工程院公開了機器人小冰創作的首部詩集《陽光失去了玻璃窗》出版發行的消息,并且聲明小冰的版權。科技發展到今日,我們不得不意識到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權屬問題。
著作權法設立的目標是承認和賦予權利人對作品的權利歸屬的認定與使用權力的保障,同時圍繞作為著作權主體的人展開。作品具有獨創性地表達,被認為必須源自人的思想感情,即為智力成果。以往傳統的機器創作是完全按照設定的程序生產出預先設定的產品,僅限于按設定的程序機械地對信息進行抓取與整合。以往機器人創作作品的方式是簡單的介入性方式,人工智能創作方式與其大相庭徑,不再是簡單的抓取與整合,而是可以在技術和算法的支持下進行整理。20世紀90年代,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國家將人工智能生成物納入了版權法范疇予以研究,日本知識產權本部通過建立類似像商標法那樣的保護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新的注冊制度。
綜上可見,探討人工智能的主題性問題首先應考慮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獨創性。其次,將人工智能生成放在著作權體系下衡量,其是否可以認定為智力成果,應從技術角度與司法判例角度論證。最后,針對現人工智能生成物在知識產權法中面臨的困境,提出相應的可行性建議。
二、人工智能生成物不具有獨創性
(一)從康德哲學角度論述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獨創性
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開啟了“以人為本”“人是目的”的理論研究,康德看來,人作為主體是有意識有目的的,其余的客體只是一種工具,而人是目的。同時,自由是人的本質,享有自由是人擁有尊嚴的前提,人作為主體應當是自由、獨立的,在認識論中人才是中心。最后,自我意識是人所具備的,人處于支配與處置地位,人高于地球上一切其他非理性動物。“人是目的”絕對命令的核心,人是其命題的核心,是出發點。該命題揭示出人因有理性而神圣,康德認為世界存在兩種“存在者”,一種是無理性的存在者,與人的意志無關,只能作為手段。另一種是理性的存在,他們為“本身的目的”。人工智能雖說具有自主生成的能力,但在現有的社會中,若將人工智能看作為這個世界的一個主體,享有理智與自由,進而成為這個世界的目的,是這個世界上的一切對人工智能有價值,所有都是實現人工智能的手段包括人,這顯然是有違于正常的倫理綱常的。
最后立足于康德哲學中“人是目的”的哲學命題,將人從單純因果必然性中解放出來,自然界中的存在物,只有對人才有價值,離開了人,所有的東西都無所謂價值。無論人工智能發展到什么階段,人工智能只能被看作為手段,若是將人工智能看作是“人”,賦予其主體性,讓其也成為這個世界的目的,而人類變為手段,變成人工智能的“奴隸”,這必然是有違于道德的。
(二)從人類智慧能力角度分析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獨創性
人類智慧最充分的表現就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而不斷發現問題、定義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隱形智慧能力”是指人通過知識、審美、感官等抽象能力而獲得的。而解決問題的能力則是人類智慧中最具操作性的,因此被稱為“顯性智慧能力”。這兩種能力相互聯系、相互支持、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人類智慧整體。
至今,人工智能生成物還未具有獨立意識,它執行的主要是設計者的意志,是基于人預先設定好的程序、算法、規則以及模型,人工智能的學習方式有些類似于人腦的“深度神經網絡”以及“深度加強學習方法實現的,其生成方法可以近似于我們通常所說的題海戰術,通過大量的接受信息,進而將這些信息儲存在數據庫中,當進行生成活動時,僅僅利用以往學習到的、存在于數據庫中的數據與算法和規則進行創作,所以在面臨相似類型的生成問題時,人工智能就會用相似或者相同的算法使用相似或相同的數據生成相似或相似的生成物。因此暫時,人工智能生成過程還不能被看作為具有獨立意識,因而不能視其具有獨創性。基于此學說,目前人工智能的發展階段僅能涉及到對“顯性智慧能力”的模仿與建構上,人工智能系統內的程序化運作現完全依賴于事前設定好的程序、規則和算法,并不能體現其主觀性以及目的性。
三、人工智能生成物不能構成智力成果
(一)從生成技術角度論證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可以構成智力成果
智力是人類所獨有的,智力成果必須來源于智力創作,同時智力成果是構成著作權法下所保護的客體的關鍵要件。下面將從人工智能生成技術角度論述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為智力成果。人工智能參與作品的創作主要運用了目前人工智能領域中的通用技術——機器學習,而機器學習的基礎在于算法。在國際通說認為,整個人類的認知過程可以看作是由人工神經網絡組成的一個統計學的學習機器,它能把外界的信息進行抽象轉化為一個最終輸出,進而來模擬人類的大腦神經網絡。機器學習是令計算機獲取新知識和技能,并識別現有的知識和學問。而人工智能生成技術主要運用的是機器學習中的“深度學習”,其動機在于建立、模擬人腦進行分析與學習的神經網絡,來模仿人腦的機制來解釋數據。人工智能不同于傳統的機器生產,它不僅僅是應用算法來直接獲取結果,但對于相同的原始資料,人工智能會采取相同的策略,即應用相同的算法,因此其并不是通過智力有個性、有思考、有選取的活動。其生成過程具有極大的重復性,它們僅僅是在處理從人搭建的現有作品數據庫中檢測到、錄入過的現有作品中通過相關算法進行創作。
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物并不能作為著作權法中的智力成果。同時,人工智能基于基礎學習與深度學習,最終可以實現脫離既定的算法來生成內容,所以有的學者認為這使得將人在算法上預設的數據與算法無法作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智力來源。
(二)從法理角度分析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構成智力成果
但是基于法理學的基本原理,權利主體與權利客體不僅是相對應的,所有權利客體均來自權利主體。也就是在法律關系中,權利客體從屬于權利主體。在權利歸屬條件中,著作權法中也規定其保護主體應當為公民。著作權法中保護的客體是與著作權主體是從屬關系的,也就是說著作權法中的作品,也就是智力成果的外在表現形式是作為作者的客體的。權利主體與客體的嚴格劃分和轉換禁止,法理上完全否定主體在任何情況下被視為支配對象的可能。人工智能實質上仍屬于物品的范疇,盡管相應的算法與數據賦予其自主生成的能力,但在倫理上仍應將其納為物的范疇,所以其并不具備在法理學上的權利主體的構成要件。若將人工智能生成物作為智力成果,就是肯定人工智能可以作為權利主體,進而可以表示為機器與人具有相同的法律資格與地位,則就是進一步證明了人工智能可以作為權利主體,同時人工智能又可以作為統一法律關系中的權利客體,這是對現有法理學原理的顛覆。
四、將人工智能生成物納入著作權法保護客體的不合理性
立法層面,人工智能的性質與我國《著作權法》中關于主體的定性相違背,在我國《著作權法》中,明確規定著作權人應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而屬于計算機的人工智能在進行智力創作時,人所起的作用僅僅是具有輔助作用的,因此在《著作權法》下人工智能并不能得到相應的保護。
法理方面,但是基于法理學的基本原理,權利主體與權利客體不僅是相對應的,所有權利客體均來自權利主體。權利主體與客體的嚴格劃分和轉換禁止,乃是絕對支配性帶來的必然結果,法理上完全否定主體在任何情況下被視為支配對象的可能。但若是將人工智能生成物作為《著作權法》的客體時,人工智能就不能作為此法律關系中的權利主體,因此人工智能就不能得到保護。
現實應用方面,人工智能生成物不能得到有效的權利保護,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輕易獲得和濫用,因為在現今的情況下,人工智能生成物為”孤兒產品”,沒有明確的定性與版權所屬,會使人工智能的設計者的智力勞動成果得不到保護,進而影響其創作熱情,影響我國的創新發展。
五、結語
目前人工智能技術雖已經具有極快的發展速度和較高的發展水平,但是人工智能生成技術仍不能具有獨立意識,現在的技術主要研究領域僅僅涉及到了“顯性智慧能力”,而最能體現人類智慧的解決問題的“顯性智慧能力”在人工智能生成技術中并未得到進展性研究,就是說人工智能生成技術仍僅停留在依賴于事先設定的程序與數據。同時,人工智能生成技術雖說現在已經發展到“深度學習”的階段,但它不僅僅是應用算法來直接獲取結果,但對于相同的原始資料,人工智能會采取相同的策略,即應用相同的算法,因此其并不是通過智力有個性、有思考、有選取的活動。其生成過程具有極大的重復性,它們僅僅是在處理從人搭建的現有作品數據庫中檢測到、錄入過的現有作品中通過相關算法進行創作。所以不能將人工智能生成物看作《著作權法》中保護的作品。但是,根據我國尊重知識產權的需要,對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權保護不能始終空白,因此本文觀點為應新設鄰接權來完善《著作權法》中對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權保護的困境。但是,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相關領域的實際情況也在不斷發展變化,故新設鄰接權這一單一措施還遠遠不能解決相關問題。本文僅通過論述相關方面表達筆者的相關看法,還望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
[1]楊駿,黃堃,李宓.“阿爾法圍棋”再揭秘[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7- 01-06.
[2]陳靜.人工智能怎樣改變我們的生活[N].經濟日報,2016-05-05(11).
[3]微軟小冰.陽光失了玻璃窗[EB/OL].http://www.ithome.com/html/next/309780.htm,2017-12-10.
[4]美國國家版權局.工作手冊[Z] .美國:U.S.Copyright office,2014年版.
[5]德國著作權法[M].范長軍,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版.
[6]智能創作作品該不該有著作權[EB/OL].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2016-04-18.
[7]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總論[M].王曉曄,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8]溫純如.認知、邏輯與價值: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新探[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9]康德.實用人類學[M].鄧曉芒,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年版.
[10]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基礎[M].孫少偉,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
[11]鐘義信.人工智能:“熱鬧”背后的“門道”[J].科技導報,2016(7).
[12]王遷.論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在著作權法下中的定性[J].法律科學,2017(5).
[13]蔡自興,蒙祖強.人工智能基礎(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14]黎橋.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在著作權法之下的法律保護問題研究[D].浙江: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