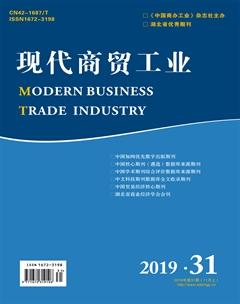江南的坐商與嶺南的行商探討
2019-10-21 09:41:14潘彤
現代商貿工業
2019年31期
摘 要:江南文化與嶺南文化迥然不同,江南文化孕育了精致儒雅的坐商蘇商,而嶺南文化同樣滋潤了不懼艱難,敢于天下先的行商粵商,蘇商留下了江南園林和“蘇南模式”;粵商也奉獻了“嶺南會館”和“廣交會”。他們都為我國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關鍵詞:江南;坐商;嶺南;行商
中圖分類號:F2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31.062
1 江南與坐商
每年6月,當江南梅子由青綠轉成黃的時候,太湖都會籠罩在一種淫雨絲絲,溫高氣密的梅雨季節。雨絲棉如銀針,簌地鉆進水里、田間或人們心里,洇化開來,成了江南的“梅子黃時雨”。
江南地處太湖流域,跨江臨海,平原迂闊,水網密布,湖泊眾多,長江橫穿東西425公里,京杭大運河縱貫南北718公里。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自古就是人口密度最高、百姓安居樂業的地區,在歷史上素有“魚米之鄉”的美譽。江南曾經是六朝等多朝代的都城所在地,在經歷了漫長的經濟和文化中心的轉換后,嬗變成為“靈秀鐘毓,人文薈萃 ”之地,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重農、崇文、重教、堅韌、柔美、秀麗、重商、開放、兼容的江南水鄉文化 。清晨頭頂竹笠,梅園摘熟,撐一支油布傘,挑一擔黃梅酒,吱吱嘎嘎走上青石板鋪就的街巷,傍晚一挑柴米或是油鹽、花布,微醺而歸。這樣的江南意境,造就了獨特的蘇商文化。
長江下游溫濕多水,使得人性柔;以插秧植稻、養蠶繅絲為主的生產方式,使人心細精致;而自南宋以來經濟文化的迅猛發展,又使得江南人崇文重教、亦商亦儒的風氣濃厚。……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