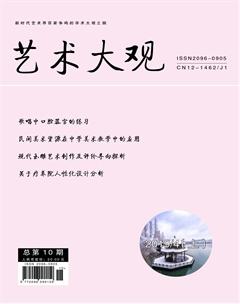梅州客家“香花佛事”舞蹈的民俗文化研究
田園


摘要:民俗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承載著人們的生活習慣及情感信仰,而民俗舞蹈以舞蹈本體為媒介,極具感染力地傳遞著民俗文化的特定主旨及內涵意蘊。本文基于梅州梅江區人生禮儀活動香花儀軌的田野調查,以儀式中呈現的香花佛事舞蹈“打蓮池”“鐃鈸花”“鯽魚穿花”為研究對象,探析其所蘊含的民俗文化價值。
關鍵詞:“香花佛事”舞蹈;民俗舞蹈;民俗文化
引言
民俗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以民俗事象為載體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潛移默化的流傳于民間。民俗舞蹈是人們在特定的表演場域、相對穩定的民俗活動中所進行的族群情感的外在表現,人們用身體語言記錄整個儀式活動過程,傳遞其特定的主旨及文化意蘊。
一、梅州客家“香花佛事”舞蹈與客家民俗文化
民俗舞蹈是一種民俗文化現象,表征在身體之上,依存于民俗事象,經過歷史積淀形成的傳統印記,需要把它放置于特定的語境中闡述舞蹈本體,分析其自身所具備的民俗文化價值。民俗舞蹈和民俗事象聯系最為密切的是歲時節日、人生禮儀和信仰民俗。梅州地區由香花僧侶在齋主家中操持的佛教形式,在梅州上水地區、下水地區(以梅縣丙村為分界線,在丙村以上的梅江區和梅縣諸鄉鎮,為上水派;在丙村以下的梅縣諸鄉鎮,以及蕉嶺、大埔等縣均為下水派)一般被稱作“香花佛事”“香花儀軌”,它既是佛教度亡儀軌,也是梅州客家人重要的人生儀禮。
香花儀軌是具有濃郁客家民俗文化特征的宗教儀式部分,包括靜態的念唱經文的音樂表演及動態的技藝規范的舞蹈表演,借助舞蹈的動作姿態表演形式,為逝去亡者頌德祝福、寄托哀思,傳遞出民俗內涵及佛學理念,香花儀軌真正實現著“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佛前皆懺悔”的心靈超升。
二、道具舞蹈:鐃鈸花
鐃鈸花,是香花儀軌中一項技藝性較高的器械舞蹈,其傳承過程中與本土文化環境相融合,形成了獨具梅州客家地區特色的民俗表演形式。“鐃鈸花”一般在場外進行,表演者僧侶或齋嫲主要依靠銅鐃鈸、一根筷子、竹竿等道具舞出花樣繁多的表演套路,其表演過程無唱念經文,而是伴隨節奏明晰的鑼鼓聲,僧人或齋嫲于一席之地,拋舞鐃鈸,舞蹈具有強烈的生活氣息、農耕文化的色彩,其目的主要是調節場面氣氛。
(一)舞蹈動作
僧侶或齋嫲表演“鐃鈸花”的動作套路源自客家人對于自然景物的模擬與生存生活的再現,蘊含佛學理念,兼具社會功能。“鐃鈸花”表演時主要使用的是銅鐃鈸,其道具為圓形,從道具中便可窺探客家民眾意欲表達對傳統文化觀念的重視,追求生命的延續,體現佛教“六道輪回”的理念。僧侶或齋嫲表演“短紅蓮”“長紅蓮”“觀音坐蓮”等動作套路時,配合著舞蹈的點步、轉身步、馬步等步伐與毫光指、鼎指等手勢,使表演凸顯藝術性,蘊含佛學意味,表演套路中極具感染力的“秕谷逗雞”“猴子挑水”等,是客家人從自然界的形態中提煉創造而成。筆者實地田野采風時,其“拋接鐃鈸”的動作令人過目不忘:慈云宮的齋嫲與北巖寺僧侶皆于各自的草席上,一同進行表演,表演時僧侶及齋嫲深蹲積蓄力量,緊接跳起時迅速將鐃鈸拋向10多米高的空中,民眾們的視線皆隨鐃鈸而去,在鐃鈸即將落地前的一剎那,僧侶及齋嫲將其平穩接住,頓時現場響起陣陣掌聲。“拋接鐃鈸”的表演過程不僅體現客家人對佛神的恭敬之意,且具有宣泄眾人內心情感、告慰亡者、凝聚族群的功能。
(二)舞蹈性別
“鐃鈸花”在梅州地區大部分由僧侶表演,齋嫲極少數。“鐃鈸花”所用的銅制鐃鈸約2公斤重,用它來完成各種繁多的動作,其難度可想而知,且表演的時間長度均在一個小時左右,有時甚至長達一個半小時。筆者在與北巖寺住持的交談中,了解到北巖寺僧侶傳承的“鐃鈸花”技藝從十幾歲已開始練習,幾十年的反復打磨才將其技藝完全掌握,而且并不是每一位僧侶都能學有所成,磨煉過程需要僧侶具備持之以恒的耐力以及細心鉆磨的精神,掌握動作要領,將“鐃鈸花”的技藝深入至舞蹈本體的記憶中,最終領悟并表現其所蘊含的深厚文化內涵。
三、隊列舞蹈:鯽魚穿花
“鯽魚穿花”在香花佛事舞蹈中屬于歌舞并進的隊列舞蹈,通過鑼、引罄等器樂的聲響節奏與僧侶們的舞蹈相互配合,極具觀賞性。據《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廣東卷》記載,“鯽魚穿花”源于僧人見鯽魚結隊嬉戲玩耍而有所啟發,于是將其編排出來,通過舞蹈的隊列變化達到勸慰生者及調控莊嚴肅穆氛圍的目的。
(一)舞蹈動作
“鯽魚穿花”主要通過腳下的步伐和調度變化來進行舞蹈表演。在實際演出的過程中,主牽著會依據場地情況,帶領僧侶及齋主進行調度,創造出豐富多樣的隊列,靈活運用圓場步、小跑步、橫磋步等步伐來比擬生活中的不同情態;通過“川花起式、雙龍聚珠、鯽魚靠背”等舞蹈隊列的多樣變化,使舞蹈兼備觀賞與娛樂的功能。“鯽魚穿花”雖是由主牽著帶領,但僧人及齋主也可隨性發揮自身的無限想象空間,使其隊列變幻。筆者實地采風時,“鯽魚穿花”的舞段就并未按部就班地進行表演,其過程凸顯幽默風趣:一小僧人本是尾隨隊列,忽而轉變方向打亂調度變化成為主牽著,帶領齋主圍著觀音壇追逐奔跑;忽而舞步釀蹌與其他僧侶相撞,引得在場客家民眾陣陣發笑,頓時緩和肅穆的場景氛圍。“鯽魚穿花”的舞蹈隊列變化不僅是僧侶智慧的結晶,彰顯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魅力,同時起到安慰生者的心靈,重拾生者對生活、對生命的信心。
(二)舞蹈性別
“鯽魚穿花”對于舞蹈表演者的性別沒有嚴格的要求,男女皆可進行表演。但在香花儀軌中,僧侶進行主持表演的為多數。香花僧侶在隊列舞蹈中,會模仿社會生活中各類人物的步履神態,雙腿膝蓋微屈時身體仍平穩前進;模仿跛子的“跛子步”,一條腿保持挺直,拖步向前;模仿老人的“老人步”,蹣跚而細碎的步履,踱步向前。“鯽魚穿花”需模仿多種低姿態及屈曲的步伐,以及整個舞蹈場面的調度掌控也需多年的實踐經驗,因而較少有女性擔任主牽著。
四、綜合性舞蹈:打蓮池
“打蓮池”是綜合佛曲、文學、儀式、唱詞、舞蹈于一體的香花佛事舞蹈。影響廣泛的上、下水香花舞蹈“打蓮池”,不僅外在的舞蹈隊列呈現出形式美感、舞蹈道具蘊含佛學理念,其舞蹈背景所闡述的目蓮救母故事也彰顯出客家民眾推崇備至的孝道精神。“打蓮池”舞姿獨特、意蘊深長,在傳承發展過程中,與客家民間其他的藝術形式互相融合,形成了梅州客家地區特有的民俗文化。
(一)舞蹈動作
“打蓮池”的舞蹈動作承載著佛學理念及客家民俗文化。“打蓮池”的整體氛圍較為莊嚴肅穆,并沒有花哨繁多的動作樣式,而是運用其特有的手勢及道具,呈現出古拙凝重的舞蹈動作。“打蓮池”中最具代表性的手勢是“毫光指”,毫光指由胸前向外繞腕而出,表達了由心而出的特定佛學內涵。表演過程中,手臂帶動毫光指劃弧線上抬至胸前,再向外拉伸至肩側的動作姿態,頗為古雅質樸,具有客家女性溫婉的審美特征。“打蓮池”的道具有錫杖、光竹、珠杯等。通過舞動錫杖八字劃繞、雙膝并攏貼地的“掄舞杖花”動作及雙腿呈八字跪地的“橫杖跪拜”動作凸顯出凝重古樸的風格,表示對開光功德的佛神的禮敬。光竹,作為道具法器,被賦予“可莊嚴佛事、供奉如來、增延佛壽”等文化內涵,其表演過程中,齋嫲或僧侶手執光竹,對空書符、舞香背香的動作彰顯出佛教度亡的嚴肅莊敬。雖“打蓮池”動作簡潔質樸,但其舞之重點在于 “意”,而不在于“形”,“打蓮池”的動作即體現了所謂舞為心聲的含義,通過“唱、舞、念、做”的形式,表達了客家人的民俗祭祀信仰。
(二)舞蹈性別
“打蓮池”是專為超度女性長者亡魂的,僧侶及齋嫲都是其表演者,但在“打蓮池”的發展變遷過程中,齋嫲逐漸成為其主要的操行者。據梁伯聰《梅縣風土二百詠》記載“循行無復舊規模,竟以親喪講樂娛。特取腥膻招蟻附,大家來看靚齋姑,自注曰:近來喪家禮佛懺,廢男僧,用齋姑,新興花樣有《打八角蓮池》等名目。”顯然齋嫲在傳承“打蓮池”中逐漸起到主導地位。齋嫲在舞“打蓮池”時,以蓮池盆為中心,進行五位八方的八字圓調度,彰顯優美流暢、“和”的美學特征,象征佛教的六道輪回思想,生命去來往復,猶如“圓”的回旋,周而復始,無有不便,同時蘊含著較強集體凝聚力的文化內質。
五、結語
作為一種活態傳承的文化,客家香花佛事舞蹈體現出敬慰亡者、孝悌精神、族群凝聚力等功能,寓意著生命過程的連續性,追求的是生命的生生不息,表現萬物皆輪回的思想。并以其獨具特色的方式宣揚著深厚的民俗文化,極具寶貴的研究價值。
參考文獻:
[1]李春沐,王馗著.《梅州客家佛教香花音樂研究》[M].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02.
[2]梁伯聰.《梅縣風土二百詠》,1944年10月抄本,梅縣地區檔案館1985年復印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