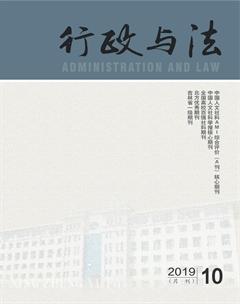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城鄉關系演變的內在邏輯
摘 ? ? ?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的城鄉關系發生了深刻的歷史變遷,城鄉關系有了顯著的改善。縱觀新中國成立70年來城鄉關系演變的歷史進程,與自然順序下城鄉關系有序循環相比,城鄉關系演變顯現出獨特的內在邏輯。其中,不斷縮小城鄉發展差別是城鄉關系演變的本質追求,改革和進一步深化改革是城鄉關系演變的不竭動力,而基本經驗是進一步實現城鄉關系變革。本質、動力和基本經驗構成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城鄉關系由分割走向緩和再逐步走向融合的邏輯主線。
關 ?鍵 ?詞:城鄉關系;發展道路;動力機制;基本經驗
中圖分類號:D630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7-8207(2019)10-0012-10
收稿日期:2019-08-30
作者簡介:李剛(1971—),男,吉林長春人,中共吉林省委黨校(吉林省行政學院)決策咨詢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理論與實踐。
城鄉關系一直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最重要的關系,始終是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條件及共同富裕的目標取向決定了我國城鄉關系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有其獨特的內在邏輯,顯現出有別于自然順序下城鄉關系有序循環的特點。因而,分析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城鄉關系演變的本質、動力和基本經驗,探究隱含在城鄉關系演化過程中的內在邏輯關系,有助于理解新中國成立70年來實施縮小城鄉差別的政策措施,闡釋城鄉關系演進的動力機制,尋找貫穿始終的基本經驗。
一、縮小城鄉差別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城鄉關系演變的本質追求
縮小城鄉差別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要求。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社會主義條件下城鄉關系是平等的關系,但由于歷史原因,鄉村傳統的生產方式尚未得到很大改變,城鄉之間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差別還很大,[1]消除或者縮小城鄉差別,特別是城鄉之間的經濟與社會差別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城鄉關系演變的本質追求。
(一)探索中國特色的鄉村發展道路,縮小城鄉經濟差別
我國城鄉經濟差別最顯著的特點體現在生產和交換環節上。長期以來,農村居民從事第一產業,城市居民從事二三產業,農業從業數量多但創造的價值低,城鄉之間存在顯著的勞動生產率差別。新中國成立以后,造成城鄉之間階級對抗的原因已經消失,社會主義社會的城鄉之間矛盾性質是非對抗性的,屬于人民內部矛盾,[2]但由于歷史原因形成的城鄉經濟差別并沒有消失,為了逐漸縮小城鄉差別構建新型城鄉關系,開始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和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工業化道路,探索城鄉之間產品與要素公平交換方式進而縮小城鄉經濟差別。
⒈探索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縮小城鄉生產效率差別。新中國成立之初到1958年,農業現代化的顯著特點是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礎上實現合作化+機械化,形成的調整農業生產關系為主,發展農業生產力為輔的格局,開始采取自上而下的計劃生產方式,并在1954年首次提出了“農業現代化”的目標沿用至今。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到改革開放前,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形成了以人民公社為主的發展模式,農業現代化進入到曲折探索階段。改革開放以來到21世紀初,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形成了以市場化為主要方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賦予了廣大農民基本生產資料和生產決定權;逐步廢除糧食統購統銷制度,放活了農產品市場流通渠道;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出現與發展,解決了“小農戶”與 “大市場”脫節的矛盾,使廣大農民充分融入了市場經濟的大潮中。[3]2007年,黨的十七大首次明確提出 “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進入到新時代,在工業化與城鎮化道路的引領下,農業現代化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農業新型經營主體不斷成熟與發展,農業基礎設施不斷完善,農業生產的技術和技術進步加快,農業現代化進入到由數量增長到質量提升階段,綠色、優質、特色和品牌成為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目標。新中國成立70年來對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探索雖然在不同階段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但基本目標是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提高農業的價值貢獻,進而縮小城鄉勞動生產率差別。
⒉探索中國特色農村工業化道路,縮小城鄉產業差別。發展經濟學經典理論已經證明城市工業化是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而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主要路徑。與國外相比,中國城鄉關系的特殊性在于人口總量大,農村人口比重更大,有限的城市工業存量顯然無法容納眾多農村勞動力轉移,因此無法效仿發達國家走過的單一城市工業化的道路,[4]探索農村工業化的雙重工業化道路,縮小城鄉產業差別進而吸收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成為一種選擇。新中國成立初期就開始探索農村工業化道路。1958年,中共中央《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提出“人民公社必須大辦工業”。當時認為公社工業的發展,不但能加快國家工業化的進程,而且將在農村中促進全民所有制的實現,縮小城市和鄉村的差別。[5]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公社工業逐漸作為相對獨立的產業出現在農村,并將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向公社工業轉移。雖然在1960年對公社工業進行了調整,但是一些地區的公社工業不僅保存下來還有了進一步發展,并最終成為改革開放初期鄉鎮工業的雛形。以公社工業為代表的農村工業是縮小城鄉產業差別最早的探索,并為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工業發展奠定了基礎,積累了經驗。
改革開放以來,以蘇南地區鄉鎮企業為代表的農村工業化為我國農村產業結構調整作出了重要貢獻。鄉鎮企業以人民公社時期遺留下的鄉村集體工業為依托,一部分農民充分抓住國家放活經營體制的政策條件和短缺性的市場條件,打破了農村以傳統農業生產為主的結構,進而又帶動了流通、運輸、服務等第三產業在農村的發展,不僅使鄉鎮企業的概念外延到農村一二三產業,也成為國家工業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農村單一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模式,實現了一二三產業的協調發展,打破了城市辦工業,農村搞農業的二元結構,使城鄉經濟逐步融為一體,從而使20世紀50年代農村工業化從藍圖成為實踐,也為探索縮小城鄉經濟差別提供了一條特殊的路徑。[6]
⒊探索城鄉之間產品與要素公平交換方式,縮小城鄉交換差別。產品與要素交換是城鄉之間聯系的主要形式。城鄉之間相互交換工農業產品和要素過程中存在著顯著的交換方式差別是城鄉經濟差別的表現形式之一。新中國成立以后,城鄉交換差別主要表現為工農產品剪刀差,即工業產品向農村和農業銷售時高于其價值,農業產品向城市和工業銷售時低于其價值,進而在交換過程中形成工農產品剪刀差,進而利用工農產品剪刀差形成的資本積累支持城市和工業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后糧食等農產品統購統銷形成的工農產品剪刀差是產生城鄉交換差別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解決城鄉產品等價交換進而縮小城鄉市場交換差別等問題,1985年開始改革傳統的農產品購銷制度,在農村全面推行農產品合同訂購和市場收購的雙軌制。1993年,糧食統銷制度退出中國歷史舞臺;1998年,進一步實現了糧食購銷市場化和市場多元化改革。市場主體多元化,初步建立起符合我國國情、糧情的糧食流通體制,[7]也使得以傳統農產品城鄉市場交換差別逐漸消失。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鄉交換差別主要表現為土地要素市場不平等交換形成了新的城鄉土地價格剪刀差,政府利用低價從農村獲得土地再以高價對征用土地按照市場價格出讓進而獲得土地增值收益,形成了土地要素城鄉之間交換差別,絕大多數的農地轉用往往伴隨著土地所有權轉移,即土地征收或土地非農化。這一過程中,通常存在著征收價格與出讓價格之間的巨大差異,即土地增值收益,[8]同時,也出現了土地增值收益在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分配不均衡問題,農民的權益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和體現。為了進一步改革原有的農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提高個人收益”,進而改變土地交易過程中被扭曲的價格體系向有利于農民的分配方向改革。在不斷改革城鄉土地要素交換利益分配格局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探索在不斷明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權能關系的基礎上,讓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自由平等進入到城鄉土地市場,激活存量資產。2015年,國務院在全國15個縣區啟動了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工作,這對于進一步實現土地要素平等交換創造了條件,有利于逐漸縮小城鄉之間土地要素交換的差別。
(二)探索公共資源均衡配置路徑,縮小社會差別
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在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和固化階段,城市對城市工商業和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等主要由國家和企業完成,農村的公共基礎設施主要由集體和鄉鎮企業完成;在社會保障方面,城市形成了以就業為中心的、較為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農村則依托于人民公社形成了較低層次的生活保障體系,[9]進而在城鄉二元結構下形成了城鄉之間社會發展差別。新中國成立70年來,為了縮小城鄉之間在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等社會發展方面的差別,作為公共資源核心部分的公共財政,其覆蓋農村的范圍不斷擴大,從純公共產品逐步向準公共產品延伸,[10]逐步扭轉城鄉社會差別過大的局面。
⒈發展農村醫療衛生教育事業。由于長期以來城鄉二元分割體制,城鄉之間醫療衛生保障和教育政策迥異,有限的醫療和教育資源全部集中在城市,農村醫療保障和教育資源十分匱乏,城鄉之間的社會發展存在顯著差別。為了縮小城鄉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差別,1965年1月,中共中央轉批了《關于城市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配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防病治病的報告》,先后組織了1521個醫療隊深入到全國各地農村開展巡回醫療。在毛澤東同志著名的“六二六”指示當中提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中去。1965年以后,大批的城市醫療工作者奔赴到全國各地農村,并在新疆、山西、江蘇等省區開展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同時,為了進一步培養農村醫務人員,采取了支持醫學專科學校建設,加強農村衛生員培養特別是大力發展農村赤腳醫生等措施極大地改善了農村醫療衛生狀況。改革開放以來,在繼續加大對農村醫療資源建設的基礎上開始進一步深化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城鄉居民統一的醫療保障制度。我國社會醫療保障體系由城鎮居民醫保、職工醫保、新農合和醫療救助組成,即“3+1”模式。為了進一步提升農村居民社會醫療保障水平,我國實施了城鄉居民統籌、接續制度改革,逐步向“2+1”模式,即城鄉居民醫保+職工醫保+醫療救助轉型。[11]
為了縮小城鄉教育事業發展差別,新中國成立以后,全國各地農村普遍建立了“掃文盲字”班,并逐漸采用建立工農速成中學、農民業余學校、農民中學、農民中等專業中學、半工半讀的高等和中等農業院校等形式發展農村教育,提高農民教育水平。[12]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對農村基礎教育重視程度不斷提升,1983年,國務院《關于加強和改革農村學校教育若干問題的通知》中首次提出在農村普及初等教育的任務,農村教育開始了由“掃除文盲”向“普及教育”的轉變。到2005年,國家開始實施免除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學生的書本費、雜費,并補助寄宿學生生活費,2006年起已在全國推廣。“兩免一補”標志著城鄉基礎教育開始進入到均衡發展階段。
⒉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體系。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受到當時的條件限制,僅在城市企業當中率先建立了社會保險制度,占全國絕大多數的農民并沒有涵蓋其中,進而形成了養老保障制度的城鄉差別。改革開放以后,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開始在農村推行,直到1992年,隨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的出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正式建立并進入到探索階段,逐漸形成了“以家庭保障為基礎、社區保障為核心、商業型保險為補充”的蘇南模式和以社區保障為主的廣東模式等典型。國內其他地區也依托農村土地經營性收益開展了多種形式的社會養老保障實踐。這些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不足的局面,但由于保障水平較低、覆蓋面較小、共濟性差和缺乏可持續性等問題仍不能滿足絕大多數農村居民養老保障需求,因此,2008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構建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的目標。為了實現上述目標,通過不斷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在個別地區通過強化政府主導責任、多級資金籌集機制、循序漸進的城鄉保障水平的統一進程、城鄉社會保障之間的并軌和轉換等措施,以“循序漸進、小步快走”的方式較快地實現了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社會保障水平的大體一致。[13]隨著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試點逐漸深化并取得成功經驗,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提出 “要堅持全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方針,以增強公平性、適應流動性、保證可持續性為重點,全面建成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2014年,《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將新農保與城市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合并實施,并與城市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現銜接,進而實現了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全覆蓋。
二、改革和進一步深化改革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城鄉關系演變不竭的動力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城鄉關系演變是一個從二元結構向一元結構轉換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通過深化改革使城鄉關系經歷了由內到外的轉型,進入新時代,進一步深化改革使城鄉關系經歷了由外而內的轉型,進而促使城鄉關系由分割到緩和再走向逐步融合。
(一)改革使我國的城鄉關系由分割走向緩和
⒈改革農村經營制度,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1978年11月,以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實施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標志拉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隨著大包干等一系列農村經濟制度改革制度的實施,特別是土地承包到戶,農民獲得了用益權與支配自己人力資本及剩余產品的權利,農民生產積極性高漲,大大促進了農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農民收入獲得了快速提高。[14]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在大幅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的同時,農民家庭擁有的生產資料顯著增加,農村非農經濟的出現使農村產生了生產資料私有化和多種經濟并存的格局,[15]進而推動商品經濟在農村的發展,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經營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扭轉了貧困的狀況,起到了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目的,但以分散經營為主要特征的單戶經營難以形成規模效益,生產效率低下,且不利于推廣農業技術。個體農戶自己決策生產和投資,受農戶資金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差、知識和能力有限、交易費用高等各種因素約束,嚴重影響了農村生產效率的進一步提升。[16]為了解決小農戶分散經營與大市場之間有機銜接之間的矛盾,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一些地區出現了“貿工農一體化”和“產加銷一條龍”農業產業化組織模式,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經營體質改革的基礎上,農業逐漸走向了適應市場經營發展的新的經營方式,引導廣大農民開始走向生產效率更高的農業產業化發展道路。
⒉改革落戶制度,實現了農村勞動力城鄉自由流動。實施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后,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發展和提高農業勞動生產效率,農業剩余勞動力大量涌現出來以后開始向非農產業轉移和向城鎮轉移。[17]為了適應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業和落戶的要求,1984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中規定,允許長期在城鎮務工、經商、有固定職業和住所的農民,在自理口糧的情況下遷入城鎮落戶。對“在集鎮有固定住所、有經營能力或在鄉鎮企事業單位長期務工的,公安部門應準予落常住戶口,及時辦理入戶手續,發給《自理口糧戶口簿》,統計為非農業人口”。[18]在1985年9月實施的居民身份證制度,標志著中國公民具有了在非戶籍地居住的合法性權利。在此期間,廣東、上海等地區廢除了具有限制勞動力流動意義的糧票。1993年,全國范圍內終止了糧票的流通,糧油開始實施市場化供給。上述關于農民能夠向城鎮流動的就業和落戶等制度性改革,雖然沒有從根本上觸及戶籍制度,但卻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對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就業的限制性措施,實現了農村勞動力在城鄉之間、農業與非農業之間的自由流動。為了進一步解決一部分轉移勞動力的戶籍需求,1997年,公安部關于《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和關于完善農村戶籍管理制度的意見》中規定了從農村到小城鎮務工或者興辦第二三產業的人員,小城鎮的機關、團體、企業和事業單位聘用的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在小城鎮購買了商品房或者有合法自建房的居民,以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親屬,可以辦理城鎮常住戶口。2001年3月,國務院決定全面推開小城鎮戶口限制,取消居住期限的限制,并在“十五規劃”中提出將建立統一的全國勞動力市場,全面取消對勞動力合理流動的限制。通過建立勞動就業登記制度,確定唯一社會保障號碼等措施,對于徹底改革城鄉分割、地區分割的就業管理制度具有重大意義。[19]
⒊改革農業農村稅收制度,促進城鄉經濟平衡發展。1958年實施的《農業稅管理條例》使我國城鄉居民之間出現了稅費差別。以農業稅為代表,農村居民不僅需要交納村提留、鄉統籌,還需要出義務工或者以資抵工,并且還規定在農村從事二、三產業的個體戶或者私營業主需交納工商稅、所得稅,與之相比較農鎮居民從事二、三產業需交納工商稅和增值稅等,不需交納其他稅費。[20]2005年12月29日取消農業稅標志著城鄉間的稅費差別已經消除,并且各省又出臺了相關政策,進一步降低或者取消針對農民的收費,對農民專業合作社進行稅費減免,免征房產稅,減免所得稅、抵扣增值稅,擴大增值稅優惠范圍。[21]取消農民的農業稅、對農業生產經營減免稅費,不僅減輕了農民負擔,增加了農民收入,也消除了城鄉稅費差別,為城鄉經濟實現平等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二)進一步深化改革使我國的城鄉關系由緩和走向逐步融合
⒈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逐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優化農地資源配置的重要環節,也是激活農村要素的重要內容。改革原有的承包權,給予農民完整、穩定的使用權成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的重要方向。[22]2016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成為進一步深化農村土地改革的重要標志。完善農村承包土地“三權分置”制度,從根本上解決了土地的基本權益關系,從而進一步保護了農業經營主體的土地經營權益,提高了農業經營主體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在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前,農業經營主體的財產權利并沒有得到應有保障,而“三權分置”改革的政策則明確規定,在依法保障集體所有權和農戶承包權的基礎上,平等保護經營主體的合法經營權,保障經營主體穩定的經營預期。從農業現代化的角度看,“三權分置”改革對于培育和發展農村各類經營主體尤其是新型經營主體有著重要意義:一方面,穩定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有利于穩定農業投資者的預期,有利于吸引社會資本投資農業生產領域,進而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土地產出效率和勞動生產效率;另一方面,農村土地經營抵押和折價入股能夠實現農村土地經營權資本化,穩定農業經營主體的生產經營行為,實現農業生產效益增長與投入增長互促的良性循環。從增加農民收入的角度看,“三權分置”改革使土地具備了流動性特點,可以合法進行農地流轉,因而農地經營權有了增收的屬性,進行流轉的農戶獲得了財產性收益,使一部分不再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或者有意愿從事其他非農產業的農民擺脫了“兼業性”羈絆,通過相應的非農產業培訓獲得工資性收入,實現職業身份轉變。農地流入方通過獲得農地經營權達到了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條件,并在土地長期流轉預期保障下,有利于實現農地經營的規模化、機械化和集約化管理模式,農業的生產效率得到極大提高,專業化農業經營的農民可以獲得更加豐厚的經營性收入。[23]
⒉深化農產品價格和農業補貼制度改革,逐漸改善工農業關系。以2004年實施小麥和稻谷最低收購價保護政策為開端,我國農業領域改革逐漸深化并形成了農產品價格保護制度和農業補貼制度,構建了農業支持保護體系。首先,逐步形成并完善農產品價格保護制度。2004年開始實施農產品最低收購價格保護政策,實施農產品價格保護制度對于穩定農民生產預期發揮了重要作用。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導致農產品價格暴跌,由于實施了價格保護制度,國家對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等“三省一區”的玉米,新疆的棉花、大豆、糖料和油菜籽實施了臨時收儲政策,穩定了該產業的收入水平,保護了農民利益,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24]其次,逐步形成并完善農業補貼制度。2005年取消農業稅改革以后,我國開始實施農業直補政策,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業補貼的力度逐漸加大,范圍逐漸拓寬。為了進一步提升農業補貼的政策效應和政策效能,國家又進一步實施農業補貼政策改革,將重點放到農業綠色生態、耕地保護和糧食適度規模經營等方面。農業補貼政策實現了對農民由“取”向“予”的轉變,促進了農業生產發展和農村社會穩定。實施農業補貼政策,完善了農業基礎設施體系;提升農業的綜合效益,改善了農業物質裝備水平;提升農業科技貢獻,更為主要的是帶來了農民收入連年增長,這一系列措施,極大地改善了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以實施農產品價格保護制度為開端,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以保障糧食安全、促進農民增收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為主要目標,由農民直接補貼、生產支持、價格支持、流通儲備、災害救助、基礎設施、資源與環境保護以及政府間轉移支付等各類支出組成,涵蓋了農業產前、產中、產后各個環節和主要利益主體的農業支持保護政策體系。[25]
三、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城鄉關系演變的基本經驗
(一)堅持協調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城鄉關系演變的內在邏輯呈現出政府與市場由對立走向融合的特點,堅持協調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是我國城鄉演變的基本經驗之一。政府設置工農產品剪刀差、農產品統購統銷和農村集體經營體制并建立起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城鄉關系固化為分割的二元經濟與社會結構體制,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失調。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后,重新確立家庭經營的市場主體地位,形成了對農業生產的市場激勵機制,在較短時間內全社會的糧食短缺得以緩解。針對賣糧難,政府通過提高收購價進行協調,從而使市場與政府由體制外對立走向體制內結合。經歷了對糧食計劃定價與市場定價雙軌制的過渡,隨著在全國范圍內取消糧食購銷合同,農產品實現市場化定價,進而實現了農產品市場價格決定的市場與政府協調。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放開最具活力的勞動力要素向城市和非農產業流動,農村工業化與城鎮化對勞動力的需求促進了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從而為勞動力市場發育提供了基礎。政府對勞動力要素從農村向城鎮與非農產業轉移由初始階段的限制向逐漸放開,再向建立與完善勞動力自由流動的保障制度轉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成為配置勞動力要素的平臺,政府為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提供保障條件,使市場機制對勞動力流動由輔助向基礎轉型,政府則做好政策補位,實現了勞動力市場的政府與市場協調。從城鄉關系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模式,向有計劃與商品經濟平行轉型,再由市場的決定性向基礎性與政府補位的協調,70來中國城鄉關系演變遵循政府放權擴大市場調節空間、實現政府與市場關系從體制外對立到體制內結合再到體制內融合、構建“雙引擎”的邏輯理路,形成了中國特色政府與市場內在融合的新型關系。[26]
(二)堅持統籌兼顧的基本戰略
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是密不可分的。縱觀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城鄉關系演變的歷史進程,不論在城鄉關系處于分割階段還是緩和階段或是逐步融合階段,堅持統籌兼顧是中國城鄉關系演變的基本經驗之一。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針對城鄉關系就提出“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27]新中國成立以后,在城鄉兼顧戰略的指導下,通過恢復城鄉交易市場促進城鄉物貿交流,通過促進城鄉工農產品平等交換,通過修繕和恢復城鄉交通基礎設施,通過取消城鄉人口流動限制等措施,城鄉關系有了短暫的改善。改革開放之初,針對日益嚴重的城鄉分割狀況,鄧小平提出“農業要現代化,才能適應工業的現代化。工業越發達,越要把農業放到第一位。這就要求工業支援農業”。[28]在城鄉互動戰略的指導下,通過農村經營體制改革,鄉鎮企業發展的小城鎮建設促進了農業和農村工業化發展,進而又帶動了小城鎮建設,在短期內極大地改善了城鄉關系。針對改革中心向城市轉移以后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擴大的狀況,江澤民提出“引導二、三產業加強對農業的支持,逐步形成以工補農、以工建農、以工帶農的機制。”[29]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核心是把農村和城市綜合起來通盤考慮,通過實施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方針政策,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協調發展。針對城鄉要素不平等交換導致城鄉發展差距持續擴大的問題,胡錦濤在深化和完善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基礎上,在黨的十八大提出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發展目標和總體要求,進一步深化了統籌城鄉發展戰略的內涵。進入到新時代,習近平在對城鄉關系新變化進行深刻總結的基礎上,對城鄉發展一體化進行了全面創新,形成了內涵更為豐富、時代特征更為明顯、戰略體系更為全面的城鄉發展一體化戰略,更加關注城鄉互動平等,更加強調通過深化改革和構建城鄉一體化的體制機制實現城鄉融合。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城鄉關系演變的基本經驗表明,統籌兼顧是解決不同時期城鄉關系的基本戰略并貫穿城鄉關系演變的全過程。雖然不同時期城鄉關系面臨的問題迥異,但堅持統籌兼顧的戰略有利于將城鄉問題綜合起來,在堅持不同階段城鄉關系差異性和互補性的基礎上,采取適當策略加以解決。
(三)堅持工業化與城鎮化的發展道路
縱觀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城鄉關系演變的歷史進程,以工業為主導,以城市為中心的發展道路是基本經驗之一。堅持工業化與城鎮化的發展道路雖然在不同階段對城鄉關系產生了不同影響,但這一戰略貫穿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城鄉關系演變的全過程。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就明確指出在城鄉關系當中城市是中心。對工業與農業之間的認識,經歷了從“重工業優先發展,農業支持工業”到“注重農業和輕工業發展,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再到“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重工業要為農業和輕工業服務”,到“最終提出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工農業發展指導思想。[30]在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以后,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實施的放寬農民進鎮落戶限制和建制鎮設置標準,鄉鎮企業迅速發展,[31]成為吸收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重要力量,帶動了城鎮和農村工業化的發展。以小城鎮為代表的城鎮化與鄉鎮工業為代表的農村工業化成為改革開放以后一個時期內城鄉關系結構演變的主要特點。進入到21世紀,到黨的十八大之前,城鎮化與工業化仍是城鄉關系的重點,更強調“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戰略促進城鄉關系轉型,進一步凸顯了城鎮化和工業化道路在城鄉關系當中的主導地位。進入到新時代,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四化同步”戰略思想,將城鎮化、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放到同等的戰略地位,強調以人為本、以實現城鄉要素公平交換和工農互惠融合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城鄉關系演變的基本經驗表明,提升工業化與城鎮化發展水平是改善城鄉關系的重要途徑,堅持工業化與城鎮化的發展道路是促進城鄉關系由分割走向緩和進而走向融合的“發動機”和“加速器”。
【參考文獻】
[1]徐勇.本質平等與事實不平等:現階段社會主義城鄉關系分析[J].求索,1990,(4):40-44.
[2]李文詮.社會主義社會城鄉矛盾問題初探[J].理論學刊,1986,(2):7-10+45.
[3]楊少壘.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探索的歷史進程[J].農村經濟,2015,(10):78-83.
[4]林木西,王慧.工業化的“二元結構”與農村工業化的發展[J].當代經濟研究,2003,(7):28-32+73.
[5]范麗霞,李谷成.我國農村工業化回顧與展望[J].產業與科技論壇,2008,(3):21-23.
[6]劉秀敏.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離不開鄉鎮企業的發展[J].經濟論壇,2001,(4):14.
[7]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所課題組.改革開放40年中國工農關系演變:從緩和走向融合[J].改革,2018,(10):39-51.
[8]李坤英.保障農民利益建立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J].新農業,2014,(10):22-24.
[9]趙曉芳.中國城鄉社會保障水平差異:危害與化解[J].石家莊經濟學院學報,2012,(5):82-87.
[10]韓俊.促進城鄉公共資源均衡配置[N].經濟日報,2015-11-11.
[11]徐健.建國初期農村教育的幾種形式[J].職教通訊,1998,(4):44-45.
[12]李曉燕.城鄉醫療保障制度一體化研究[J].學術交流,2012,(6):143-146.
[13]陳天祥,饒先艷.“漸進式統一”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模式——以東莞市為例[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1):16-24.
[14]陳儉.新中國城鄉關系演變的特點及啟示[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6,(6):48-52+58.
[15]武力.1949—2006年城鄉關系演變的歷史分析[J].中國經濟史研究,2007,(1):23-31+76.
[16]張培麗.農村走出困境之路——農業產業化和農村組織形式創新[J].改革與戰略,2001,(6):57-60.
[17]陳廷煊.建國以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歷史進程和特點[J].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1):1-7.
[18]顧朝林,陳金永.大城市戶籍應該逐步放開[J].城市發展研究,2001,(6):25-33.
[19]黃平.近年來中國農村人口流動的思考[J].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02,(9):26-28.
[20]劉洪云.淺析當前我國城鄉差別的幾個問題[J].天津農學院學報,2002,(S1):41-43.
[21]楊春悅.各地農民專業合作社稅收優惠政策綜述[J].中國農民合作社,2010,(9):14-15.
[22]趙紫玉.構建我國農地產權“三權分離”模式——對現行農地產權制度改革的設想[J].國土資源,2006,(9):32-34.
[23]郭濤,趙德起.農地“三權分置”促進農民增收的理論與實踐研究[J].新疆農墾經濟,2017,(8):13-18+52.
[24]孔祥智,張效榕.從城鄉一體化到鄉村振興——十八大以來中國城鄉關系演變的路徑及發展趨勢[J].教學與研究,2018,(8):5-14.
[25]湯敏.中國農業補貼政策調整優化問題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7,(12):17-21+110.
[26]劉儒,王換.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歷史演進的內生性邏輯與基本經驗——以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為主線[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6):93-100.
[27]毛澤東選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7.
[28]鄧小平年譜(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382.
[29]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129-130.
[29]《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出版[N].人民日報海外版,2002-08-28.
[30]許彩鈴.城鄉經濟關系思想的演進:從毛澤東到習近平[D].福建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33.
[31]王蘋,郭雪飛.鄧小平城鎮化改革思想發展與實踐探析[J].毛澤東思想研究,2015,(1):47-50.
(責任編輯:王秀艷)
Abstract:In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Looking a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lations in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compared with the orderly cycle of urban and rural relations under the natural order,the evolu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lations in China shows a unique internal logic.In particular,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the essential pursuit of the evolution of urban rural relations.Reform and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are the inexhaustible driving force for the evolution of urban rural relations,and the basic experience is further.The 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should be followed.The essence,motive force and basic experience constitute the logical main line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Key words:urban-rural relationship;development path;dynamic mechanism;basic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