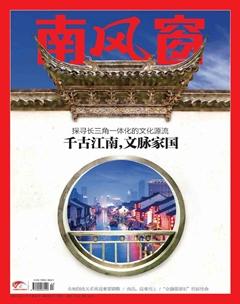他山之石,卻難攻玉?——再探“第三方”改造困境的源頭
他山之石,卻難攻玉 —再探“第三方”改造困境的源頭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 羅婧 本文節選自《社會學研究》2019年第5期

(一)“躲不過、理還亂”的兩重邏輯
首先,合作和賦能是作為“第三方”的社會組織參與鄉村建設不可或缺的兩重邏輯。當前各類社會關系都在不斷演變,作為建設“社會”的社會組織需要在已有的結構中運行和發展,那么合作是社會組織努力成長和發揮影響的首要策略。對于需要進入鄉村社會,改變鄉村現狀的社會組織而言,讓社區成員參與到尋求發展的過程中來,是其實現社會建設目標的必經之路,那么賦能于民勢必是社會組織的核心理念。
其次,兩重邏輯具有難以彌合的內在張力。合作邏輯下,社會組織直接進入基層權力網絡,要得到國家的許可、地方的認同,其中有失去自我、失去目標的風險,因此社會組織要著力強化自我的組織架構與行動能力。賦能邏輯下,社會組織需要培育社區成員的組織與行動能力,它試圖不陷入當地的利益糾紛,卻又嘗試改變原先鄉村社區的社會結構和發展路徑。這讓社會組織在如何設計組織制度、如何處理與政府和居民的關系、選擇是否深入融入社區、是否設立退出機制等方面舉棋不定。
這樣來看,作為“第三方”的社會組織參與鄉村社區建設時,“好心難辦好事”的結局似乎并非巧合。各色懷揣理想、勇于承擔責任的“第三方”模仿、借鑒、探索了各種制度和策略,核心都是要將合作與賦能兩重邏輯相互理順,如此才能辦成好事,實現目標。然而在當前我國鄉村轉型的語境下,合作與賦能邏輯的理順與協調卻極為困難。
沿著本文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合作與賦能兩重邏輯的理論根基大多以西方社會為原型,在分析我國現實情況時,學者們對這些理論中的概念范疇進行了適應性調整。但基于中西社會基礎的差異,合作和賦能這兩重邏輯在中西語境下具有完全不同的意涵。
(二)中西比較下的范疇困局
中西社會中“合作”與“賦能”的意涵完全不同,這是由于這兩重邏輯生長的社會基礎具有差異。我國當代社會組織的發展極大地借鑒了來自西方社會組織的經驗,然而即便把它們視為“嫁接”來的組織,其發展所需的養分還是來自傳統的根系。這導致陷入困境的并不只是試圖建設社會的社會組織,還有試圖理解和分析社會組織的研究。也就是說,“第三方”的鄉村改造困境不只是實踐難題,也是理論層面的范疇困局。如果從生長于西方的理論框架、概念范疇出發來探討我國的情況,不論如何進行適應性調整,學者只能進行彼此之間“原地打轉”式的爭論。
這樣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何我國的“第三方”難逃困境,合作和賦能兩重邏輯理順起來如此困難。西方的社會組織在參與本土治理時,普遍沒有遭遇類似我國社會組織的困境,并不是因為西方社會具有某種先進性,而是因為國家與社會分立的社會基礎與側重參與決策的權能相互穩定契合。西方的社會組織同樣試圖在社區既有的基礎上帶來改變,但其行動的合法性獨立于國家和社區,且對目標實現與否的衡量是社區成員是否習得決策的協商程序。所以,合作和賦能往往不會出現對立和排斥的狀況。
但在我國當前以“變”為核心的社會轉型語境下,各種關系都在不斷重構,合作和賦能中包含了諸多的不穩定因素。與此同時,每個人都只關心自己的境況是否改變,所以社會組織能否實現賦能取決于成員是否感知到境況的改善:對于境況得以改善的社區成員而言,社會組織一切策略性的配合方式都是“足智多謀”的;而對于境況未改善的成員而言,社會組織各種的靈活策略都是沒有規則的“詭計”,充斥著勾結的氣息。
信訪制度的雙重邏輯與“非行政信訪”—以A市重復集體訪為例(2010~2014年)
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夏瑛 本文節選自《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4期
(一)信訪實踐的現狀特征
總體而言,A市重復集體訪凸顯了當前信訪實踐的如下兩個特征:
首先,民眾利益訴求構成信訪主要內容,信訪制度在事實上發揮著社會糾紛解決機制的功能,回應本文開端對信訪制度功能所做的討論。雖然學界在規范層面對信訪制度的功能定位看法不一,從“政治動員”論到“政治參與”論,從“糾紛解決”論到“社會治理”論,等等;但是,信訪實踐所反映的情況卻是相對明確且統一的,信訪制度在事實上發揮著社會糾紛解決機制的功能,因進入信訪渠道的訴求多為民眾個體的具體利益訴求,少見完全政治性或公共性的信訪訴求。
從這一角度來看,將信訪視作民眾政治參與平臺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低估了民眾利用信訪制度解決自身問題的工具理性與功利主義算計。
其次,大量非行政信訪活躍于信訪渠道,信訪制度的現實功能遠超“小信訪”(行政信訪)的功能范疇。等待信訪制度解決的問題不僅僅是行政類糾紛或政策類糾紛,還有許多與政府、政策沒有直接關系的民事類糾紛。這一發現與信訪研究中的主流論述有所不同。很多研究認可信訪制度的糾紛解決功能,但都潛在地假設進入信訪渠道的糾紛是民眾和政府之間的行政性糾紛。換言之,他們是在“小信訪”的框架下分析信訪制度不同于其他行政糾紛解決機制的功能定位。而我們從A市重復集體訪看到的情況是,“小信訪”框架僅能分析一部分信訪實踐,它無法解釋為何有一半左右的非行政信訪存在于當前的信訪實踐中。
(二)信訪實踐的制度解釋
如何理解信訪實踐的這種現狀?在本文看來,根源還在于中國當下的信訪制度糅合著“政治”與“行政”兩種制度邏輯;信訪制度的雙重邏輯為“非行政信訪”的存在提供了條件和空間。
信訪制度的政治邏輯強調信訪作為黨的群眾路線的功能定位,或者認為信訪是《憲法》所規定的人民民主權利的保障機制。作為黨的群眾路線的一部分,信訪部門應對人民群眾的各種訴求持開放聆聽的態度,并盡力回應和解決群眾訴求;同樣道理,作為人民民主權利的保障機制,信訪應給人民群眾通過來信來訪向各級黨委和政府提出要求、建議、批評和揭發、控告、申訴提供充分的制度化空間和正式回應。因此,政治邏輯指導下的信訪制度應向“大信訪”方向發展。
信訪制度的行政邏輯卻有著明確的制度規范和法律范疇,它強調信訪只依法接納、處理行政糾紛類或政策類的民眾訴求,其他類型的社會糾紛應依法通過其他糾紛解決機制尋求解決。行政邏輯下的信訪制度更傾向于向邊界分明的“小信訪”方向發展。信訪制度在最近幾年的改革,尤其致力于將涉法涉訴類信訪從普通信訪中剝離出去的信訪法治化改革,實際上正體現著信訪制度在執行機制上越來越向行政邏輯發展的趨勢。
“政治”與“行政”的雙重制度邏輯為信訪工作帶來了一些不確定性。筆者在A市調研的過程中,不少信訪干部坦言,他們在處理具體信訪案件時時常矛盾于政治與行政兩種邏輯之中。根據信訪法治化改革的要求,信訪部門可以將眾多涉法涉訴訪剝離。根據這一邏輯,大量非行政信訪或許可以被認定為“不合理上訪”。但在具體操作中,這種做法時常遭遇壓力,很難順利落實。原因之一在于信訪人,甚至信訪部門本身更傾向于從政治邏輯的角度來理解和要求信訪工作,這種定位與要求使得信訪部門不得不正面應對與政府并無直接關系、但卻真實困擾信訪人自身利益的信訪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