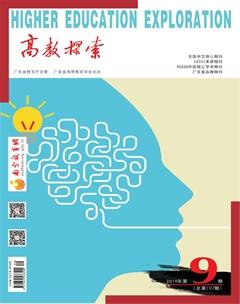論高等教育發展與科技革命的關系邏輯
崔衛生
摘要:科技革命是科學知識革命和技術應用革命的統稱。16 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發生的近代科學革命和現代科學革命帶動了三次技術革命。科技革命不僅改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而且改變了人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從而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核心動力。科技革命對高等教育發展邏輯的深度影響體現在五個方面:改變高等教育發展方向;重構高等教育核心價值體系;催生新型教育元素如職業技術教育與繼續教育;推動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趨向多元化;改變高等教育內容與教學方式。
關鍵詞:科學;技術;科技革命;高等教育發展
科學技術變革對高等教育具有深刻影響,是推動高等教育不斷發展的根本動力。每一次人類教育實踐活動方式的重大進展或突破,皆與科技革命深度關聯。探尋科學與技術如何型構高等教育的發展邏輯這個問題,有助于我們準確把握正在興起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對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準確把握新時期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趨勢,從而及時推動我國高等教育模式的創新與嬗變。
一、理性知識與應用技術:從分立走向融合
“科技”是“科學”與“技術”的統稱。科學一詞出現在14世紀,源自于拉丁文“scientia”,蘊含了希臘文“episteme”的含義,是“知識”之意。在古希臘,科學是一種相對獨立的、在理性生活中具有支配性作用的精神范式,希臘的知識傳統也就是廣義的科學傳統。1786年康德在《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初始根據》中指出:“任何一種學說,如果它是一個體系,亦即是一個按照原則來整理的知識整體的話,那就叫做科學。既然那些原則要么可以是知識在一個整體中的經驗性聯結的原理,要么是其理性聯結的原理,……唯有其確定性無可置疑的科學才能被稱為本真的自然科學;只能包含經驗性的確定性的知識,是一種僅僅非本真地如此稱謂的學識”[1]。由此可見,科學所探討的是自然界的真理,其本質是具有嚴密邏輯的理性的知識體系。然而,“科學遠遠不僅是許多已知的事實、定律和理論的總匯,而是許多新事實、新定律和新理論的繼續不斷的發現。它所批評的,以及常常摧毀的東西,同它所建造的東西一樣多”[2]。科學不僅僅是系統化、理論化的知識體系,也是人們認識自然界、社會以及人類自身的一種探索過程,是一項以理性的方式認識自然界、以邏輯的方式解釋世界、以理論的方式表述客觀規律的理性事業。
技術源于人類生存及其發展的需要,技術應用于人類生活必然涉及三個要素:主體行動者、使用的對象以及使用的方法。因此,“技術”的內涵可以從三個層面進行詮釋:一是指主體行動者的能力;二是表現為物化形態的生產工具、裝備、設備等;三是生產上所使用的方法、途徑、策略以及制度等有關規則的知識。在西方語境中,“技術”一詞大體包含著三個方面的意思:一是指生產某種物質產品或精神產品的技巧和技能;二是指具有特定目的的一系列行動組合而體現出的行為方法和途徑;三是指人類創造的體現生產力水平的勞動工具。技術的目的是增強人類的生存能力,改善人類的生活質量,具有明確的功利性目標。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階段,科學和技術彼此分離。科學由一些有知識、有學問、有身份的人所掌握,是對“閑逸的好奇”的追求,屬于知識范疇。技術屬于生產勞動的實踐經驗范疇。在古代甚至近代的早期,在科學與技術之間一直存在鴻溝,二者分屬于兩個不同傳統,即哲學家傳統和工匠傳統。技術發明主要源于體力勞動者的實踐經驗,科學對技術的更新與發明很難起到作用。16世紀以后,科學和技術之間的界限或隔閡逐漸消失。近代科學既有代表古典的理性知識傳統,也有以功利為明確訴求的新興特征,即具有“技”的一面。“新科學的一個革命性的特點是增加了一個實用的目的,即通過科學改善當時的日常生活。尋求科學真理的一個真正目的必然對人類的物質生活條件起作用。這種信念在16世紀和17世紀一直在發展,以后越來越強烈而廣泛地傳播,構成了新科學本身及其特點”[3]。1660年,英王查理二世批準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專業的科學組織——倫敦皇家學會,標志著科學已經不再依附于宗教,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建制。在啟蒙運動中,思想家們強調只有科學才能使人正確認識自然,強調科學對于實用技術的作用以及在社會發展中的獨立功能;18世紀60年代,英國進入以瓦特蒸汽機的改良和廣泛使用為核心內容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使科學和技術成為生產過程必不可少的因素,標志著科學與技術的真正結合,科學與技術之間呈現出“科學技術→生產”的發展模式,科學與技術逐漸融為一體,共同服務于人類的社會生產。科學研究成果不斷地被轉化為技術,技術中的科學含量也越來越高,現代技術被稱為是一種“作為應用科學的技術”。
二、科技革命的歷史邏輯
英國物理學家、科學學(Science of Science)奠基人貝爾納(J.D.Bernal)在《沒有戰爭的世界》(1958年)—書中首次提出“科技革命”。從科技革命的歷史來看,可以將科技革命分為兩個不同階段的科學革命及其影響下推動的三次技術革命,即:近代科學革命(16世紀-19世紀)與第一次技術革命(17-18世紀)和第二次技術革命(19世紀30年代-19世紀末);現代科學革命(19-20世紀末)與第三次技術革命(20世紀30年代以后)。
近代科學革命也稱為第一次科學革命,以1543年尼古拉斯·哥白尼發表的《天體運行論》為標志。基于運動的相對性,哥白尼論證了行星視運動的機理是地球運動和行星運動復合的結果,創立“日心說”,最先突破宗教神學中流傳1000多年的“地心說”,宣告近代科學革命的開始。18世紀初到19世紀末,近代自然科學進入全面發展時期。近代科學革命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突破了古代科學活動中直接觀察法的桎梏,建立起以控制性的實驗、邏輯體系的建構、嚴格的實驗檢驗以及糾錯機制為主要特征的實證科學方法;[4]二是自然科學理論方面的重大發現及其對兩次技術革命的推動。在自然科學領域,具有革命性的理論突破主要有:物理學中經典力學體系的建構、經典電磁學理論的建立、能量守恒定律的發現以及熱力學的研究;生物學中細胞學說與生物進化論思想的確立;化學中原子論、元素周期律的提出等等。這些重大理論的發現標志著近代自然科學體系的建立,也帶動了兩次技術革命的興起。第一次技術革命是以1765年英國人瓦特在已有蒸汽機技術的基礎上發明的高效能蒸汽機為標志,在工業生產中用蒸汽動力技術取代經驗性手工技術。第二次技術革命是以19世紀中葉電動機與發電機的發明為標志。電磁學的創立奠定了開發和應用電能的理論基礎,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電力技術廣泛應用于人類的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電報、電話的發明開創了遠程通信技術新時代,人類從蒸汽時代進入到電氣時代,電力技術取代了蒸汽動力技術。
現代科學革命通常也稱作第二次科學革命,化學、物理學、生物學等學科領域的重大理論突破主要包括相對論(1905-1916)、量子力學(1911-1926)以及X-射線、放射線和電子的發現以及系統科學的興起與自組織理論的誕生等。現代科學革命的偉大理論成果推動了以電子技術為主導技術的第三次技術革命,并引發了60年代以后的高新技術,即以科學的最新成就為基礎、知識高度密集的、對經濟和社會發展起先導作用的新興技術群,如信息技術、材料技術、能源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等。[5]縱觀400多年科技革命的發展變化,其歷史演變的邏輯如表1所示:
“歷史邏輯是以歷史時間的歷時性和共時性統一為基礎的概念推論,研究關于敘述史中基本概念之間的意義關系和推論規則”[6]。科技革命的歷史邏輯蘊含了科技革命的兩個根本性特征。一是從科技革命的功用來看,科技革命具有社會性。科技革命發展的歷史表明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與更新的根本動力來自于人們對物質世界的需求以及了解自然、探求支配自然的手段的需要。“科學的功能有兩個主要方向:消除可以預防的人類禍患;開辟可以滿足社會需要的那種新的活動領域”[7]。科技革命推動了產業革命,使人類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其影響波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因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成為一個歷史命題,“生產力=[(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生產管理]×科學技術”[8],科學技術滲透在社會生產力的各要素中,科技社會化,社會科技化,科學技術已是高度社會化的產物。二是從科技革命自身的性質來看,科技革命具有創新性。管窺科技革命的歷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的科學理論的發現與體系的建構以及對傳統的技術的突破是每次科技革命的標志。這意味著“持續性的打破,與過去隔斷聯系的新秩序的建立,它是一條明顯的裂縫,一邊是舊的、熟悉的東西,另一邊是新的、生疏的東西”[9]。對未知領域的探索、向前發展以及新穎性與科技革命相伴相惜,創新是科技革命的根本屬性與內核。
三、科技革命建構高等教育發展邏輯
根據存在領域的差別,可以將規律劃分為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共同性在于客觀性,二者的根本區別在于,自然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社會規律就是人實踐活動規律,它在具有客觀性的同時,也具有主體性要素。因此,我們用邏輯概念來作為社會發展規律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更能夠準確體現社會歷史發展各要素之間的關系。所謂科技革命建構高等教育的發展邏輯,就是指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科技因素與高等教育因素之間本質的必然的聯系,科技革命的影響力能夠決定或左右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或演進路線。
(一)科技革命引領高等教育發展方向
科技革命最終促成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趨勢。傳統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是為培養少數社會精英服務的。適齡青年(18-25歲)的入學率即使在發達國家也只有20%左右,發展中國家僅僅只有6%-7%。[10]但是,科技革命改變了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一方面,科技革命使大工業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業小生產,把人類從傳統的手工勞作中解放出來,人類由此可以獲得更多的閑暇,擁有更多的時間資源去接受教育;另一方面,現代科技革命所帶動的信息產業的迅速崛起對從業人員的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的要求越來越高。高等教育要為社會培養越來越多的高素質人才,以滿足新科技革命所推動的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美國學者馬丁·特羅認為當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5%時,高等教育就進入了大眾化階段。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教育概覽2017》顯示,經合組織和合作伙伴國家的25-34歲的年輕人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2016年平均為43%;[11]在中國, 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27%。[12]
科技革命催生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新趨勢。第一,國際學術交流與研究方式的改變。“現代科學技術革命造成了一個高度分化與高度綜合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13]。科學技術的發展呈現出整體性與群體化趨勢,規模大、協同性高,互聯網、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的成熟為這種大規模、協同式合作提供了條件。因此,高等教育國際化中的科學研究國際合作逐漸從個人自由研究為主的小型合作轉向以國際合作聯合實驗室、國際聯合研究中心、國際合作基地等國際合作平臺作為組織形態進行大規模的、重大科技項目的合作。第二,“虛擬流動”成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新形式。人員流動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基本要素,出國留學是學生接受國際優質高等教育最重要的途徑。在信息技術的支持下,虛擬流動(virtual mobility)成為高等教育國際化中人員流動的一種新形式。虛擬流動是一種學習形式,完全通過信息通信技術支持的虛擬組件組成的學習環境,包括與來自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們一起工作和學習的跨境合作,其主要目的是加強跨文化理解和知識交流。[14]通過遠程教育、網上開放課程、多媒體的應用與即時對話技術等,沒有機會出國的學生在本土也可以共享全球大學的優質學習資源,接觸各國不同的文化,獲得國際化的學習經歷。“虛擬流動”推進了高等教育國際化從一種傳統的“國外國際化”的范式轉向“國內國際化”“校園國際化”等新范式,使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受益學生群體從少數精英轉向普通學生。
科技革命“倒逼”高等教育走上現代化道路。科技革命成果在社會生產中的廣泛應用推動了社會經濟運行模式和生產方式的變革,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和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變這兩大階段,演繹了社會現代化的軌跡。在現代化的不同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結構、經濟狀況與人的思想觀念等各不相同。高等教育作為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發展受制于社會的發展。教育與社會的關系規律是教育必須與社會發展相適應,“適應”一個方面是“受制約”,一個方面是“為之服務”。[15]因此,高等教育要與社會的現代化協調發展,成為“時代的表征”與“風向標”,現代化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由之路。高等教育現代化“要求我們要以先進的教育思想觀念為指導,使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的現代化發展相適應,達到現代世界高等教育先進水平,培育出滿足現代經濟和社會建設要求的新型勞動者和高素質人才”[16]。
(二)科技革命重構高等教育價值體系
科技革命促使科學研究成為大學的基本職能之一。歐洲中世紀大學是現代大學的源頭,“求知與教學”以及“對真理和自由的追求”是中世紀大學的立學根基。這種中古的學術傳統一直到18世紀末都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大學的唯一職能就是培養人才,科學研究是在大學以外的研究所進行的,科學技術的發現和發明與大學無關。19世紀初,與早已進入工業革命的英國、法國相比,德國工業化的進程比較緩慢。經歷了1806年第一次普法戰爭割地賠款的慘敗,德國開始十分重視大學在民族發展和振興中的作用。1809年,德國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組建柏林大學,明確提出大學是“帶有研究性質的學校”,大學具有科學研究和培養人才兩項職能,在科學研究過程中實現人才培養,“由科學而達至修養”。科學研究成為大學的一個基本職能標志著現代大學新理念的建立。
科技革命使得科學研究成為評價高等教育的重要標準。科技革命對社會生活產生的變革性影響見證了科技對推動人類與社會進步的巨大力量,也彰顯了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以科研服務社會是現代大學的重要目標之一,科研成果逐漸變成一種學術資本。科研成果是評審教師的職稱和業績、院系的專業成就、高校辦學水平的主要標準,而科研實力也是衡量大學國際地位的首要標準。例如,全球大學排名的權威機構中,QS世界大學排名的6個一級指標中,與科學研究相關的就有兩個,分別是“學術聲譽”和“教師論文的引用率”,兩個一級指標的權重分別是40%和20%,為總權重的60%;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中,與科研相關的一級指標權重也占總權重的60%。
科技革命使得“有用性”成為評價知識的價值尺度。在現代科學與技術一體化的背景下,新技術產品的開發越來越依賴于科學理論的指引,要求有較高的科學知識投入。對高深知識的探索是大學存在的合法性根基,而在現代教育體制下,國家不再是知識的主要資助者,因而大學要尋求多種渠道的額外資金來進行知識生產,這種需求與市場上開發新技術產品的需要不謀而合。“有用”成為知識的主要存在方式,也成為評價知識價值的標準之一,知識變成了以使用者為主導,“出現了一種新的知識生產模式,在這種模式里,知識的使用者對知識的性質比生產者更有發言權”[17]。這樣的背景催化了大學逐漸向工具性價值觀傾斜,也促使大學的主導價值觀被一種以知識產品換取金錢、權力和榮譽的功利性觀念所取代。
(三)科技革命改變高等教育結構
科技革命導致職業技術教育的出現。一方面科技革命推動的工業化大生產需要越來越多的技術工人;另一方面生產力要素中科學與技術的構成越來越高,對于生產和經營管理者的科學與技術素養的要求也隨之提高。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以后興起的“朝陽產業”對工人的知識、技術要求更高,“信息素養”“信息技術”成為21世紀核心素養的基本構成部分。職業技術教育是普通教育與勞動就業之間的耦合劑,是高等教育機構中的一支新力軍。英國是世界上最先進入工業革命的國家,從19世紀中期以后就開始出現有別于傳統大學的各種技術學院和師范學院,旨在培養技術和職業人才。“到20世紀30年代,技術學院中的在校生數構成了英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主要部分”[18]。
科技革命使得繼續教育成為社會必需的教育新品種。科技的不斷更新及其在生產中的應用引起了社會就業結構的改變,呈現出舊職業的不斷淘汰以及新職業的快速興起,新舊職業更迭的時間周期在逐漸縮短。世界正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創造新職業,淘汰舊職業,一個人的一生中可能會面臨多次的職業轉換,因此需要接受多次的再教育與再訓練。[19]傳統的“一次性教育”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一個人要生存、要發展就必須終身不斷學習。在此背景下,繼續教育應時而生,成為社會必須的一種教育新形式。在歐美等經濟發達的國家,繼續教育被視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也被視為教育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例如,1970 年 2 月,聯邦德國教育審議會通過的《教育結構計劃》中,將繼續教育作為一種獨立的教育實踐形式,與其他教育形式并列,按照教育的時間邏輯和知識成長邏輯,將教育體制確定為由學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繼續教育等層級構成。
(四)科技革命催生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
科技革命推動了高校與社會機構合作培養人才的模式。傳統的高等教育注重知識人才的培養,然而,科技革命推動了產業的迅速發展,社會廣泛需要的是創新型人才和實踐性人才。正如《學會生存》一書所指出的,科學技術的時代意味著:知識正在不斷地變革,革新正在不斷地日新月異。所以人們取得的教育共識是:教育主要任務不是致力于傳遞知識和儲存知識,而是更加注重創新和傳授獲得知識的方法。創新能力和動手能力的培養是現代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核心。因此,需要改變傳統的學校人才培養的一元化格局,形成學校、家庭、企業、社會等多元的交互式人才培養體系,構建“學校-企業”“學校-企業-研究所”“學校-企業-產業部門”等高校與社會機構聯合培養的新模式。
科技革命推進了國際高校聯合培養人才模式的常態化。世界各國科技體系的發展具有不平衡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科技發展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同一國家在不同的學科領域其科技發展狀況也不盡相同。任何一所高校都不可能培養出通曉所有高科技知識的“技術全才”。因此,合作辦學、師生出國交流等形式同世界上科技發達國家的高校之間聯合培養科技人才是現代大學國際化、開放式的科技人才培養模式的常態。美國是世界科技強國,學習與科技相關的專業也是去美國留學學生的首選方向。美國門戶開放報告數據顯示,2016-2017年,在美國的國際學生學習的前三個領域依次是工程,占當年在美國國際生總數的214%;商務和管理,占186%;數學和計算機科學,占155%。[20]
(五)科技革命從根本上改變高等教育內容與教學方式
科技革命推動高等教育內容的改變。一是新型學科的出現。學科是人類對知識體系進行分類所形成的科目或分支。現代科技的復雜性與綜合化需要各門學科理論之間的相互滲透與整合,系統化、整體性是現代科學的特點。這就導致高等教育傳統的學科門類的變化,大量新型的邊緣學科、橫斷學科、交叉學科不斷涌現。二是專業的調整。高校的專業是根據社會分工與就業情況來設置的,服務于社會職業的需要。科技革命推動的產業革命引發社會人才需求的變遷,高校專業也隨之調整,出現新舊專業的更替現象。在2017年度我國高校新增的2311個本科專業中,新增“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專業的高校就達244所。三是課程內容的拓展。“科學是通過課程而進入教育的”[21]。在古典主義教育傳統中,課程內容是以古典文科和神學為主。隨著科技革命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加深,自然科學知識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并對古典教育的課程內容提出了質疑。英國著名的教育改革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指出,“除了人數很少的某些階級以外,所有的人在做什么?他們都在從事商品的生產、加工和分配,而商品的生產、加工和分配的效率又靠什么?就靠運用適合這些商品各種性質的方法,靠在不同情況下相當熟悉它們的物理學的、化學的或生命的特性;那就是依靠科學這方面的知識,大部分在我們學校科目中沒有列入”[22]。17-18世紀,近代自然科學逐漸被納入英國大學的課程內容之中。2006年1月,美國前總統布什在其國情咨文中提出知識經濟時代教育目標之一是培養具有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數學(Mathematics)素養的人才,認為這種素養是全球競爭力的關鍵。STEM課程成為現代科技內容進入高校課堂的一種新形式。
科技革命推動高等教育教學方式的轉變。一是教學范式的轉變。科技發展需要創新型人才,好奇心、創造性的思維、發現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等是創新型人才必備的素養。“以教師為中心”的“權威式傳授與被動接受”的傳統的教學范式已不能適應新時代培養創新人才的需求。“以學生為中心”、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協作學習與探索問題能力的創新教學范式將逐漸取代傳統的教學范式。二是教學方法的虛擬化與信息化。科學技術對高等教育的影響、滲透,突出表現在教學中對網絡技術的應用。在新媒體的背景下,通過對互聯網絡、大數據等通信新技術的應用,高等教育中的教學內容呈現“數字化”的發展態勢,虛擬大學、數字校園、網絡課程、在線課程發展迅速;教學中翻轉課堂、游戲化學習、微課等虛擬學習方式與現實課堂的有機結合成為科技革命影響下新的教學方式。
在21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創新需要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人去實現相關目標。人才是創新活動的主體,是科技發展與進步的關鍵因素。人才培養是高等教育的首要和基本職能,為了迎接科技發展的挑戰,高等教育無論是在理念、結構、培養模式、教學內容與方式上都在不斷的變革之中。從目前世界科技發展視角看,在即將到來的、以生命科學為基礎的科技革命(時間周期大約是在2020年到2050 年之間)可能在兩個方面給高等教育帶來革命性變化:“一是學習革命。信息轉換器進入學校,人腦和電腦直接信息交流,學習成為“知識充電”,學校成為“心理培訓所”,人類從沒完沒了的學習壓力中解放出來;二是大學革命。大學轉變職能,從教育機構轉變為科研機構”[23]。如此一來,科技革命對于高等教育演進邏輯建構的力度,必將是前所未有。
參考文獻:
[1][德]伊曼努爾·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M].李秋零,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476-477.
[2][英]J.D.貝爾納.歷史上的科學[M].伍況甫,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81:626.
[3][美]I.伯納德·科恩.牛頓革命[M].顏鋒,等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5.
[4]錢時惕.科技革命的歷史、現狀與未來[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36.
[5][8][13]張密生.科學技術史(第二版)[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272,389,313.
[6]孫顯元.論歷史邏輯[J].安徽行政學院學報,2014(1):5-10.
[7][英]J.D.貝爾納.科學的社會功能[M].陳體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507.
[9][美]I.伯納德·科恩.科學革命史[M].楊愛華,等譯.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5.
[10]王守法.新科技革命對高等教育的影響[J].中國科技論壇,2002(3):47-52.
[11]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7:OECD Indicators[R].Paris:OECD Publishing,2017:25.
[12]教育部.中國教育概況——2016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情況[EB/OL].[2017-11-10].http://www.moe.gov.cn/jyb_sjzl/s5990/201711/t20171110_318862.html.
[14]Bijnens,H.et al(eds.).European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through Virtual Mobility:A Best-Practice Manual[M].Belgium:Heverlee,2006:26.
[15]潘懋元.教育的基本規律及其相互關系[J].高等教育研究,1988(3):1-7.
[16]瞿振元.實現高等教育現代化要理論先行[J].中國高教研究,2013(12):3-5.
[17][英]杰勒德·德蘭迪.知識社會中的大學[M].黃建如,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3.
[18]黃福濤.外國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41.
[19]林素川.從歷史到現實:科學技術的進步與教育的變革[J].教育理論與實踐,1992(1):2-5.
[20]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S.,2017“Fast Facts”[EB/OL].[2017-11-13].http://www.iie.org/Research-and-Publications/Open-Doors/Data/Fast-Facts.
[21]張楚廷.課程與教學哲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57.
[22][英]赫·斯賓塞.斯賓塞教育論著選[M].胡毅,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65.
[23]何傳啟.第 6 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方向[J].中國科學基金,2011(5):275-281.
(責任編輯 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