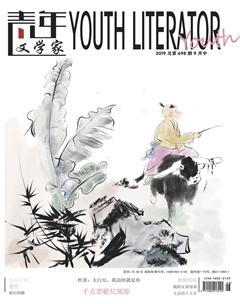論趙樹理文學創作的農民立場
王鳳杰 李祥耀
摘? 要:趙樹理的小說創作立足于農民立場,用通俗平易的語言,構建出一個新型的東方農村敘事模式。他的文學敘事具有超越性意義。這對當下的文學發展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本文通過梳理其文學創新,闡述其文學立場,挖掘其對未來中國文學的意義,思考東方文化振興和復蘇的方向。
關鍵詞:趙樹理;農民立場
作者簡介:王鳳杰,女,1996年生,浙江諸暨人,杭州師范大學錢江學院中文系學生;李祥耀,男,1978年生,江蘇贛榆人,文學博士后,教授。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6-0-02
長期以來,趙樹理的小說被普通讀者認為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政治化作品,忽略了其在文學藝術上的創新以及劃時代的探索意義。在當今面臨全面西化危機的中國文壇,如何去尋找一個不同于以往的中國化小說敘事的方式極為重要,趙樹理的文學創作恰恰為此提供了全新的道路指向。本文通過梳理其文學創新,闡述其文學立場,挖掘其農民立場之意義,以此再次肯定趙樹理特殊的文學價值,提高他在普通讀者心目中的文學地位。
一、趙樹理的農民立場
趙樹理的時代處于解放區和新中國成立后,他是40年代最炙手可熱的解放區文學代表。在解放區,改革如火如荼,新思想不斷涌入,農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了極大的關注。趙樹理少年時期在農村的生活經驗,使他從小熟知農村生活,所以能將心比心地為農民著想,從而更能理解在改革之際,農民心中對新思想的那份困惑。隨著1942年毛澤東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的理念,他發覺到了以往的文學和農民群眾是脫節的缺陷,自身的農村經驗加上政策的宣揚,使他走上了為農民為大眾的創作道路。
他曾經說過,“需知道這問題的提出是為大眾,不但是想讓文學漸漸走進大眾,有欣賞能力,并且有創造的可能和機會,使文學變為社會的東西,變成大眾,由大眾的東西。”[1]可以看出,趙樹理對于農民群眾的關愛體貼和同情理解,他認識到了如果仍然固執地保持五四以來啟蒙者居高臨下的知識分子態度,將永遠改變不了農民群眾蒙昧的現狀。要改變農民,必先走近他們。他認為農民的本性都是善良的,是可以改造的,就如身上所沾染的塵土,拍一拍就可以蛻變。趙樹理從文壇走下來,重新回到農村,走進大眾的身邊,他曾坦言自己的理想并不是做一個文學家,而是“做一個文攤文學家”,花幾毛錢就可以在攤子上買到他的作品來閱讀。他對自身讀者的定位就是普通的農民群眾,1943年出版的《小二黑結婚》在農民群眾中的得到了熱烈的反響,加印了好多冊,引發了“趙樹理風潮”。
趙樹理的寫作立場與30年代的左翼作家又是有明顯差別的,雖然二者都是刻畫農村和農民,但是角度還是不同。左翼作家的小說中,引起情節矛盾,主人公要走向進步之路的原因通常是由于階級矛盾。如葉紫的《星》,深刻地揭露了農村的階級壓迫對梅春姐的迫害,從此她由一個被踐踏的平凡青年婦女,一步步走上了婦女解放的道路,成為農民運動中的中流砥柱。主人公身上洋溢的理想主義光輝是受壓迫者的吶喊,強烈地表現了階級矛盾。而趙樹理小說中推動故事進程的矛盾點卻是出于民俗,如《小二黑結婚》中的矛盾點是因為父母不同意小二黑和小芹的婚事進而引發的一系列追求婚姻自由、破封建的故事。如《李有才板話》,是因為地主閻恒元明明貪污盜竊,卻騙得了“模范村”的榮譽,李有才帶領小輩,用快板同他們斗智斗勇的故事。這兩個小說的矛盾點全然不像葉紫的《星》那樣有昂揚的階級斗爭基調,而是樸實又生活化的,這恰恰能被農民群眾所理解。農民群眾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階級矛盾”、“革命”這樣的詞對他們來說太過于高深,是沒辦法理解的。就像魯迅筆下的阿Q,他并不明白革命是什么,卻嘴上總是喊著革命,是因為他只知道喊著革命對他自身利益有好處,所以他就支持革命,實際上他對革命的意義一無所知。趙樹理正是抓住了農民的這個特質,所以他的故事矛盾以農民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的事情出發,如婚姻問題、財產問題等,這樣的文學才更貼近農民群眾,農民朋友才愿意去讀,也就自然而然吸收了小說中所蘊藏的進步思想。
二、趙樹理農民立場的創作突破
(一)突破五四以來的敘事角度
五四是一個革命的時代,為了挽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中華民族,新一代的知識分子發起了文學革命運動,他們承擔著思想啟蒙的重任,以激烈昂揚的姿態全力擺脫舊文學舊思想的束縛。至此,中國文學廣泛吸收西方文學思想,倡導白話文寫作,與傳承兩千多年的中國傳統文學徹底決裂,走上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道路。
新文化運動以來,以魯迅為主的作家,開辟了一條以國民性批判為主題的小說道路。他們的創作目的是動搖固守在人們心中的封建思想,以此改革中國,拯救生活在苦難中的民眾。這個民眾的主體中包括了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小農經濟中生活的主人公——農民,這是中國一個極其特殊重要的群體,他們善良勤懇,卻又愚昧奴化。在趙樹理出現以前的文學作品里,作家們通常是以俯瞰的姿態來描寫農民,而作家們的身份通常是知識分子。如魯迅,他出身于一個書香門第的貴族家庭,后遭遇家庭變故,才使他深刻地感受到封建思想對于民眾深深的毒害,才有了喚醒蒙昧群眾的作家理想。“喚醒”一詞就注定了他和他筆下的那些農民是處于一種割裂狀態的,他試圖喚醒他們,試圖引領他們,做他們的啟蒙者,對他們感到同情和憐憫,卻永遠不可能和他們站在相同的位置上,與他們對話時思考他們真正的生活需求。
而趙樹理則開創了真正為農民而寫作的小說。在閱讀魯迅和趙樹理的小說作品中,可以明顯感覺到兩者寫作立場的差距。讀魯迅時,是“唉,他們怎么這樣”的感慨,而讀趙樹理時,是“喔,原來他們是這樣生活”的理解。從兩個截然不同的閱讀體驗中,可以體會到魯迅的寫作動機是首先站在國家利益的角度上的,為了國家的先進發展,所以要改造蒙味的 愚民。他避開農民的日常生活,把筆墨著重落在描寫農民封建落后的思想精神上,他要的是農民的覺悟。可結果卻不盡人意,他的書在知識分子和普通市民階層里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進程,使啟蒙思想在中國得到了普遍傳播,但是卻幾乎沒有農民愿意看他的書。五四以后整個中國展現出蓬勃新生的反封建圖景,在農村卻仍舊是一片死寂。趙樹理把魯迅的書給他的父親看,父親并不樂意讀下去,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他開始思考農民需要的到底是怎么樣的文學這一命題。
趙樹理從小生活在農村,接受著封建思想的教育,他曾經同千千萬萬的農民一樣愚昧過。若不是日后經受了知識分子的教育,他長大后的生活軌跡也會同普通農民一樣,并無差別。所以他才能理解農民,了解他們的精神訴求和合理愿望,并且切身站在農民群眾的角度上,迫切地希望改變他們的生活情況。關心農民的文化境況、信仰價值和行為方式,做農民真正的代言人,從而寫出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他對農民的同情不同于五四時期作家們對農民愚昧無知的痛心和憐憫,而是講述農民因生活環境造成自身固有的特質,擺脫舊習俗的困難,更多的是娓娓道來的教育引導。趙樹理突破了五四以來以啟蒙者知識分子的高傲姿態寫作的敘事角度,創造出一種符合農民趣味,關心農民利益的敘事方式。
(二)語言體式的改變
趙樹理曾說,他每當寫作的時候,一直不會忘記他的作品是寫給農民讀者讀的,照顧農民群眾的鑒賞習慣和審美水平是他小說創作中的關鍵點。已經站在農民的立場上去寫作了,那么第二點就是尋找一種恰當合適的語言類型和文章體式令農民群眾喜聞樂見。在語言使用上,他采用了近乎口語的文字表達,貼近農民的文化底蘊和接受能力,批判繼承民間文學的精華與糟粕。在文章體式上,他采用了傳統文學中章回小說的樣式,一章一個主題,故事緊密相連,環環相扣,段落整齊,通俗易懂。在敘事視角上,采用的是對整個故事情節結構能全部掌握的全知上帝視角,使看故事的人沉溺其中,迫不及待想要知曉接下來的故事發展,引人入勝。趙樹理語言文字的樸素和小說體式的通俗傳統,這種貼近農民生活,寬厚質樸而又簡單自然的文風吸引了眾多農民群眾,在鄉村讀者里造成了極大的轟動。
三、趙樹理農民立場的文學價值
(一)對為意識形態而寫作進行反思
1958年“大躍進”期間,趙樹理創作出《鍛煉鍛煉》,被批判不夠“典型化”,善于表現落后的一面,又不善于表現前進的一面。趙樹理批判“小腿疼”和“吃不飽”兩位落后的農村婦女,可內含的卻是對她們深深的同情。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文學環境都是相當激進的,干部們為了實踐政策,“不把人當人”的蠻橫做法沒有人敢說,但是關心農民的趙樹理已經發覺了。他拒絕書寫“典型化”的“理想主義”作品,以一種微弱的姿態開始反抗這個文學傾向。正是這種在當時被認為跟不上時代的做法,在如今看來,卻真正體現了趙樹理在文學創作上的價值與意義。他才是那個永遠心系農民群眾,一心為農民說話的人。他主動放棄了為政治意識形態的寫作,盡管那是猶豫的,不尖銳的,略顯退緩的,但是對于他那時的文學地位來說已經是相當艱難的一件事了。沒有了40年代與政治意識形態相統一的干擾,在巨大的政治壓力的包裹下,趙樹理的農民立場才完全顯現出來,彰顯出趙樹理豐富而深沉的人格魅力。
(二)為未來中國文學提供借鑒
中國從揭開現代序幕以來,幾乎被西方文化概念中的線性時間發展模式所同化,本民族傳統敘事模式被視作一種落后的存在慢慢被拋棄,“安于土地和安于生存變成了一種貧窮和恥辱”[2],多數人認為描寫鄉村是展現國家落后一面的可恥行為,是作家和導演們為了獲獎而不擇手段的方式。當今世界的一切變化太快,人心躁動,人人活在不得不努力的焦慮不安中,從古老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另一種靜謐與安寧成為一種時代任務。
中國農村的未來建設離不開文學的書寫,而文學也離不開這樣珍貴又獨具特色的傳統文化載體,世界也同樣需要這樣一種非西方文明來調和全面西化造成的危害。而趙樹理曾經就構建了這樣一種新型的東方農村的敘事模式。在當下,這極具超越性意義,當今作家可以從他的作品中得到很多啟示,找到最適合中國文學未來的發展道路。
趙樹理的文學創作是東方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文明結合的最佳范例。當前中國文學需要的正是這樣一種不被西方文化侵蝕,能夠發揚自身傳統文化的文學敘事模式。發掘趙樹理文學作品中傳統文化與現代性兼具的文學創作方式,可為新時期中國文學的發展提供極富意義的借鑒。
注釋:
[1]1934年趙樹理在山西地方刊物上發表《歐化與大眾化》。
[2]劉旭.東方循環時間觀與東方化敘事建構的可能.當代文壇,2019(03):136-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