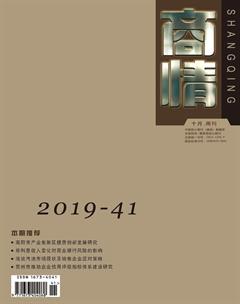以勞動時間來分析經典勞動理論的創新
崔麗燕
【摘要】勞動時間是勞動力市場的重要變量,本文探討了關于勞動時間的生理臨界、生存的需求與異質勞動者三個假設,以此推出勞動供給模型,實現了對于經典勞動理論的創新擴展。在此過程中表明,客觀約束在影響微觀經濟決策時比主觀偏好的影響更加直接,效用最大化假設也并非時總體勞動供給模型的基石。
【關鍵詞】勞動時間?勞動理論?客觀約束?效用最大化
1效用最大化與加總問題
傳統經濟學將視線的焦點集中于宏觀現象背后的微觀基礎,在效用最大化這一理論假設的基礎上,微觀經濟理論在數十年的時間不斷發展,這一理論大廈為個體選擇提供了的理性基礎,同時也為諸如失業、通貨膨脹以及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構建了一座橋梁。基于效用最大化理論所導出的個體供給和需求模型內在具有的基數特性可以較好地解決效用函數本身不能加總地難題。若能在控制商品所具有地特殊稟賦的基礎上保證不同的個體卻指向同一類產品,就能夠確保商品本身所具有的同質性,進而可以由微觀層面的決策結果推導出宏觀總體的趨勢,這便是微觀經濟學基本模型所遵循的主要思路。
這一思路在學術上總體沒有爭議,唯一的反思點就在于“加總難題”,也就是當微觀個體的差異非常顯著之時,橫向加總的結果會與單個個體的決策結果恰好相反,這便形成了矛盾。因此,如何尋求代表個體效用的表達式就落在了特定的函數模型設定上,這一設定即是使微觀決策與宏觀趨勢保持一致性,這一思路在奈爾遜看來就是為了賦予宏觀經濟學而以微觀基礎來進行賦予,可以說是一種強迫,把“加總難題”間接轉化成了“還原問題”。
由于凱恩斯學派的巨大影響力,“加總難題”一般很少涉及勞動力市場的討論而是聚焦于廠商的生產領域。勞動經濟學理論的停滯不前使得研究者還尚未意識到勞動供給決策的經驗研究已經數據方面給“加總難題”帶來了困難。接下來本文探討的主題將會集中于有關勞動時間的研究,從而指明所謂的相互矛盾不過就是“加總難題”在勞動市場上的表現而已。
2圍繞加總難題和勞動供給理論的研究
2.1圍繞加總難題的研究
加總難題是在20世紀50年代被美國學者提出,羅賓遜在研究的時候發現,主流經濟學刻畫總體生產函數有問題。總體生產函數F=F(K,L)中K指的是資本存量的加總,而當經濟中如果存在異質資本商品之時,資本的計量便不能再基于實物的數量之和,故此對于異質資本商品的加總需要使用其他的指標。可行的指標包括按資本品的生產率、按資本品的購買力、按資本品的生產成本,這些指標均涉及到了資本的價值量,度量這些指標必須要考慮到折舊問題,資本存量又影響著價格,因此資本存量的度量不能獨立決定,其內生于經濟運行當中。實質上說,羅賓遜指出的“資本加總悖論”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名義價格變量的確定沒有實物基礎。
迪頓曾為了構建起代表消費領域的需求體系,嘗試從成本最小化的角度出發分析需求,他提出了AIDS成本函數,可以推導出任何一組需求函數的一階近似,并且基于效用最大化。在波動較小的情況下,n個家庭商品支出匯總的總支出Y恰好代表了一個家庭總支出等于Y/n時的消費決策。換句話說,無論總支出如何在n個家庭之間進行分布,都不會影響到這一組家庭整合之后的消費支出狀況。這個結論比較重要,它可以避免因消費偏好與家庭收入相互影響而產生的恩格爾效應。米爾鮑爾也曾專門提出一個理論,探討群體偏好的成立條件。
因此可以看到循環邏輯的危險,微觀經濟理論的豐富與完善本是為了給宏觀經濟學堅實的地基。比如,卡爾多指出的典型事實讓學者們意識到經濟中的很多趨勢并非無跡可尋,不僅如此還能夠保持一定時期的穩定性。為了更好地解釋這一穩定性,學者們開始不斷地對個體多樣的行為進行建模,然后依據模型能夠擬合現實的程度來判定不同微觀設定的優劣。比如,泰勒曾經清楚地在宏觀經濟學手冊注明,粘性工資和粘性價格的討論是為了解釋經濟學家們所觀察到的貨幣、通脹和實際產出的若干現象。泰勒在充分比較不同的價格和工資設定理論之后認為,滯后合同模型所推導出的結果與宏觀事實更為接近,并隨之探討了滯后合同模型所涉及的微觀決策機制。為了不使代表性消費者受到宏觀機制影響,個體所具備的偏好差異可以被假定為無,從而完全忽視現實世界所具備的個體異質性的豐富多彩,這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部分理論研究的初衷。
綜合起來,宏觀經濟學以之為基礎的微觀經濟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個體效應的加總結果在存在異質性的情況下可能會產生突變,進而得到完全不同的總體結果,故此應該更加關注分解而非加總的過程,這與“加總難題”的預設便有所不同。
2.2圍繞勞動供給的理論和經驗研究
價格理論直接應用的體現時對勞動供給決策的分析,這是傳統微觀經濟學的觀點。價格變化會從兩方面影響需求: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對于正常的商品,無論替代效應還是收入效應都是同向,也即負方向。相反的,劣等品替代效應是負方向而收入效應是正方向,也即意味著價格提高而需求反而增加。如果假設空閑時劣等品,工資變動便會在兩種情況下影響勞動時間,繼而產生倒C型勞動供給曲線,而麥克唐納則認為需要額外設計比較復雜的主觀效用模型方可做到。德賽因在家庭成員聯合效用函數模型的基礎上導出了倒S型曲線,這進一步拓展了倒C型曲線。韋爾默朗在對單一和聯合勞動決策模型分析的基礎上認為,單一決策模型會更符合于單身人群,卻不適合結婚人群,相應的聯合決策模型更加擬合于后者的決策現實。
勞動供給模型的經驗探究也聚焦于家庭問題,比如在壓力狀況下,女性勞動者如何進行勞動供給決策,并嘗試將其他微觀機制諸如稅收機制、通勤時間等與勞動時間的供給決策相互聯系起來。跨期勞動供給彈性則是針對勞動供給曲線經驗估計的重點。埃夫斯對經驗研究的結果進行深入分析,發現之前的研究估計值相差較遠。他認為,經濟學家無法就使用哪一種彈性水平才適合政策評估達成一致的認識。很多學者嘗試如何才能將彈性波動的來源解釋清楚,有些學者認為這是由于稅收制度的再分配導致,有些學者則認為稅收對于勞動供給的影響微不足道,關鍵點還是在家庭維度上,諸如家務活對于有償勞動的替代、家庭的生存需求以及成員之間的相互替代。不管是哪一種研究,都不過是加總之后的結果,而由于微觀數據獲得性難度較大,只有少數研究對于微觀方面的勞動供給彈性進行了估測。
又一經濟學家對于紐約出租司機的勞動決策進行了詳細追蹤,這些出租司機能夠自己控制勞動時間并進行勞動決策,這為從司機每天營業狀況和工作時間推測個體勞動供給狀況提供了方便。研究者發現,出租車司機并不是營收越多工作時間越長,關系恰恰相反,即收入越高,這些司機就會選擇提早收工。還有其他的經濟學家也進行了相似的跟蹤,發現的結果是不同的,即出租司機決定收工的遲早是由之前累積工作時長決定的,這比較能夠說得通,因為累積工作時間越長,司機們就會選擇給自己的身心放松一下,即使在當天收入比較低的情況下也是如此。這兩批經濟學家之所以得到不同的研究結果,是因為之前的研究都是通過工作時長來計算收入而不是司機的載客量。第三類經濟學家則運用新加坡的最新出租車司機的數據,結果發現目標收入值較大地影響了出租司機地勞動供給決策。綜合來看,現有的研究越來越關注家庭維度對于勞動供給理論分析的影響。
3關于勞動者異質性的研究
上述針對勞動需求的分析,并沒有嚴格觀察不同勞動者的勞動能力,而是采取了簡化處理,即認為所有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時間都是同質的、沒有差別的。這很明顯不符合經濟學嘗試。因此有必要針對勞動者的異質性進行下一步研究。
不同勞動者再生產自己勞動力的成本不盡相同,并且他們創造價值的能力也不盡相同。基于勞動者工作時長的加總而得到的勞動供給曲線假設,并不是說明不同勞動者具有相同的勞動能力,而只是作為一種解釋,說明雇主可能不能甄別不同勞動者之間的差異。那么企業怎樣才能進行區分呢?盡管勞動力市場存在形形色色的信號傳遞、甄別以及篩選機制,但是讓企業一個一個進行勞動者勞動能力的評估實在會耗費較大成本。
現在建立一種假設,企業只能夠區分三類不同的勞動者,分別是低水平、中等程度、高水平,那么三者在勞動供給曲線的主要差別就在于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再假設這三類勞動者的勞動力再成產成本所在區間皆不相同,那么這三類勞動者必然對應三條總勞動力供給曲線,每一條都是內部橫向加總的體現。在進行模擬之后,三條曲線全部呈現出倒C型,如果進一步對比,低水平勞動者供給曲線更加近似于水平線,也就是學術上通常說的“無限勞動供給”。這給企業提供了一個啟示,只有提升工資率才能夠吸引更多的中水平勞動者。研究過程盡管沒有遵循主觀效用函數最大化的設置,但是研究的結果卻與新古典經濟學的成果比較類似,這進一步證明了總體結果相對于微觀組成的突變特性。
4結論
綜上所述,學術研究針對于勞動供給決策通常都是參照著新古典經濟學所提出的“主觀效用最大化”,沒有在意從微觀到宏觀、個人到總體的過程會存在“突變”的可能性。傳統經濟學對于勞動供給曲線的估值與實際現實相差比較大,而針對差異的解釋也不盡相同。本文基于勞動力再生產理論,建立了勞動時間的政治經濟學模型,巧妙地模擬了勞動力供給曲線以及倒S型曲線,拓展了經典勞動理論。并且研究結果說明,分析個體性差異以及總體加總的突變性會更加有效相對于觀察代表性個體而言,而主觀效用也沒有客觀約束更加直接。
參考文獻:
[1]陳瑞琳.勞動時間的政治經濟學分析[J].政治經濟學評論,2017,8(1):186-206.
[2]韓丹.計量經濟學方法之時間序列分析[J].市場周刊,2018(7):90.
[3]王倩.企業節約時間與提高經濟效率的經濟學分析[J].消費導刊,2018(19):202.
[4]鄭曉康.龐巴維克經濟學時間觀的思考[J].華章,2010(34):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