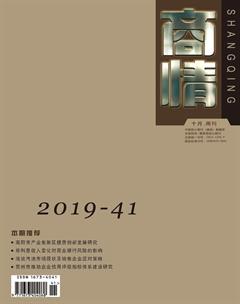簡析侵權責任法上共同侵權的特例
【摘要】《侵權責任法》中,就教育機構作為特殊主體成立共同侵權時存在著立法的不明確。本文通過法理和價值分析對《侵權責任法》第12條規定的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與第四章中規定的教育機構承擔侵權責任發生法條競合時,如何適用法條,提出筆者的分析。
【關鍵詞】共同侵權 教育機構責任 法條競合
引言:我國《侵權責任法》在立法模式上采取了一般條款和具體列舉相結合的方式。一般條款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涵攝性,對于未來新型侵權行為的發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具體列舉則是針對被類型化的特殊侵權類型,單獨在分則中進行的具體規定。這樣的立法模式就是典型的潘德克吞學派總結的民法典的體系結構——總分結構。據此分析,我國《侵權責任法》第四章關于責任主體的特殊規定是總則還是分則,實難形成定論,當涉及到第四章的適用時,不僅要求運用法學基礎理論積極主動解釋法律,更要求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之,對《侵權責任法》中的共同侵權特殊形態的探討和論述則顯得尤為重要。
一、由教育機構作為共同侵權人案件責任承擔引出的問題
案例:端午節前夕,劉某照常去上學,但不久就傳來劉某在人工湖中溺水身亡的噩耗。事發當日系學校正常上課期間,區小學根據上級主管部門的安排,在學校開展“慶端午”的社會實踐活動,考慮到低年級學生參加活動存在不安全因素,故決定組織六年級學生參加本次活動,對低年級學生予以放假。由于校方沒有采取合理的方式通知到劉某的父母,致使其父母不知劉某放假,疏于管理,最終貪玩的劉某在人工湖溺水身亡。事后經查明,區水務局雖不是該人工湖的建設者和施工人,但依據法律規定對轄區內的河道負有行政管理職責,包括竣工后的人工湖。而區水務局作為涉案水道的管理單位,在工程完工后沒有在涉案水域附近采取相應的安全措施,未設置任何安全防護設施,也未設置警示標志,區水務局在監管涉案水域過程中存在過錯。
就上述案件在審理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同的意見,一種觀點認為應當作為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處理,適用《侵權責任法》第12條規定;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應當作為校外第三人侵權,適用《侵權責任法》第40條規定。
二、對教育機構作為共同侵權人案件責任承擔的法理分析
通過法條解讀和法理分析,侵權責任法第12條規定的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其實即指數人基于分別行為而致受害人損害,主觀上行為人之間無意思聯絡,不存在共同過錯,由加害人分別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此條規定的特點就是“分別實施、結合造成”。具體就是:一是數人分別實施侵權行為,但沒有共同過錯。二是造成同一損害。三是各個行為均不足以單獨導致損害結果的發生。對此類無意思聯絡的的數人侵權,應適用按份責任。各個行為人要根據其責任的大小承擔相應責任。
侵權責任法第40條規定的是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行為能力的未成年學生在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學習、生活期間,受到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以外的人員人身損害的,就是第三人造成學生損害的。首先由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教育機構未盡到管理責任的,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
教育機構有過錯時,不是和實際侵權人一起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而是僅僅承擔補充責任。這樣從直接侵權人和教育機構的關系來看,兩者雖然是基于偶然的原因而對受害人承擔責任,但表現的卻是不作為與作為結合的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
三、對教育機構作為共同侵權人案件責任承擔問題的解決
學校的責任最終是以原因結合的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承擔按份責任呢,還是以校外第三人侵權學校只對自己的過錯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呢,顯然這是一個法律適用方法上的問題,不僅是法條的選擇適用問題,更是法律價值取向的問題。筆者傾向于適用后者,其理由有如下幾點:
第一,校外第三人侵權其實是原因結合的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的一種特殊形式,只是由于其中的一方是學校這樣一個特殊的主體,法律做出了不同的價值選擇。即是說校外第三人侵權在形式和內容上是完全符合原因結合的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的,無論是構成要件還是侵權形態上,唯一不同的就是基于責任主體的不同身份法律給其設置了不同的責任形式,如果不是特殊的主體直接按原因結合的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承擔按份責任即可。
第二,法律對這種特殊主體另行規定,其實亦是價值衡量的結果,就學校來說,具有公益性質,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事業單位法人,它的責任能力其實是有限的,如果讓其承擔過重的責任,會影響到學校的生存和教學質量的保證,最終影響的是教學關系的和諧,所以對于校外第三人侵權,法律規定了學校只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
第三,就整個《侵權責任法》的體系來講,原因結合的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屬于一般規定條款,而校外第三人侵權屬于特殊規定,是在原因結合的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的一般規定中,考慮了行為人的特殊性,而做出的特殊條款,是法律和社會價值衡量的結果。綜上,筆者認為在原因結合的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與校外第三人侵權出現競合的情況下,應優先適用特殊條款,按校外第三人侵權對待,讓學校承擔與其過錯相適應的補充責任。
第四 ,就《侵權責任法》的法律結構來說,很多學者認為《侵權責任法》第四章關于責任主體的特殊規定,既不是總則也不是分則,而是起連結總則與分則作用的過度篇章。在具體適用時應作法律解釋和個案分析。就教育機構責任的規定來說是屬于具體的、特例的規定是特殊條款,傾向更多的是分則的成分。
綜上,筆者認為在原因結合的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與校外第三人侵權出現競合的情況下,優先適用特殊條款,按校外第三人侵權,讓學校承擔與其過錯相適的補充責任。
結語:法諺有云:法無解釋,不得適用。如何使《侵權責任法》這部“紙面上的法律”變為“行動中的法律”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從靜態的法到動態的法,實現立法的最終目的,不是僅僅確立了科學的法律條文,更為重要的是對這些條文的適用,具體的調整社會關系、處理實在糾紛。以共同侵權來說,類類種種、形態萬千,這里筆者只就教育機構作為共同侵權人這一特例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見,希望對我國《侵權法》的完善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參考文獻:
[1]王利明.中國侵權責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400.
[2]楊立新.侵權責任法條文背后的故事與難題.法律出版社,2011.158.
作者簡介:岳紅艷,畢業于西北政法大學,天津招融律師事務所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