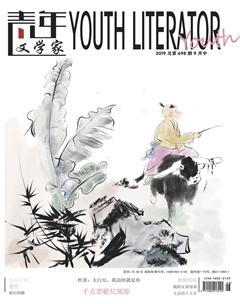四川綿陽方言芻議
胥爽
摘? 要:四川方言屬于西南官話,西南官話的范圍很廣,包括了云貴川的大部分地區,西南官話在漢語方言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綿陽方言屬于四川方言的次方言區。雖然不及成渝片區的方言具有代表性,但是自身也有一些獨特的特點。
關鍵詞:綿陽話;方言系統;內部差異;形成原因
[中圖分類號]:H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6--03
引言:
四川方言屬于西南官話,西南官話在漢語方言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綿陽位于四川省西北部,涪江中上游。綿陽北接甘肅文縣,南臨遂寧射洪縣,東臨廣元劍閣縣,南充的南部縣,西部與阿壩藏族自治區接壤。古代歷史上出現了幾次大規模的移民,老四川話和移民的方言不斷地融合,形成了新的方言“湖廣話”。綿陽位置偏北,受“湖廣話”影響較大。以綿陽為例,∕?∕的讀音與成都話不同,其中,綿陽話的∕?∕的讀音更高。而湖南話中∕?∕的舌位也是較高的。
一、綿陽歷史沿革與行政區劃
綿陽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底蘊。從公元前201年漢高祖設置了涪縣開始,歷來為郡縣州府治所。東漢末年,劉備據蜀,改名為“綿州”。據《三國志》載:“先生入涪,宴于山上,顧謂龐統曰‘此州之民,其富樂乎?”綿陽富樂山因此得名。據《天下郡國利病書》載,“左綿界東、西二川,北負梁雍,風氣所濡,各得其偏,故其俗文而不華,淳而不魯,剛而不狠,柔而不弱。”綿陽人性格溫婉、和悅。語音也有自己獨有的特點。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綿陽的元音∕?∕的舌位高低與四川其他地方不同。綿陽的元音∕?∕的舌位最高,成都發元音∕?∕的舌位最低,德陽的元音舌位居中。
二、選題緣由
筆者家鄉四川綿陽,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人,對家鄉方言比較了解。第二個原因是隨著普通話的普及,方言的影響被大大的削弱了,方言漸漸地進入了一個極為不利的地位,許許多多老一輩的方言發音和方言詞匯,我們已經聽不到了。筆者希望通過自己所學的語言學知識對從老一輩尤其是七八十歲的老人的那里收集的語料資源進行分析,希望為家鄉的方言保護盡一點綿薄之力。
三、研究現狀
目前,關于四川方言的研究較多,其中尤其是以研究成渝片區的方言為最多。成渝方言作為四川方言中的主流語言,研究成果頗為豐富。這些研究成果中,以《四川方言調查報告》和《四川方言音系》最為系統。然而,因為年代久遠,加上四五十年代條件有限、收集資料不夠全面,所以這兩本巨著并不能很詳細的闡述某一些次方言區的語音特點及其演變的內部規律。近幾年,又有很多學者對各個次方言區進行詳細的挖掘,由點及面,細致地闡述了次方言的內部特點及細微差異。李大鵬《四川方言鼻邊音不分說》以鼻邊音作為切入點,結合各地區方言的實際情況,從音韻學的角度對四川各個地方方言進行詳細的比較。顧盼《四川綿陽方言音系分析》一文中通過與北京話比較,對四川綿陽方言的聲韻調系統和其語音特點進行描寫。其中,還將綿陽話與成都話、重慶話在細微處進行比較。[2]李東穗《四川樂山方言系統研究》對樂山方言與普通話和中古音進行對比,找出其異同點并探尋其演變規律[3]。周及徐《從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歷史-兼論“南路話”與“湖廣話”的區別》一文根據移民歷史和四川地區的方言地理分布情況對其形成的“湖廣話”和“南路話”之間的差異進行分析,從而總結出四川西南地區方言音系和語音特點[4]。蔣紅柳《漢語方言變異與普通話的推廣》一文指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語言也發生了相應變化。由于普通話的廣泛影響,各方言區人民交流與融合日益深入,使得方言間不斷融合甚至趨同[5]。周巧媛《成都方言語音問題研究》[6]把成都方言作為一個專題來研究。對成都方言進行系統有效的田野調查,通過傳統的聽音辨音手段來分析和描寫成都方言語音特點。其次,在描寫的基礎上,以音變理論、歷時和共時比較法、社會語言學等理論為依據,進行歷時和共時的對比分析,描寫成都方言的主要語音特點,并總結規律、分析成因。[6]
在筆者看來,方言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語言現象。目前,四川保護的較好的方言要數洛帶古城地段。當地建筑是典型的客家建筑,而當地人也秉承著“寧丟自家田,不丟自家言”的祖訓,力求保護好自家方言。所以,當地還保留了較完整的客家方言。這無疑是“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的鐵證了。
李如龍在《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7]中指出:“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自然包含著語音、詞匯和語法的比較。在語音方面,語音的比較應該擴大視野。在語音方面,以往的比較多限于音值的異同和音類的分混,這是受到傳統音韻學的局限。從現代音系學的觀點來看,音類如何組合成音節便是結構系統的重要課題,什么音充當介音和韻尾,什么音可以自成音節,聲韻調之間組合的可能度有何不同?”筆者重點從聲母、韻母、聲調及其拼合規律還有一些典型性的方言詞匯來探討綿陽方言系統。
1、聲母
綿陽方言輔音聲母共19個,與普通話相比,無翹舌。

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四川方言[h]、[x]不分,把湖南的湖讀作[fu35],把葫蘆讀作[fu21nu21],把花讀作[fa]。“葫蘆”在口語中還讀兒化[fu53ner55]。“葫蘆”在一般用前一個音,但是在一些口語中,比如形容一個人其貌不揚,又矮又胖,就會說“長不像冬瓜,短不像葫蘆兒”這里就變調為55調,并且有兒化。蛤蟆四川話讀作[xa21ma55]或者[t?h21me55]。綿陽方言屬于四川方言的此方言區,有幾個音明顯有缺陷(或者說在方言發音里沒有這個音):在普通話發音中,zh[t?]舌尖后、不送氣、清、塞擦音;ch[t?]舌尖后、送氣、清、塞擦音;sh[?]舌尖后、清、擦音。四川方言發不出翹舌,將幾個部分分別讀作c[ts]舌尖前、送氣、清、塞擦音,s[s]舌尖前、清、擦音。z[ts]舌尖前、不送氣、清、塞擦音。這是因為四川人發音舌位靠前,導致了發音的不足。
2、韻母

據我們查證,陰聲韻:元音韻尾和無韻尾;陽聲韻:是以鼻音為韻尾;入聲韻:是以塞音收尾的韻母。因為綿陽方言輔音沒有zh、ch、sh,所以它的韻母沒有普通話的韻母-i,也沒有后鼻韻ing、eng/weng,所以綿陽方言大多發陰聲韻,其中,陽聲韻和入聲韻較少。
3、聲調
綿陽方言屬于四川方言的次方言區。四川方言古音中的入聲字歸陽平。
綿陽方言的聲調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其調值皆與普通話相異。綿陽話中,陰平調值記作 45,陽平調值記作 21,上聲調值記作 53,去聲調值記作 213,經查證,綿陽方言中的入聲字在方言中均讀陽平。如綿陽方言的“教育”的“育”在方言中讀陽平35調。這一點,與四川方言是有共性的。
4、方言詞匯
李如龍在《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中指出: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自然包含著語音、詞匯和語法的比較。在詞匯方面,就“方言”這個術語來講,既包括社會方言,也包括地域方言。但本篇文章主要講的是地域方言。方言是流行于一個地域的語言,承載了這個地域的文化。很多人擔憂方言會被普通話同化,事實上,方言在與時俱進的發展。綿陽方言處于四川方言的次方言區,詞匯上大體相似。普通話中有一個詞匯格式“可憐巴巴”,“巴巴”表示一種狀態。邵敬敏在《ABB式形容詞動態研究》[8]中指出,ABB式形容詞的靜態結構一般都分析為“A+BB”,但從形成ABB的動態結構方式來看,情況又會不同了。BB也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可以單獨成詞的,比如“巴巴”。另一類不能單獨成詞,永遠只是一個構詞成分,如“燦燦”等。在四川方言中有“巴沙”在四川方言中是一種很常見并且能產性很強的語素,也表示一種狀態,多表示不好的狀態或者消極的意義。“心慌巴沙”、“嚇人巴沙”、“笑人巴沙”、“焦人巴沙”、“可憐巴沙”、“妖艷巴沙”。“巴沙”在這里的作用是湊成了音節,至于“巴沙”是否做為“類詞綴”或者“詞綴”,這個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加以驗證,目前,我們只能說“巴沙”處于一種虛化的過程中。同理,還有一個例子,在天蒙蒙亮的時候或者天快黑的時候,看東西看不太清楚,從“麻沙”到“麻沙沙”,這里是AB+B→ABB(后重疊擴展式),我們也可以說“麻沙”還有ABAB重疊變式,“麻沙麻沙”綿陽方言經常說:“天麻沙沙的”,指早晨或者傍晚光線不好,看不清路,這里“麻沙”做為疊韻詞,從“麻沙”到“麻沙沙”是一個構形上的重疊,“麻沙麻沙”也是其重疊變式,這里表現了語言由動態到靜態的一個發展變化趨向。
綿陽位于四川東北部,深受巴蜀文化的影響。方言詞匯也獨具巴蜀特色。四川方言歇后語中就有很多別具特色的方言詞匯。“癩蛤寶兒吃豇豆兒-懸吊吊的”這里面的“癩蛤寶兒”就是我們常見的蛤蟆,書面語叫蟾蜍。蛤蟆在綿陽這一帶有著多個讀音[xa21ma55]、[t?hie21mer55]、[t?hye21mer55](這幾個音在實際運用中還有上聲的變調)。蛤蟆還有一個叫法叫癩格寶、癩克寶、癩蛤蟆,據《漢語大詞典》記載,蛤蟆還有一種說法“蟆蟈”。“我看把她放了吧,反正一只蟆蟈也沒多大用處。[10]”
5、方言的現狀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大力推廣普通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文字法》更是以法律形式確立了普通話的特殊地位。普通話的推廣,確實讓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人們溝通、交流更加便利。另一方面,這一舉措也把普通話推上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勢必會削弱方言的影響力。現在綿陽很多家庭,父母會講方言,孩子只會說普通話。這可能是方言環境缺失所帶來的影響。如若這種狀況發展下去,那么,方言的可能會逐漸消亡。漢字如果消亡,我們可以在古籍中找到,但是,方言一旦消亡,就會無影無蹤了。
六、結語
綿陽方言具有獨特的特點,在聲、韻、調方面都跟成渝話有很大的不同,在方言詞匯上也有細微的差異。從方言史角度來看,綿陽話可以作為移民融合而成的“湖廣話”的代表。綿陽話語音上最大的特點就是綿陽的元音∕?∕的舌位較高。因此,本文采用共時和歷時結合的研究方法,從聲、韻、調方面將綿陽方音系統分別同普通話進行對比分析,更加生動地展現出綿陽方的特征。此外,本文還通過結合綿陽歷史,從移民歷史的角度探尋了方言差異的根本原因。
本文對綿陽方音系統的研究,是將語言學、方言學、歷史學結合起來的一次大膽嘗試,但由于筆者能力有限,未能將方言同中古音作對比分析,這一點還需在今后的學習中積極探索。
參考文獻:
[1]李大鵬.四川方言鼻邊音不分說[J].劍南文學,2011(4).
[2]顧盼.四川綿陽音系分析[J].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10(10).
[3]李東穗.四川樂山方言系統研究[D].江西師范大學,2017(6).
[4]周及徐.從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歷史-兼論“南路話”與“湖廣話”的區別[J].語言研究,2012(7).
[5]蔣紅柳.漢語方言變異與普通話的推廣[J].第七屆中國語音學學術會議暨語言學前沿問題國際論壇,2008.
[6]周巧媛.成都方言語音問題研究[D].天津師范大學,2012.
[7]李如龍.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J].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8]邵敬敏.漢語語法的立體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9]查中林.四川方言詞語之語素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8.
[10]羅竹風. 漢語大詞典[M].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