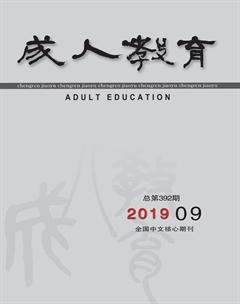大規模協作支持的在線學習集體智慧生成路徑研究
祁晨詩 王帆 郝祥軍



【摘 要】在線學習環境中,大規模群體通過深度交互,充分交織個體智慧,能生成具有重要價值的集體智慧。然而,在大規模協作實際運行中,群體協作和群體知識建構效果不佳,導致個體智慧孤立,集體智慧形成的基礎薄弱。構建在線學習集體智慧生成路徑(OCIG):以個體智慧為起點,在媒介供給、組織策略和社交互動的支持下,能實現個體參與群體協作,最終生成集體智慧。并依此設計大規模協作方案,進行實踐與分析,結果表明:適切的媒介功能,為集體智慧生成提供技術保障;多樣的組織結構,轉變集體智慧生成方向;提供逐級的互動支架,能夠提升集體智慧層次。
【關鍵詞】大規模協作;集體智慧;在線學習;群體交互
【中圖分類號】G72;G4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794(2019)09-0022-10
一、問題的提出
互聯網+時代,在線學習環境為學習者創造了靈活的交互方式、廣闊的互動空間和更多的交流機會。[1]在學習科學與技術實踐的推動下,研究者將關注點逐漸從支持設備、呈現形式轉向了在線交互質量和學習成效。[2]在線教育開拓者琳達·哈拉西姆(Linda Harasim)強調協作的重要性,提出在線協作方式能夠充分激發學習者的創新思維,是提高在線學習質量和效果的根本保證。[3]專家學者利用大規模協作學習方式開展各種實踐探究,如卡洛琳·佩恩斯坦·羅澤(Carolyn Penstein Rose)利用整合會話分析與文本挖掘技術優化大規模協作學習的過程與結果,但在在線學習實際運行過程中,學習者協作能力缺失,導致同伴間無法開展良好協作。[4]楊芳利用協作學習模式開展大規模在線英語教學的效果提升研究,實踐中發現,學習者在進行協作交互過程中,存在互動深度和廣度不足,知識建構水平較低等情況。[5]李海龍等人通過對大規模在線學習變形體的新探索,深刻認識到保障學習者的協作體驗感和提供個性化支持服務,對于提升在線協作內驅力的重要性。[6]
大規模群體在網絡環境中深度交互,使得個體智慧充分交織,協作產生解決實際問題的創新性方案,生成具有重要價值的集體智慧。[7]然而,學習者協作積極性不高、協作能力不強、建構水平低下等一系列問題導致在線學習中個體智慧彼此孤立,集體智慧形成基礎薄弱。[8—9]群體協作成效與集體智慧生成結果相輔相成,生成與應用高水平的集體智慧能夠有效支持學習活動,優化協作過程,提升協作質量。[10]因此,探究大規模協作中高質量的集體智慧生成路徑,對于提升在線活動的實施效果,促進學習者生成集體智慧有重要的意義,也是本研究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二、概念界定
(一)大規模協作
“大規模”這一概念最初起源于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2013年,布雷默(Bremer)依據鄧巴(Dunbar)的研究,[11—12]從個體的社會網絡負荷考慮,將超過150人的學習群體定義為“大規模”。他指出,當學習者超過這個數值時,由于人類的智力水平和認知能力有限,群體之間的關系密度會被稀釋,人際網絡結構變得不穩定,這將導致有效性溝通減少。
克雷斯(Cress)等人曾明確指出,大規模協作是大量人員為完成同一項目所進行的集體活動,通常在互聯網上借助社交軟件和協作工具(例如wiki技術)進行,實現分散式創新。[13]泰普斯科特(Tapscott)和威廉姆斯(William)等人將大規模協作概括為一種大范圍內大型網站用戶的群體性參與(活動)模式。[14]國內學者范哲、吳克文等人提出,大規模協作是基于互聯網環境,將擁有不同背景的分散且獨立的個體,通過特定組織或個人召集,依靠互聯網平臺和社會化軟件組成網絡團隊,或顯性或隱性地通過組織方式,形成高質量的團隊作品。[15]
文獻中對大規模協作雖無統一概念的界定,但存在一些共性的觀點:“人員異質”“數字工具支持”“高質量協作成果。”綜上,本研究認為大規模協作是一種計算機支持下的持續的群體性活動模式,具有多方面異質性的學習者,在統一目標的指引下深度交互,以去中心化的組織形式,進行多人靈活而高效的交流,共同參與活動,發揮集體效應,共同完成協作任務。
(二)集體智慧
集體智慧最早被界定為一種解決問題的能力,如1964年韋克斯勒(Wechsler)指出集體智慧是個體在穩定的組織結構中,在明確目標的指引下進行深入思考,產生高效處理問題的能力。[16]但在技術與教育不斷融合發展的推動下,社會互動成為生成集體智慧的一種有效手段,這一點在波爾(Por)和阿拉克(Alag)的研究中得到體現,[17—18]他們認為個體聚集通過社會性交互能夠獲取群體性行為,幫助學習同伴高效解決問題并產生集體智慧。大規模群體協作的實現必然少不了工具的支持,于是傅韋達(Wai-Tat Fu)從工具的輔助性出發,闡述了集體智慧是在工具的支持下由個體智慧經過整合與分化而來的。[19]國內研究者也在關注集體智慧,如甘永成和祝智庭提出,通過系統的有效組織促進個體間長期的互動、合作和知識建構,運用個體智慧解決實際問題,達到集體智慧的凝聚和升華;[20]段金菊等人強調集體智慧是個體通過良好的活動組織促進個體與知識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產生聯結,實現知識共享與創造,逐漸轉識成智。[21]
綜合上述觀點,研究發現“工具支持”“群體組織”和“社交互動”是生成集體智慧重要的過程性條件。本研究將集體智慧總結為:個體為完成共同的目標而群聚在一起,借助媒介工具,在組織管理下以協作形式進行深度交互,共享個人的知識、行為、思想、經驗等,并將其轉化為解決復雜實際問題的創新能力。
三、集體智慧生成路徑設計
瓦西利斯(Vassilios)在他的研究中提出,基于用戶生成的集體智慧分為五個層面,分別為個體層、媒介層、組織層、社交層和集體層。[22]重新思考這五個層面之間的相互關系,有助于更好地構建集體智慧的生成路徑。組成群體最基本的單位是個體,個體層的智慧是生成集體智慧的基礎,個體帶動集體,實現群體層智慧的凝聚與創新,最終生成集體智慧。在這個過程中,媒介技術不斷發展,滿足在線學習的各種需求,起到支撐學習活動的作用。同時,不同的組織形態對群體社交互動有重要的影響,良好的組織策略能夠提升群體凝聚力,形成高水平的社交互動,進而生成高質量的集體智慧。由此可以總結出,在集體智慧的五個層面中,媒介、組織和社交為三大支撐條件,個體和集體是集體智慧生成的兩大表征。在三大支撐條件的作用下,個體和群體相互配合,生成集體智慧。在此基礎上,鄭惠先(Heisawn Jeong)等人進一步研究,他們認為大規模協作學習中交互水平的最低層次為個體參與,最高層次為群體協作。[23]個體參與,是聚集學習者開展大規模協作活動的起點,也是學習者適應大規模協作的重要過程。在參與階段,往往以難度較低、要求不嚴的學習活動吸引學習者,調動參與積極性。以個體參與促成群體協作,使群體性學習在協作中得以進一步深化,整個過程中,學習者按照共同的目標開展活動,共享協作并且承擔著集體責任,使個體智慧得以充分交織。
綜合上述研究,本文構建了大規模協作支持的在線學習集體智慧生成路徑圖(Online Learning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Generation,簡稱OCIG),如下頁圖1所示。
OCIG中右側的滑輪結構表示學習者的行為,在媒介供給、組織策略和社交互動的相互配合下,以最小的作用力實現個體參與、促成群體協作,使個體智慧提升為集體智慧,這三者是生成集體智慧的重要條件。
媒介供給:作為定滑輪,媒介為群體協作水平的提升提供支點和保障作用,為集體智慧的生成在學習性、社交性和工具性等方面提供技術支持。[24]
組織策略:作為動滑輪之一,在生成集體智慧的過程中,發揮著引導作用。組織策略是參與者以及群體活動的設計者為提高群體參與度,加強群體凝聚力,增強建構效果而使用的方法與技巧。
社交互動:作為另一個動滑輪,在生成集體智慧的過程中,起到提升知識建構質量的重要作用。個體通過社交互動,從對學習內容的自我建構轉向群體建構。社交互動的水平體現了學習者對知識內容不同程度的理解與思考,推動著集體智慧的生成,提升著群體知識建構的質量。
左側虛線表示大規模協作支持的在線學習過程與結果,個體智慧是產生集體智慧的基礎,一切活動以個體認知為出發點。[25]集體智慧是群體大規模在線學習最終、最理想的結果,體現著群體協作的實際效用。
由媒介供給、組織策略和社交互動構成的滑輪組,在實現個體參與向群體協作發展,個體智慧向集體智慧生成過程中,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引導和提升作用,以更好地生成大規模在線學習效果,提高在線學習質量。
四、大規模協作方案的設計與實施
(一)大規模協作方案的設計理念
1.選擇合適的媒介工具
從協作學習理論視角對大量計算機支持的協作學習實踐進行分析,發現媒介工具在支持協作學習過程中,主要起到吸引學習者參與、促進溝通、共享資源、細化任務、匿名討論、記錄學習過程和輔助同儕反饋等7大媒介功能的作用。[26]因此,在進行媒介選擇時,要對媒介工具進行功能分析,考慮媒介在與學習者交互過程中達到的實際功用。同時,媒介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界面設計的美觀性也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
2.設計靈活的組織策略
在大規模群體中,往往難以實現對所有學習者的統一管理,而且自上而下的他組織管理方式有其存在的固有弊端,群體內部在活動中自發顯現的核心人物,無論是在內容貢獻程度還是號召力方面,都有重要的引領作用,[27]如若不加以利用,反而浪費了這一有利資源。在群體自發產生的核心人物的基礎上,對這一群體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鼓勵實施群體內部的自組織策略,擴大他們的影響力,充分發揮輻射引領作用。
3.搭建有效的互動支架
大規模在線學習中,往往討論較為自由,學習者沒有明確的交互方向,呈現邊緣化參與,缺乏互動積極性、群體思維發散而難以凝聚和升華等,可使學習者圍繞互動支架,依據學習內容,進行話題討論。這不僅為學習者提供話題討論的契機,促進學習者不斷深入思考,也為個人自主發帖提供參考依據。問題支架的情境性、系統性與啟發性不僅提高社交質量,同時也促進個人知識的全面建構與體系化發展。[28]
(二)大規模協作方案的實施
1.實施對象
本研究以某市教師培訓中近4.3萬學習者作為大規模協作方案的實施對象,通過前期調查顯示,學習者男女比例3∶4,年齡在30—50歲之間最多,大專,本碩博學歷均有一定比例,分布于該市各地。從學習者的職業特征來看,學習者教授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和中職這五個學段,在語文、數學、英語等十多門學科領域中各有專長。該群體在人員構成方面,滿足人員數量、學習者異質性和參與獨立性這三方面的要求,符合大規模特征。
2.實施過程
大規模協作實施過程主要包括視頻學習引發個體廣泛參與、角色分化顯現核心人物、搭建互動支架聚合個體智慧、自主發帖深化群體協作四個環節,而媒介供給、組織策略以及社交互動作為三大重要支持條件,貫穿活動實施的始終,具體實施方案見圖2。
引發參與。大規模在線學習的起點是學習者有組織地共同參與學習活動。利用在線學習視頻作為基礎資源引發學習者參與其中。鼓勵學習者在觀看視頻的同時,在視頻下方針對學習內容進行文字的質性評論和量化評分,以激發學習者參與學習活動的積極性。
分化協調。為了最大化學習者自主協調成果,充分發揮成員的核心作用,本研究定位前幾期培訓中,活躍度高、影響力相對較大、參與質量較高的學習者,組成本期的200人核心學習者群體,以他們為自組織領袖,組織開展在線學習。核心學習者不僅是學習的主體,也是群體在線學習的主要負責人,有具體的發帖和回帖指標要求,負責散發社交魅力,組織和引導在線討論的方向,形成群體參與動力。
群體聚合。為了更好地引導在線交流,提升在線學習的質量,在線課程的運行者在每一主題下搭建包括理解、應用、分析、評價和創造這五大層次的互動支架。聚合成果是個體在互動支架下評論回復的總和,學習者通過支架式問題將視頻學習的零散內容進行思考與表達,為群體建構和智慧生成奠定基礎。
深化協作。深化協作實質上是促進個體之間的交互,深化群體內部的知識建構。因此,在課程運行中,鼓勵學習者能夠以內容為核心,圍繞具體的話題內容,形成良好的互動關系。學習者可以針對自己困惑的問題或感興趣的內容自己組織討論或選擇他人建立的話題加入其中,與其他學習者展開學習與討論。在交互中促進自己的思考,優化個體知識,總結學習心得,形成學習報告,用以解決復雜的實際問題,達到深化協作學習的目標。
五、數據分析與結果描述
(一)媒介供給分析
1.媒介使用功能分析
本研究選用“江蘇教師教育網”作為在線學習平臺,力求為在線學習生成集體智慧提供技術的基礎性保障。在培訓結束后,對學習者的平臺使用感受進行調查,有不少學習者提及,媒介功能為在線協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如:
“我在網上設計了投票類的討論問題,我發現這個功能非常好,大家對于投票的參與熱情遠遠高于直接發起話題討論,通過統計投票的結果,也能很好地收集討論內容。”
“平臺能夠將好的帖子置頂,節省了我們從大量的帖子中篩選精華帖的時間和精力,在優質的話題內容下討論,可以看到更多的好的觀點,提高自己的認識、加深自己的理解。”
“以前的教師培訓,只能在電腦端看視頻參與討論,現在的微信端十分方便了。在電腦端看視頻,手機微信端口進行在線討論,方便快捷,實現了無縫學習。贊!”
因此,結合“江蘇教師教育網”的實際媒介功能,總結分析了本次在線學習受到一致歡迎的媒介功能,如圖3所示,體現出媒介的使用能夠誘發學習者參與、促進溝通、促進資源共享、檢測學習過程以及促進同儕反饋等優勢功能。
(1)PC+微信端口同步使用。學習者無需下載新的軟件,微信端即點即用,將在線學習與日常社交融為一體,支持學習者無縫學習,更加方便快捷地記錄個體智慧。
(2)視頻學習與論壇討論一體化。學習者無需轉戰多個平臺,相比往期在江蘇教師教育網觀看學習視頻后,前往百度貼吧進行討論,現有的網絡平臺更加具有統整性,支持個體智慧的持續性傳播。
(3)論壇精華帖置頂功能。方便標記優質討論帖,排序置頂,醒目提示,吸引更多學習者參與高質量的學習與討論,凝聚高水平的集體智慧。
(4)添加標簽功能。學習者進行討論帖主題歸類,細化討論內容,促進不同類別話題之間的橫向比較和同類話題的縱向提升,使得發散的個體智慧得以收斂。
(5)投票功能。江蘇教師教育網在功能上,不僅支持文本、圖片、視頻、超鏈接、附件等形式的內容上傳,還提供投票功能,觸發更多學習者查看發帖,提升學習者的積極性,推動集體智慧的創新性發展。
2.媒介使用感受分析
本研究借助黃國幀教授設計的學習系統滿意度量表,[29]調查學習者對在線學習選擇“江蘇教師教育網”的滿意度。問卷由7道量表題目組成,從非常不同意(1分)到非常同意(5分)依次遞加,核算每個學習者的平均分值,并將其結果以圖的形式呈現出來,見下圖4。
平臺使用滿意度各個題項均值都在4分以上,Q1得分最高,學習者強烈認為目前使用媒介平臺較以往而言,更為方便。從Q4中可以看出,平臺得到了學習者的一致認可。7個題中,相對分數較低的是Q3,表明了“江蘇教師教育網”在引導學習者轉變思維方式,重塑認知結構方面,功能性還不夠突出,在以后媒介的選擇或是媒介設計時,不僅要注重媒介的載體功能,還要關注媒介作為認知工具起到優化學習者認知、調整學習者思維方式的輔助作用。Q5、Q6、Q7三題表明學習者愿意將“江蘇教師教育網”進行推廣使用,體現了對媒介功能的肯定。簡潔的界面設計、公開的交流環境、無縫的溝通交流,能夠讓學習者在交互中發現更多新的問題,借助平臺優勢對學習內容進一步加工與思考,能觸發個體智慧的發散、收斂,集體智慧的凝聚與升華。
(二)組織策略分析
1.他組織分析
(1)他組織群體考核數據分析。以大規模協作方式開展在線學習,用統一且標準化的考核方式能夠實現對所有參與者學習情況的考察。通過設置不同類型的題目,了解學習者對知識的記憶、理解、運用、分析等方面的能力,較為公平地反映學習者的個體知識水平。
針對某地區第五期大型教師在線培訓活動進行設計和研究,幾期的人員相對固定,綜合客觀題和主觀題的考核結果,本期的整體合格率為98.12%,說明學習者具備扎實的理論基礎和較為突出的個體智慧。將200名核心學習者的在線考核成績與近4萬普通學習者進行對比,結果如表1所示。從客觀題的均分和主觀題合格率來看,表明核心人物整體在知識掌握方面優于大規模群體,同樣也驗證了前期對核心人物的篩選工作是有效且正確的,核心學習者的確在群體中起到了模范作用,個體認知表現較為突出。
(2)他組織群體網絡屬性分析。搭建互動支架是課程設計者進行他組織的重要策略,利用UCINET軟件分析群體屬性,如表2所示。在他組織下,學習者僅圍繞某一個互動支架所形成的網絡規模相當可觀,最高引發1936人參與,最差引發683人參與。“安全教育”創造性支架的關系達到2 024,表明學習者之間交互的帖子達到2 024條,弱一些的“理論之光”應用性支架也產生了709條交互帖子。結合網絡規模來看,他組織策略建立的群體網絡結構是龐大的。
他組織策略,自上而下發布任務,引發了大規模學習者廣泛參與,學習者的學習行為從視頻學習轉向了支架互動。網絡密度用以刻畫節點之間相互聯系的密集程度,受網絡規模影響,一般而言,網絡規模越大,網絡密度就越大。從兩個互動支架的網絡密度來看,密度0.015,0.024均屬于較低水平,說明群體中成員之間的聯系存在偏重現象,大多數學習者僅回復互動支架發布者的問題,而學習者之間相互產生聯系較少,群體成員之間的聯系較為疏遠,互動不夠積極,群體互動氛圍不夠活躍。網絡平均度最優達到1.045,最差達到1.034,表明群體中每個學習者之間平均建立起1.045、1.034個連接,與不足2個學習者產生聯系,除去組織者之外,成員之間的交互頻率不高。
2.自組織分析
(1)自組織群體考核數據分析。為更好分析兩類學習者在自組織策略下個體認知的發展情況,對核心學習者和普通學習者進行課程學習前后的對比測試,利用SPSS對兩組前后測試進行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中可以看出,核心學習者的前后測平均分都高于普通學習者,說明核心學習者的個體知識掌握和知識運用程度要優于普通學習者。核心學習者后測成績提高并不顯著,而普通學習者的后測成績則有明顯提升,說明普通學習者的學習效果更加突出,經過培訓后,個體知識發展有較大的變化,而核心學習者本身具有扎實的知識和豐富的知識轉化經驗,在線學習提升空間較小,因此學習效果不明顯。在自組織策略下,無論是核心學習者還是普通學習者,作為個體智慧的重要組成部分——個體認知,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為形成高質量的交互內容,生成高水平的集體智慧,奠定牢固的基礎。
(2)自組織群體網絡屬性分析。學習者自主建立新帖是自組織的重要策略。分析自組織下群體屬性,能夠對自組織水平進行整體把握,如表4是自組織群體屬性分析表。
從表中可以看出,核心學習者建立的主題帖所形成的網絡規模比普通學習者主題帖的規模要大,所形成的關系數也較普通學習者多。核心學習者498個節點數產生了2 572條關系,也就是共有498名學習者參與了這條帖子的討論,并產生了2 572條交互帖子;普通學習者的帖子共有175名學習者參與,形成了481條帖子。核心學習者建帖所形成的網絡密度為0.373,普通學習者建帖網絡密度為0.149,都遠高于他組織下學習者所形成的網絡密度,說明學習者自發建立的主題帖中,成員之間的互動關系更加緊密。核心學習者建立的帖子結構中,平均度為5.73,說明群體中的學習者與5.73個節點產生聯系,平均一個人約與6名學習者產生交互,這一指標優于普通學習者建帖的2.48個節點數,這與他組織網絡結構相比,均有所提高。
核心學習者開展自組織活動,以內容和興趣為出發點自主建帖,自中而下發散集體智慧,帶動普通學習者發布草根式話題,自下而上實現集體智慧的收斂。集體智慧的形成動力來自于學習者之間積極的互動,互動程度和互動方向影響著群體建構和集體智慧的生成水平。自組織策略下,群體交互程度越高,交互越多向,學習者之間的關系就越緊密,知識建構和生成集體智慧的效率和水平就越高。
(三)社交互動分析
1.社交互動過程分析
不同深度的社交互動水平,反映了學習者個體和集體智慧的不同層次。在論壇討論區將9個主題的45個互動支架問題按照對學習者認知要求由低到高依次拋出,學習者通過互動支架,從視頻學習過渡到真實問題的理性思考中。依照Gunawardena等人研究的知識建構內容交互編碼(①內容共享,②探索發現,③協同構建,④觀點加工,⑤知識創新),[30]對六周(即六個學習周)互動支架中學習者的討論內容進行編碼和計算平均值處理,結果如圖5所示。
從圖中可以看出,隨著在線學習活動不斷推進,無論是普通學習者還是核心學習者,在線社交水平均有所提高。從時間上來看,由于前三周分階段拋出理解應用型、分析評價型以及創造型互動支架,因此前四周互動深度變化較大,到第五、六周趨于穩定,尤其是普通學習者的變化幅度更為明顯。普通學習者從學習開始時,在線互動停留在內容分享和探索發現這兩個較低層次上,而后在核心學習者的引領下,討論深度不斷增加,逐步過渡到意義協商、觀點加工水平,實現在線學習效果的較大突破和集體智慧層次的較大提升。核心學習者作為在線學習的核心引領式人物,在線討論保持著較高的質量水平,在與其他學習者的相互交流和促進中,討論深度逐漸向觀點加工和達成共識的高層次方向發展,保持核心人物集體智慧的較高水準。
2.社交互動結果分析
在六周互動支架的幫助下,學習者能夠對學習內容有更全面的認識和更深入的思考。在個體智慧持續提升的基礎上,集體智慧應運而生。群體交互能集眾人之長解決現實復雜的問題,這是搭建在線平臺進行交流的主要目的。眾多學習者能夠充分利用在線學習交流的契機,集眾人智慧,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在收集了學習者提交的學習總結后發現,許多學習者能夠很好地利用在線平臺,通過群體交互,集眾人智慧解決自己遇到的復雜的實際問題,由理論向實踐發展,轉識成智。例如,泰州市姜堰區第四中學的石建華老師將培育站的研修主題“農村初中數學課堂的研究”作為話題拋到論壇中,得到了114條同是一線教師的學習者評論,為他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廣泛的素材。泰州市城東中心小學的陳娟老師、靖江市實驗學校的賈平老師等將擔任班主任期間面臨的問題與其他老師分享,獲得了350條寶貴經驗的分享與實踐指導。
據統計,除了預設九個主題的互動支架,學習者通過自主發帖,自發形成了如圖6(部分展示)所示的2 244條新的話題。這些話題中涵蓋了當前的熱點話題、前沿理論和實踐難題,其中與他們日常教學工作相關的實踐類問題探討占74.83%,這表明學習者能夠從這次線上培訓和集體探討中收獲實實在在的內容,而不僅是為了完成考核任務。論壇中所有的討論內容是集體智慧的重要呈現,而學習者自我總結和自我反思的內容是集體智慧內化作用于個人的結果,對學習者個人而言更有價值,因此,在集體智慧創生的過程中,大規模協作促進了個體和群體的共同成長與提高。
六、研究結論
(一)適切的媒介功能,提供集體智慧生成保障
在本次在線學習中,學習者已掌握了基本的媒介操作技能,并不存在操作難度或認知困難,學習者對媒介的功能普遍較為滿意,并愿意將其推廣使用。研究所選用的媒介“江蘇教師教育網”,最大特色在于界面的簡潔明了,功能的適切供給,如投票、置頂、標簽等功能配合著PC和手機端的使用,極大地方便了學習者的使用,沒有冗余的信息和復雜的認知負荷。適切的媒介功能,如共享資源、引發參與、促進溝通、細化任務、檢測學習過程以及同儕反饋等為生成集體智慧創造了便利的條件。
媒介作為認知工具,學習者除了關注其社交性和工具性兩方面,也對媒介的學習性保障產生了新的期待。以后在線課程設計者進行媒介設計和選擇的時候,還要關注媒介輔助學習者認知,為轉變學習者思維方式、優化認知結構提供更多的支持。
(二)多樣的組織結構,引導集體智慧生成方向
本研究以他組織形式自上而下發布學習任務,保證學習者基本的參與行為;以自組織形式進行自下而上的草根式話題討論,確保話題內容的實用性和價值性。在經過幾期的在線學習后,學習者的加工、存儲和提取信息等綜合能力得到持續提高,認知水平得到不斷發展。在線課程的學習內容,往往是由課程設計者結合課程大綱和教學目標進行設計和確定的。從他組織角度出發設計,自上而下開展活動,往往能夠聚集大量學習者參與學習,但可能存在教學理論性重于實踐指導性,或理論與實踐脫離,學習者學習興趣低下等情況。
多樣化的組織結構,能夠引導集體智慧多向生成。在專家學者制定的固定話題基礎上,核心學習者以點帶面,發揮輻射引領作用,帶動大規模學習者,引發學習者之間多向溝通和緊密互動。以自組織形式自主建帖,自下而上產生草根匯聚式的知識內容,更能滿足學習者的實際學習需求。在自組織和他組織的雙重作用下,集體智慧得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多向生成。
(三)逐級的互動支架,提升集體智慧生成層次
視頻學習資源是大規模在線學習的主要學習內容,向學習者呈現了靜態的知識內容。在沒有具體目標和具體要求的情況下,學習者自主學習和獨立思考發布的內容層次較低,體現了個體思維的局限性。當提供了不同層級的互動支架后,學習者圍繞互動支架進行內容的思考和回復,隨著互動支架層級的不斷提高,學習者被推動著不斷深入思考。
個體通過觀看學習視頻進行智慧的發散,在回答互動支架問題中實現集體智慧的收斂,通過核心學習者的話題引導凝聚集體智慧,再到通過自主建帖討論創新生成集體智慧,這個過程中,學習者將視頻中有限的靜態知識轉變為個體和群體的動態生成的智慧,理論指導實踐,解決實際的復雜問題。互動支架幫助學習者由簡單的概念理解提高到策略方法的提出,由內容陳述提高到觀點創新,整體社交水平也在不斷提高,進一步提升了集體智慧的層次。
【參考文獻】
[1]王志軍.遠程教育中“教學交互”本質及相關概念再辨析[J].電化教育研究,2016(4):36—41.
[2]張思,劉清堂,雷詩捷,王亞如.網絡學習空間中學習者學習投入的研究:網絡學習行為的大數據分析[J].中國電化教育,2017(4):24—30.
[3]琳達·哈拉西姆,肖俊洪.協作學習理論與實踐:在線教育質量的根本保證[J].中國遠程教育,2015(8):5—16+79.
[4]王阿習,王旭.整合會話分析與文本挖掘技術來評價協作學習:訪談卡耐基梅隆大學著名教授卡洛琳·佩恩斯坦·羅澤[J].現代遠程教育研究,2017(6):3—10.
[5]楊芳,魏興,張文霞.MOOC edx討論區的協作學習模式探析:以英語會話技巧的教學實踐為例[J].外語電化教學,2015(6):60—68.
[6]李海龍,李新磊.“后MOOC”時代基于分布翻轉的SPOC體驗式學習探討[J].電化教育研究,2015(11):44—50.
[7]張劍平,胡玥,夏文菁.集體智慧視野下的非正式學習及其環境模型構建[J].遠程教育雜志,2016(6):3—10.
[8]李海峰,王煒.社會系統理論視域下的在線學習共同體構建[J].中國電化教育,2018(6):82—90.
[9]黃建鋒.基于“互聯網+”的碎片化學習策略研究:從“碎片”到“整體”的嬗變[J].電化教育研究,2017(8):80—84.
[10]郁曉華,江紹祥.在線教與學集體智慧的有效利用:學習分析的視角與架構[J].開放教育研究,2016(3):98—106.
[11]Bremer C, White D.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Categorization and analysis of participant behavior using the example of OPCOs 2011 and 2012.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am Main, 2013[C].Germany: TUD Press, 2013.
[12]Dunbar R I M. Coevolution of neocortical size, group size and language in humans[J].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993(4):681—694.
[13]Cress U, Jeong H, Moskaliuk J. Mass Collaboration and Education[M].Cham: Springer, 2016.
[14]唐·泰普斯科特,安東尼·D.威廉姆斯.維基經濟學:大規模協作如何改變一切[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
[15]范哲,吳克文,朱慶華,等.互聯網群體協作概念、應用與適用理論探討[J].情報理論與實踐,2013(6):13—20.
[16]Wechsler D.Die messung der intellignez Erwachsener[M].Bern-Stuttgart: Hubrt, 1964.
[17]Por G. The quest for collective intelligence[M].San Francisco, CA: New Leaders Press, 1995.
[18]Alag S.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 action[M].New York: Manning, 2009.
[19]Fu W T. From distributed cognition to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Supporting cognitive search to facilitate online massive collaboration[M].Cham: Springer,2016.
[20]甘永成,祝智庭.虛擬學習社區知識建構和集體智慧發展的學習框架[J].中國電化教育,2006(5):27—32.
[21]段金菊,余勝泉.基于社會性知識網絡的學習模型構建[J].現代遠程教育研究,2016(4):91—102.
[22]Solachidis V, et al.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generation from user contributed content[C].Berlin: Springer, 2009.
[23]Jeong H, et al. Joint interactions in large online knowledge communities: the A3C framework[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2017(2):133—151.
[24][26]Jeong H, Hmelosilver C E. Seven Affordances of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How to suppor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How can technologies help?[J].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16(2):1—19.
[25]Richardson M J, Pasupathi M. A handbook of wisdom: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7]Cohen A, Shimony U, Nachmias R, et al. Active learners characterization in MOOC forums and their generated knowledge[J].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9(1):177—198.
[28]郝祥軍,王帆,汪云華.問題支架促進在線知識交互的途徑假設與驗證[J].中國遠程教育,2019(3):34—42.
[29]Chu H C, Hwang G J, Tsai C C. A knowledge engineering approach to developing mindtools for context-aware ubiquitous learning[J].Computers & Education, 2010(1):289—297.
[30]Gunawardena C N, Lowe C A, Anderson T. Analysis of a global online debat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action analysis model for examining social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computer conferencing[J].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1997(4):397—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