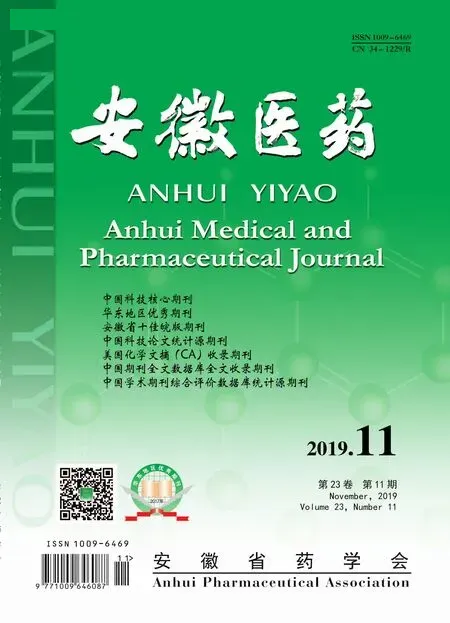Caprini與Autar血栓風險評估模型在血管外科篩選靜脈血栓栓塞癥病人中的意義
劉純,朱松波,周大勇,尚爾寧
靜脈血栓栓塞癥(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包括深靜脈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和肺栓塞(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PE),作為血栓性疾病,是目前院內病人較常見的死亡原因之一。有研究顯示,在血管疾病中VTE的發生率僅次于急性冠脈綜合征和腦卒中,無論是手術還是非手術病人,40%~60%的住院病人存在VTE風險。而DVT和PE發生后,1個月內病死率分別達到6%和10%[1]。因此在臨床上高效便捷地評估VTE風險,為臨床及時采取預防措施提供依據顯得尤為重要。目前國內外常用風險評估模型包括Autar評估、Caprini評估、JFK評估表、Padua評分表、RAP評分法等[2]。無論是哪種VTE風險模型,一般均為提出風險項目并賦予分值,根據病人實際情況進行評分,按總分高低以劃分病人風險等級[3]。由于目前國內缺乏統一系統的評估,本研究旨在比較Caprini與Autar血栓風險評估模型在血管外科篩選VTE病人中的意義,探討如何指導臨床采取實時的預防以降低VTE發生風險。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2017年1—12月南京醫科大學附屬蘇州醫院血管外科收治的VTE病人61例為觀察組,其中男24例,女37例,年齡>40歲有53例,體質指數(BMI)≥25 kg/m2有30例。髂股靜脈血栓形成35例,上肢靜脈血栓形成2例,下肢深靜脈血栓性形成14例,肺栓塞10例,納入標準:臨床癥狀和輔助檢查均符合國家制定的VTE診斷標準,其中均通過嚴格的影像學確診[4]。排除標準:病歷資料不全、肝腎功能異常等。選取同時期未診斷為VTE的病人155例作為對照組,其中男72例,女83例,年齡>40歲有141例,體質指數(BMI)≥25 kg/m2有66例。兩組病人在年齡、性別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所有病人其近親屬均知情同意,本研究符合《世界醫學協會赫爾辛基宣言》相關要求。
1.2 風險評估模型Autar量表由英國德蒙特福德大學Autar教授于1996年研發并推出[5]。此量表主要包含7個風險因素,分別為年齡、活動能力、BMI、特殊危險因素、創傷、手術、高風險疾病。每個風險因素賦值1~7分,根據總分分為4個等級,即無風險、低危、中危和高危。Caprini風險評估模型由美國西北大學教授Caprini等于1991年發布。該模型含有40項條目,包括年齡、BMI、腫瘤史、腦梗史等,各項賦值1、2、3、5分不等。根據總分分為4個等級,低危,中危,高危,極高危[6]。
1.3 評分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顧性病例對照分析,對入組的216例病人分別進行Caprini和Autar評分,從累積風險以及風險等級兩個層面比較評分模型對觀察組和對照組的區分能力,并針對風險等級分析兩種評估模型對相同病人風險等級劃分的準確性和靈敏性。為統一兩個評分的分層級別,按照VTE發生率的高低,將Caprini評分和Autar評分分別劃分為低、中、高危,見表1。

表1 兩種風險評分風險等級劃分[7]
1.4 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 22.0軟件。正態分布資料以±s描述,偏態分布資料以中位數和四分位數范圍M(P25,P75)表示。觀察組和對照組的累積風險分數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風險評分等級資料采用秩和檢驗。采用ROC曲線評價風險評估模型的靈敏度和特異度,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致性分析(1)對兩組病人進行血栓風險評分,Caprini得分采用t檢驗,Autar得分采用t’檢驗。兩種模型在兩組間的累積風險得分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兩種評分模型均可以將兩組病人進行有效的區分。結果見表2,3。

表2 兩組資料統計

表3 累積風險得分t檢驗
(2)采用Mann-WhitneyU檢驗和Wilcoxon符號秩和檢驗對評分的等級資料進行進一步統計學比較。Mann-WhitneyU檢驗結果顯示兩種風險評估模型在兩組間的風險等級資料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可認為兩種模型在觀察組的評分等級高于對照組,見表4。而Wilcoxon符號秩和檢驗結果顯示,Caprini模型較Autar模型能將更多的觀察組病人和存在高危因素的對照組病人劃分到高危人群,結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4 風險等級資料Mann-Whitney U檢驗

表5 風險等級資料Wilcoxon符號秩和檢驗
2.2 ROC曲線分析通過ROC曲線描述評估模型的評價效能,分析兩種模型預測VTE發生情況的靈敏度與特異性。結果顯示Caprini模型的曲線下面積明顯大于Autar模型(P<0.01),說明Caprini模型具有較高的靈敏度和特異性。見表6,圖1。

表6 兩種評分模型曲線下面積

圖1 兩種評分模型ROC曲線
3 討論
VTE的形成與多方面因素有關,Virchow三角學說是血栓形成的重要理論基礎,該學說認為血栓形成是血管壁損傷、血流動力學改變和血液粘滯度增加相互作用的最終結果[8]。由于許多因素都可以影響上述條件,評估VTE風險時具有一定難度。Caprini等通過大量實驗數據、臨床觀察和文獻查詢,針對多項風險因素研制的Caprini評分量表,已發展成為目前較為完善的血栓風險評估體系。
自我國引進Caprin模型后,許多醫務工作者針對該模型進行了驗證與評價。雖然關于該模型在血管外科病人中的應用較少,但在其它科室的病人中顯示了其有效性。婁英華和沈怡[9]以婦科159例病人為研究對象,比較了惡性疾病組與良性疾病組Caprini累積風險得分,結果發現惡性疾病組評分(7.8±2.6)分顯著高于良性疾病組(4.1±2.2)分,P<0.001。作者認為Caprini量表涵蓋了常見高危因素,因而可以有效識別高危病人。而周海霞等[10]采用病例對照研究,在內科病人中選取218例VTE病人和394例非VTE病人,對兩組進行了Caprini評分,VTE組評分顯著高于對照組(P=0.000)。該研究認為Caprini風險評估模型對內科住院病人的風險評估是準確有效的。此外還有針對ICU病人[11]、老年重癥肺炎病人等[12]諸多研究,均認為Caprini評分是安全有效的。
本研究選擇目前尚無文獻研究的血管外科病人作為研究對象,針對具有較高發生率與死亡率的靜脈血栓栓塞癥,進行了VTE風險評估模型的對比研究。由于不同類型的病人所具備的危險因素不同,因此為不同疾病的病人選擇個體化的風險評估模型顯得尤為重要。我院血管外科目前主要采用Autar模型對住院病人進行栓塞風險評估。而隨著Caprini模型在國內外的逐步推廣,特別是應用于外科領域,因此本研究主要考察這兩種模型在對不同風險等級病人中篩選方面的優劣性,為臨床選擇血栓風險評估模型提供參考。與Autar模型相比較,Caprini模型的優勢主要體現在:(1)Caprini模型的評分量表中涉及DVT的危險因素更為全面,能夠使醫護人員更及時的發現高危因素,有利于第一時間采取預防措施。如有些項目詳細到病人1個月內的疾病狀況,對于手術的類型也進行了細分等;(2)通過本研究統計分析及繪制ROC曲線,證明了Caprini模型較Autar模型對陽性預測和陰性預測均具有更高的靈敏度和特異性,同時Caprini模型能夠將更多的存在高危因素的病人劃分到高危人群,結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3)國內外已有大樣本研究也證實了Caprini模型可有效的預測靜脈血栓栓塞。綜上所述,Caprini模型較Autar模型更適合應用于臨床,對于血管外科篩選VTE病人的應用值得推廣。
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1)主要采用回顧性研究,由于個別病人信息資料缺失而可能導致結果存在偏倚,因此有待多中心、大樣本的前瞻性隊列研究佐證本研究結果;(2)對照組中大部分為靜脈曲張的病人。然而靜脈曲張本身也是VTE高危因素之一,因此該兩種評估模型在低危病人中的評價效果需進一步驗證。另外,由于國內外人群特點不同,飲食習慣、疾病特點等差異,因此在借鑒國外評估模型的基礎上,制定符合我國人群特點的風險評估模型也是非常必要的。已有研究顯示高血壓、糖尿病、吸煙等也是VTE發生的危險因素[13-14],而且我國是吸煙大國,糖尿病、高血壓發病率也居高不下,但是這些因素在國外的評估模型中卻很少體現。面對這一現象,對于我們醫務工作者來說,需積極研究更加符合我國病人的風險評估模型。
(收稿通知:2018-09-06,修回日期:2018-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