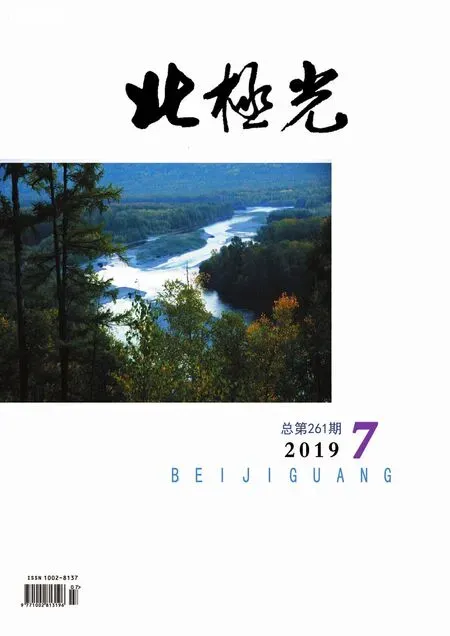生死鄉(xiāng)愁
⊙王鳳瑞
我是一頭牛。
我自幼奔跑在一望無際的大平原上,或跳躍穿梭在濃密的森林里。
每當(dāng)太陽落山時(shí),我站在丘陵上眺望著田野里勞作的人們。他們成群結(jié)隊(duì)地赤腳走在田埂上,肩上扛著石鋤,在燃燒著的晚霞里,我甚至能聽見汗水滴落在地上的聲音。勞作的男子們打著赤膊,古銅色的皮膚上沾著霞光,女子們挑著一擔(dān)擔(dān)清泉,澆灌干渴的土地。這幅我記憶里最深刻的圖景,像樂器的和弦,或一串吶喊,原始而滄桑。
直到有一天,我的主人把我領(lǐng)回他所住的,叫做“家”的立方形盒子里。他給我干凈的水,豐富的草料,以及溫暖干燥的草垛堆。我漸漸感受到我周遭的一切,不同于年少時(shí)期所經(jīng)歷的自然風(fēng)光給我的快樂,更是一種陌生卻親昵的溫暖。他用繩牽著我,來到田野上。漆黑的土地仿佛深邃安靜的夜空,從很遠(yuǎn)的地方飄來麥粒熱烈狂野的香氣。
我的脖子被套上繩索,牽引著千鈞重的鐵器。我和另一頭牛并排走著,拉著沉重的龐然大物,腳下黑色的土地被割開一道道深深的溝壑,柔軟而順從。金黃靈巧的麥粒撒在被鐵器打的均勻又整齊的孔洞中,像在夜空里閃爍的星星。我駐足觀賞,卻被鞭子狠狠地抽了一下,我被刺痛逼迫得向前走去,繩索深深勒進(jìn)我的皮肉,廣闊平坦的土地依然一眼望不到頭。我和我的伙伴東倒西歪的向著田野的盡頭跑過去,去追趕散發(fā)刺眼光芒的太陽。
從那個(gè)時(shí)候開始,夕陽下,再也不是古老的贊歌,而是疲憊嘆息著的土地。我知道,我告別了兒時(shí)在田野的風(fēng)中奔跑的那種活潑,告別了初春新生的嫩芽,每一個(gè)春天對我來說也只不過是更加繁忙的勞作。我知道了吊在我身上的大家伙叫“鐵犁”,也知道了在桑葚紅了的時(shí)候,人們就會(huì)種下麥子。我的視野范圍,也就只囚禁在一方狹小烏黑的土地之中了。
這樣的生活持續(xù)了幾十年之久。我的主人離世了,他的兒子來接班;鄰居大叔家的小孫子成人了,也能下地干活了。
時(shí)間像一只巨大溫溫吞的野獸,緩慢穩(wěn)當(dāng)?shù)匦凶咧|闊的黑色土地上生活著的人們還是不疾不徐的枯榮著。時(shí)間從我稀疏的牙齒間流過,我再也不能下地干農(nóng)活了。
我走出牛棚,費(fèi)力地咀嚼著鮮嫩的青草,我慢慢地走過碧綠的種滿小麥的田野,走向荒原,走向地平線。
然后我倒下了。
綜上所述,在小學(xué)美術(shù)教學(xué)中使用數(shù)字化教學(xué)資源不僅可以提高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主動(dòng)性,同時(shí)也可以改進(jìn)傳統(tǒng)教學(xué)模式中的不足,激發(fā)學(xué)生的參與熱情。因此,教師要運(yùn)用好數(shù)字化教學(xué)資源,提高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質(zhì)量,實(shí)現(xiàn)美術(shù)教學(xué)的目標(biāo)。
原來我?guī)资旮鞯耐恋鼐谷绱巳彳洠褐[約的香氣,沉默而溫暖。
下輩子也許還會(huì)成為一頭牛吧。
我閉上了眼睛。
我躺在柔軟的干草垛上睜開了眼睛。
今天晚上的月亮很亮,照著安靜的熟悉的牛棚。我打了個(gè)滾站起身來。新生的身體靈活而充滿力量。我望著布滿星辰的天空,想起它們還是種子時(shí)的樣子。
我等著黎明的到來。牛棚、馬廄、雞籠,熹微晨光照耀下的一切都不露聲色。
女主人的縫紉機(jī)吱吱扭扭響至深夜;商人駕著車一路顛簸揚(yáng)起塵埃;機(jī)械化大生產(chǎn)的時(shí)代來臨了。那個(gè)叫聯(lián)合收割機(jī)的大家伙真厲害,簡直是個(gè)長臂巨人,比我還要能干百倍、千倍。農(nóng)場主的孩子們經(jīng)常爬到我背上淘氣地唱著牧歌;金色的麥子,如同夕陽下的海浪,一層層卷向天空的盡頭。
陽光下,波濤洶涌著的麥浪海頃刻間掀起了萬丈巨浪。田間地頭眺望著的人們——我看見他們眼里閃著亮晶晶的光——一邊奔跑著,一邊歡呼。他以千百個(gè)我也不能匹敵的速度奔跑著,然后喘著粗氣停在田野盡頭,手里握著大把成熟的歡欣。
后來的日子我再也沒有被牽到田埂上,也沒有再經(jīng)過飄香的打谷場。我所做的只是弓著腰拖動(dòng)著載滿糧食的車子在許許多多雙腳中穿梭,或是就關(guān)在牛棚里,看著遠(yuǎn)處淺色的天空,陽光透過破碎的云片,在地上投下深淺不一的色塊。
我還做夢,夢里我躺在滿是星星的湖水里,那星星像麥粒一樣多的數(shù)不清,一閃一閃,又像田埂上的一雙雙眼睛。火紅的夕陽下傳來古老的歌聲,然后我渾身冰涼地從夢里醒來。
人們在村莊的邊緣蓋起了樓房,塵埃滾滾,掩埋了我的天空。田埂上負(fù)手而立的人眼里不再有閃亮的光芒。我在無人的田地里偷偷靠近高大的機(jī)器,沒有麥子的氣味,用舌舔一舔,冰涼而苦澀。
工廠搶奪了田地,我也找不到家了。
沒有了使用價(jià)值的我被送進(jìn)了屠宰場。和許許多多我的同類一起,關(guān)在狹小的籠子里,耳朵上別著號(hào)碼牌。它們聒噪地吼叫著,不安地扭動(dòng)著,瘋狂地掙扎著。
一個(gè)小女孩蹲在我面前,隔著鐵籠子怯生生的望著我。
提著屠刀的男人走過來,女孩兒拉拉他的衣角說:“爸爸,你看,牛在哭。”男人不耐煩地驅(qū)趕她進(jìn)屋,轉(zhuǎn)頭打開了鐵籠子的門。
我看著沾染了骯臟血污的屠刀,我閉著眼睛。
我的鼻腔留著小麥和機(jī)油的氣味,我親吻著土地。
巨大溫柔的蔚藍(lán)色星球仍在一刻不停地轉(zhuǎn)動(dòng)著,日升月落,陰晴圓缺,綠色陸地上生活著的生生不息的人們。
我又充滿了活力,沒有了病痛,身子輕盈極了。我飄飛著,回到了我的原野,我的森林,我的小村莊。
吹牧笛的孩子還在,村口的大樹變成了樹樁,樹樁上發(fā)出嫩綠的芽。工廠拆掉了,河水里的魚兒回來了,殘存的大煙囪里開出了美麗的玫瑰花,去城里的年輕人回來了,擁抱著他們的孩子。
我又止不住淚流,化作春雨滴答。淚眼朦朧里我看見老主人在遠(yuǎn)端那一邊向我招手,我知道,他也在找我們生死不滅的鄉(xiāng)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