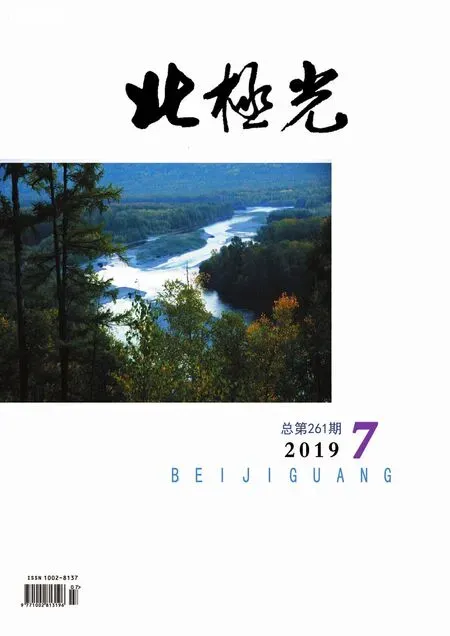肅南,哈達(dá)上的家園
⊙王振武
“西至哈至,夢(mèng)中的西至哈至。 祖先曾在那里放牧牛羊,祖先曾在那里休養(yǎng)生息。碧綠的草原是幸福的向往,五彩的經(jīng)堂是生命的延續(xù)。”
西至哈至,一個(gè)古老的歷史地名。它來(lái)源于裕固族民間傳說(shuō)故事及其民歌《堯乎兒來(lái)自西至哈至》,認(rèn)為西至哈至就是裕固族人民的故鄉(xiāng)。其確切的地理位置和確切的語(yǔ)言含義,歷來(lái)眾說(shuō)紛紜,莫衷一是。就連地道的肅南裕固族土著居民,也是說(shuō)不清道不明的。可見(jiàn),裕固族是一個(gè)神秘的民族,一個(gè)飽含了許多秘密的民族。
一
肅南,是個(gè)很有個(gè)性且充滿陽(yáng)剛氣息的特殊縣份。假若你打開(kāi)甘肅地圖仔細(xì)審視,定會(huì)發(fā)現(xiàn)肅南這個(gè)版圖的特殊性。它安臥在莽莽蒼蒼的祁連山腳下,整個(gè)地域東西長(zhǎng)六百多公里,橫跨甘肅河西五市,與甘、青兩省的十五個(gè)縣市相接壤毗鄰,裕固族、藏族、漢族、回族、蒙古族等17個(gè)民族的3.8萬(wàn)多人占據(jù)了2.4萬(wàn)平方公里的闊大地盤。假若你開(kāi)動(dòng)跨越時(shí)空的思維,再沉思默想下它的地形地貌,定會(huì)驚奇地發(fā)現(xiàn),圣潔的祁連雪線、茂密的原始森林、遼闊無(wú)垠的大草原,猶如三條宏大無(wú)比的圣潔哈達(dá),大氣磅礴地鋪展在廣袤的肅南大地上,肅南各族兒女就在這圣潔的哈達(dá)之上歡天喜地地勞作著,吉祥安康地生活著。其地理的特殊性和地域的廣闊性,由此可見(jiàn)一斑。
民樂(lè)與肅南,相依相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唇齒相依的親兄弟、好伙伴。家鄉(xiāng)民樂(lè)的西南邊緣,如修長(zhǎng)銀龍一樣綿亙的祁連雪線下的廣袤草原上,就匍匐著現(xiàn)今馬蹄藏族鄉(xiāng)所管轄的南城子、東城子、大泉溝、大坡頭、大都麻、馬蹄寺等村落和聞名遐邇的馬蹄寺、金塔寺。而這些大大小小的村落和石窟寺院,歷史上曾一度就是民樂(lè)的地盤,直至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成立后,才劃歸肅南縣管轄。管轄權(quán)屬雖然變化了,但生活習(xí)俗、民族情感、宗教信仰、文化交流始終密密匝匝地交織于一體,而且愈加貼近愈加親切了。
就是這樣一個(gè)飽含秘密的民族,一面七拼八湊的地理版圖,連同白雪皚皚的祁連山,碧草青青的大草原,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瑰麗神奇的石窟藝術(shù),化作了綿綿的思念,靜靜地流淌在我的心田,久久縈繞徘徊,難以釋然。
二
巍峨壯觀的祁連山,是河西走廊的父親山。它猶如一列長(zhǎng)長(zhǎng)的火車一樣?xùn)|西綿亙一千多公里。而肅南境內(nèi)的祁連山地段,蜿蜒長(zhǎng)達(dá)四百多公里,幾乎占了整個(gè)祁連山脈的一半。海拔4700米以上,終年積雪,冰川廣布。祁連山主峰素珠璉,七一冰川,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的發(fā)源地,都在肅南境內(nèi)安家落戶。莽莽蒼蒼的雪峰,明凈瓷實(shí)的冰川,大大小小的河流,猶如大地母親甘甜的乳汁一樣毫不保留地哺育滋養(yǎng)著河西走廊,是河西人民賴以生存的天然寶庫(kù)。正如匈奴歌云:“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也正如《中國(guó)國(guó)家地理雜志》所言:“正是有了祁連山,有了極高山上的冰川和山區(qū)降雨,才發(fā)育了一條條河流,才養(yǎng)育了河西走廊,才有了絲綢之路。”這樣至高無(wú)上的定位,對(duì)祁連山而言實(shí)至名歸。祁連山雪線以下,森林遍布,松柏長(zhǎng)青,千峰萬(wàn)壑綠浪翻滾。有林才有雨,有林好積雪。皚皚雪域孕育了大面積的水源涵養(yǎng)林,水源涵養(yǎng)林孕育了廣袤無(wú)垠的大草原,大草原滋養(yǎng)了河西走廊上包括人類在內(nèi)的一切生靈。冰川、森林、河流、草原,億萬(wàn)生靈,猶如祁連山的至親骨肉一樣,同生共榮,和睦相處,休戚相關(guān)。
祁連山特殊的地理資源,孕育了祁連山下豐富而廣袤的“賽罕塔拉”(美麗的大草原)。千里大草原,優(yōu)質(zhì)大牧場(chǎng),沿祁連山主脈呈“一”字形橫貫東西,地域廣闊,水草肥美,氣候涼爽宜人,生態(tài)環(huán)境良好。以肅南的多民族之所以能像石榴籽一樣抱團(tuán)成長(zhǎng),和睦相處,親如一家,所依仗的就是這遼闊無(wú)垠的大草原啊。皇城草原,馬蹄草原,康樂(lè)草原,大河草原,祁豐草原,明花草原,相互連綴起來(lái),猶如一系綠色的修長(zhǎng)哈達(dá),自東向西起起伏伏地鋪排飄蕩在祁連山腳下,將多民族同胞親密無(wú)間地維系在一起。廣袤肥沃的大草原,是馬牛羊駝鹿的天堂,也是野生動(dòng)植物的天堂,更是牧人的棲息圣地。高山細(xì)毛羊,絨山羊,雪域牦牛,白唇鹿,馬鹿,雙峰駝,是草原的驕子,牧人的驕傲。藍(lán)藍(lán)的天上白云飄,白云下面牛壯羊肥駿馬跑,就是大草原的形象寫照。牧人有了成群滿圈的馬牛羊,幸福的歌兒唱不完。臉上涂滿高原紅的裕固族姑娘,剽悍驍勇的藏族小伙子,打馬走過(guò)千里大草原,一會(huì)兒漫“少年”,一會(huì)兒唱“花兒”,就這樣跑著唱著,不知不覺(jué)間,便唱出了激情,唱出了感情,唱出了婚姻,唱出了吉祥幸福的游牧生活。雪豹,野牦牛,野驢,巖羊,盤羊,藍(lán)馬雞,時(shí)常在峰巒、溝壑、森林和大草原上曉行夜宿、晝伏夜出,或覓食撒歡,或激情舞蹈,或暗送秋波,或潛入牧人營(yíng)地與家畜家禽偷情做愛(ài),盡情享受著各自的榮華富貴,該是何等的逍遙自在啊。至于那高山雪蓮、冬蟲(chóng)夏草、高掛草、鎖陽(yáng)、野生蘑菇等等的名貴中藥材和名優(yōu)食材,更是各族牧民向外人夸飾炫耀的掌中寶和搖錢樹(shù)。牧人們將優(yōu)質(zhì)牛羊肉、鹿產(chǎn)品和野生名貴中藥材紛紛打出了雪域珍品、野生山寶、生態(tài)無(wú)污染飲品等等的金字招牌,或饋贈(zèng)親友,或網(wǎng)絡(luò)銷售,或就地交易,備受遠(yuǎn)方游客的青睞和喜愛(ài)。
三
圣潔的祁連雪線,茂密的原始森林,遼闊無(wú)垠的大草原,好不羞澀地鋪展在河西走廊的千里大地上,將“肅南”這個(gè)特殊縣份梳妝打扮得靚麗明艷,光彩照人。悠久的草原歷史文化,旖旎奇特的自然景觀,壯觀博大的丹霞地貌,神奇多彩的人文資源,瑰麗奇?zhèn)サ氖咚囆g(shù),濃郁獨(dú)特的民族風(fēng)情,傳統(tǒng)古老的生活習(xí)俗,多彩絢麗的民族服飾,美甲天下的地方特色小吃等,諸多地域本土元素集于一身,將肅南鍛造成了令人勾魂攝魄而又實(shí)至名歸的旅游避暑勝地,曾招引得國(guó)內(nèi)外游客們紛紛引頸矚目,時(shí)常蒞臨光顧,人人都在大呼小叫地驚訝贊嘆呢。由于地緣的緣故,我曾頻繁光顧過(guò)馬蹄草原,老早時(shí)的秋季就在水草豐美的東城子、南城子草原上跟著父親采摘野生蘑菇,冬季的星期天還要趕上驢拉車到草原上撿拾燒炕取暖的馬糞蛋和牛糞塊。高原草甸厚墩墩的,軟綿綿的,油亮油亮的,一年四季都給人以耳目一新的美感。無(wú)論是麗日晴空的秋天,還是冷風(fēng)嗖嗖的冬天,每次光顧草原,大草原始終以好客而寬廣的胸懷接納我,大大方方地供我欣賞藍(lán)天白云下成群的像灑滿珍珠一樣的牛羊,無(wú)怨無(wú)悔地任我東來(lái)西蕩地奔跑和踐踏,好讓我童稚般的心靈里時(shí)不時(shí)激蕩著滿滿的收獲和快樂(lè)。工作后熱衷于攝影,時(shí)常還要忙里偷閑地尋找一切機(jī)會(huì)搭車奔赴馬蹄草原、康樂(lè)草原和大河草原賞花觀景、采風(fēng)拍照,捕捉和定格大草原上的美麗瞬間,不知疲倦地將挺拔圣潔的雪山、茂密濃郁的森林、厚實(shí)柔軟的草甸、覓食撒歡的牛羊、熱情好客的牧民、飄香味濃的奶茶、肥美可口的手抓肉,一股腦兒地悉數(shù)打包收藏,好在閑暇時(shí)刻仔細(xì)地品味、慢慢地欣賞。更有那大河草原上人工馴養(yǎng)的成群的白臀馬鹿,猶如大草原上的律動(dòng)精靈,其美麗粗壯的茸角、激情跳躍的姿態(tài)、耳鬢廝磨的神情,準(zhǔn)令你激蕩不已的心情賞不夠、高端快速的長(zhǎng)槍短炮攝不完。
四
石窟和寺院是天造地設(shè)的一對(duì)孿生兄弟,在河西乃至全國(guó)的地界上,大都如此,比比皆是。肅南的大草原上,也毫不例外地派生了這樣的幾對(duì)孿生兄弟,諸如馬蹄寺石窟、千佛洞石窟、金塔寺石窟、文殊寺石窟、上中下觀音洞等。諸多的石窟和寺廟,寂靜地安臥在大草原上,招引得天下四面八方的僧尼和游客不厭其煩地光臨做客,大大方方、畢恭畢敬地上香跪拜,致使這里的石窟和寺廟名揚(yáng)天下,光環(huán)照人。
坐落在馬蹄藏族鄉(xiāng)臨松山下的馬蹄寺、千佛洞、金塔寺、上中下觀音洞,同歸于馬蹄寺石窟群的名下。石窟群中的七十多個(gè)佛龕,或橫向排列,或縱向排列,均開(kāi)鑿在臨松山谷的紅砂巖崖壁上。就其規(guī)模而言,馬蹄寺北寺最為突出,就其造像和壁畫而言,當(dāng)屬金塔寺和千佛洞最為重要了。馬蹄寺是窟群的中心,擁有南北二寺,聞名遐邇的是北寺中規(guī)模最大、結(jié)構(gòu)最為特殊的“三十三天”,高達(dá)數(shù)十米,自下而上縱列五層,十九個(gè)佛窟呈金字塔形排布。庫(kù)內(nèi)平面多方形、人字坡頂形、或盝頂四面坡形。每窟內(nèi)正面開(kāi)一個(gè)大佛龕,佛龕內(nèi)塑一尊佛像,佛龕外的四壁上,上面塑千佛,下面彩繪壁畫,佛像法相莊嚴(yán),壁畫多姿多彩,壯觀美麗。佛家弟子絡(luò)繹不絕地參禪求法,大批香客們紛至沓來(lái)地上香還愿,民族文化學(xué)者、美術(shù)攝影藝術(shù)家不厭其煩地頻頻光顧,大都是瞄準(zhǔn)了“三十三天”的赫赫大名而來(lái)的。至于佛窟佛龕的神秘和魅力,單從佛窟走廊通道里那些被行人踩踏磨光的石臺(tái)階上就能斷定出它們的誘惑力和分量來(lái)。石窟外一處處隨風(fēng)起舞飄蕩的經(jīng)幡,莊嚴(yán)肅立的佛塔,肆意綻放嬌艷的各色山花,連同來(lái)來(lái)往往的香客和游人,無(wú)不裝點(diǎn)和渲染了石窟藝術(shù)的神秘和魅力。魅力誘人的金塔寺石窟開(kāi)鑿在大都麻村刺溝內(nèi)的紅砂崖壁上,石窟與地面的垂直距離約六十多米,四周植被茂密,景色優(yōu)美如畫,是一處深藏掩映在天然勝景中的奇異佛教石窟。前些年窟外沒(méi)有登臨的石階,是很難一觀其神秘莫測(cè)的真容的。況且,鑒于安全和保護(hù)的重要,該石窟原本就沒(méi)有對(duì)外開(kāi)放的。近年來(lái),文保單位新建了登臨光顧的二百多級(jí)石臺(tái)階,開(kāi)窟門,方能零距離目睹窟龕內(nèi)的泥塑造像。紅色的砂石崖壁上,坐擁著東、西相對(duì)的兩窟,均是平面呈長(zhǎng)方形、中心塔柱窟、覆斗頂?shù)氖撸甲C年代也屬北魏時(shí)期,還傳說(shuō)該石窟是北涼皇帝沮渠蒙遜早年專為崇信佛教的母親開(kāi)鑿的。打開(kāi)石窟大門,只見(jiàn)中心方柱的四面均分三層開(kāi)鑿圓拱形佛龕,龕內(nèi)有泥塑造像,四壁的頂部多彩繪壁畫,或兩層,或三層。塑像和壁畫,都是北涼至元代的產(chǎn)物,顯得古樸典雅,宗教色彩極其濃郁。而最具特色的,當(dāng)屬東窟一層龕楣兩側(cè)懸塑的十多身立體高肉飛天菩薩像,個(gè)個(gè)挺胸蹺足,騁目注視下界,其飄飄欲仙、凌空飛舞的神態(tài),輕盈活潑、呼之欲出的動(dòng)感,顯得極其神奇瑰麗、惟妙惟肖,無(wú)不令人唏噓贊嘆。這些國(guó)內(nèi)絕無(wú)僅有的高肉雕塑飛天和豐富多彩的壁畫,具有很高的藝術(shù)價(jià)值,足可與敦煌莫高窟的石窟藝術(shù)相媲美。我很想把這樣難得的美景咔嚓咔嚓地全裝到相機(jī)里保存,好仔細(xì)地鑒賞,但文保員一再提醒自己,石窟里面是嚴(yán)禁拍照的,只好望美興嘆了。石窟規(guī)模雖小,但其造型藝術(shù)名揚(yáng)天下。寺廟雖無(wú)僧,但把守看護(hù)得卻很是寧?kù)o。假若你步入馬蹄寺旅游景區(qū)大門,首先撲如視野的就是千佛洞了。千佛洞也建于北涼時(shí)期,有北段、南段和中段三部分。北段多浮雕石塔林,大都是苦行僧居住和存放舍利子的處所。南段和中段以佛窟為主,窟內(nèi)開(kāi)佛龕、造佛像,窟檐為梵剎式的木結(jié)構(gòu)飛檐。陡峭的紅砂巖上,石窟石塔樓閣高懸林立,石梯棧道縱橫遍布,相互映襯,顯得富麗堂皇,極具詩(shī)情畫意之美麗。
五
位于祁豐鄉(xiāng)秋季牧場(chǎng)上的“七一”冰川,距戈壁“鋼城”嘉峪關(guān)市不足百公里,汽車出嘉峪關(guān)進(jìn)入直達(dá)鏡鐵山礦區(qū)的公路,翻越土達(dá)坂、吊達(dá)坂后,在吊達(dá)坂腳下折頭向南行駛,經(jīng)過(guò)便道到達(dá)黃毛溝口。然后從海拔4000多米的山腳下沿著彎彎曲曲的山路徒步登山,經(jīng)過(guò)約兩個(gè)多小時(shí)的艱難爬行,即可到達(dá)“七一”冰川。“七一”冰川海拔5000多米,冰川總面積3.64平方公里,平均厚度70米,大約發(fā)育于前震旦亞代至晚古生代時(shí)期。當(dāng)你邁著碎步艱難地攀爬上最后一個(gè)高臺(tái)地時(shí),大面積的冰川毫不吝嗇地讓你飽覽無(wú)余。從山頂?shù)缴焦龋瑵M眼的冰天雪地,在日光的映照下散射著刺眼的白光,恰似巧奪天工的瓊樓玉宇。一座座冰峰縱向排列,此起彼伏,堆銀集玉,好像九天銀河下凡,大有汪洋恣肆、一瀉千里、銳不可當(dāng)之勢(shì)。當(dāng)你小心翼翼地邁步徐徐深入到冰川的斷面時(shí),撲入視野的又是另一番景象。置身于這冰清玉潔的世界,猶如置身于神工鬼斧般精心打造的藝術(shù)殿堂。只見(jiàn)冰巖、冰崖拔地而起,盛氣凌人,如刀砍斧劈般陡峭嶙峋。潔白的冰乳順著一束束冰錐淅淅瀝瀝地垂下,猶如玲瓏剔透的串串珍珠鏈條,潔白無(wú)暇。無(wú)數(shù)蜂窩狀的冰洞中,洋溢出涓涓細(xì)流,在冰崖下匯成淙淙小溪,時(shí)而有形,時(shí)而無(wú)影,時(shí)而有聲,時(shí)而無(wú)音,神妙莫測(cè)。間或有兩三只蒼鷹翱翔雄視于藍(lán)天、白云和冰峰之間,愈加襯托出了冰川的雄偉壯觀和高潔無(wú)極。
六
占據(jù)白銀、康樂(lè)、大河鄉(xiāng)境內(nèi)的丹霞地貌,當(dāng)屬肅南的一大奇觀。奇形怪狀的丹霞地貌,以窗欞狀、宮殿式居多,曾被中國(guó)丹霞地貌旅游開(kāi)發(fā)研究會(huì)終生名譽(yù)會(huì)長(zhǎng)黃進(jìn)先生定位為“肅南窗欞狀、宮殿式丹霞地貌中國(guó)第一”,其300多公里之大的面積,絕冠華夏。進(jìn)入丹霞景區(qū),一處處垂直發(fā)育的紅色巖層,在風(fēng)吹、日曬、雨淋、沖刷、切割、崩塌等諸多力量的綜合作用下,將一處處地貌鍛造剝蝕成了平臺(tái)、方山、石谷、石柱、石墻等形態(tài)各異的丹霞地貌奇觀。它們有的像羅馬城堡,神秘莫測(cè);有的像帝王皇宮,巍峨雄渾;有的像金駝?dòng)e,憨態(tài)可掬。有的像石柱擎天,有的像寶塔凌空,有的像寶劍沖天,有的像陰陽(yáng)并舉,有的像惡虎爭(zhēng)斗,有的像巨龍騰天,有的似仕女漫步青云端,有的似達(dá)摩面壁思過(guò)錯(cuò),有的似老和尚念經(jīng),有的似牧童拜觀音,有的似菩薩下凡界。真?zhèn)€是溝溝有美景,岔岔見(jiàn)奇觀,五步一小景,十步三換景,惟妙惟肖,流光溢彩。所有這諸多奇形怪狀的絕妙景觀,足可以值得你放慢腳步仔細(xì)觀察,駐足留戀地慢慢鑒賞和品味它們的無(wú)窮魅力來(lái)。每當(dāng)晨曦微露時(shí)刻,周遭的平臺(tái)、方山、石谷、石柱、石墻,自上而下地徐徐鍍上了一層銅,泛著縷縷金光,色彩格外艷麗迷人。每當(dāng)夕陽(yáng)灑落時(shí),余暉斜射在一處處姿態(tài)萬(wàn)千的山體上,有的如妙齡女郎身披金縷玉衣裳,靚麗明艷,光彩照人。有的恰似力士金剛和山神,巋然不動(dòng)地默默守衛(wèi)著這片風(fēng)水寶地。置身于絕妙奇景,游客們便紛紛端起長(zhǎng)槍短炮咔嚓咔嚓地按動(dòng)快門定格這神工鬼斧般的美景,唯恐錯(cuò)過(guò)遺漏了這千載難逢的一幕。
七
大凡少數(shù)民族,大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裕固族也毫不例外。他們向外人介紹時(shí),動(dòng)不動(dòng)會(huì)很自豪地說(shuō):“我們的娃娃嘛,剛會(huì)說(shuō)話就能唱歌,剛會(huì)走路就能跳舞。”這話說(shuō)得雖有些夸張和懸乎,但贊嘆他們能歌善舞一點(diǎn)兒也不過(guò)分。他們有句俗話說(shuō):“當(dāng)我忘記了故鄉(xiāng)的時(shí)候,故鄉(xiāng)的語(yǔ)言我不會(huì)忘;當(dāng)我忘記了故鄉(xiāng)語(yǔ)言的時(shí)候,故鄉(xiāng)的歌曲我不會(huì)忘。”可見(jiàn),唱歌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放牧的草原上,你可以看到整群整群的牛羊,也隨時(shí)能聽(tīng)到動(dòng)聽(tīng)的歌聲。剪羊毛、織帳篷、搟氈襖等等勞作的過(guò)程中,既可欣賞到他們慢悠悠的勞作習(xí)慣,也能聆聽(tīng)到勞作者引人入勝的歌謠。婚喪嫁娶的特殊場(chǎng)面中,高水平的職業(yè)歌手更是接二連三地登臺(tái)表演。或悲壯的葬禮,或喜慶的婚禮,都是在壯美歌聲的伴奏中完成一個(gè)接一個(gè)的程序的。裕固族也是個(gè)很浪漫的民族,決定了其民歌的內(nèi)容非常豐富,大多取材于勞動(dòng)生產(chǎn)、生活方式和風(fēng)俗習(xí)慣中,而且曲調(diào)相當(dāng)優(yōu)美,節(jié)奏簡(jiǎn)潔明快,極具鮮明的地方民族特色。諸如《夢(mèng)中的西至哈至》《家園》《裕固族姑娘就是我》《姊妹三個(gè)都嫁給你》《紅纓帽子頭上戴》《說(shuō)著唱著才知道了》《我只得到處含淚流浪》等民歌,就逼真地反映了裕固族的遷徙史、婚宴祝酒歌、以及裕固人背井離鄉(xiāng)的綿綿鄉(xiāng)愁等。裕固族詩(shī)人們也很豪爽,著名詩(shī)人賀繼新在酒至半酣時(shí)刻,常常會(huì)異常興奮地跳到沙發(fā)上揮動(dòng)手臂大聲高歌或吟詩(shī),激動(dòng)豪爽之情溢于言表。裕固族激情飛揚(yáng)、慷慨豪放的民族舞蹈,更是張掖大地上獨(dú)樹(shù)一幟的絕活。建國(guó)以來(lái),裕固族舞蹈代表張掖人民多次赴京跨國(guó)登臺(tái)演出,獲得了多項(xiàng)殊榮,贏得了廣泛贊譽(yù)。
“我的家在很高很高的地方,馬背上的人們能撫摸到月亮。我的家在很遠(yuǎn)很遠(yuǎn)的地方,溫暖的氈房里兒女在成長(zhǎng)。當(dāng)你從絲綢之路走過(guò),她會(huì)留住你的腳步。當(dāng)你把祁連山遙望,她會(huì)牽引你的目光。美麗的風(fēng)光,遍野的牛羊。雪山腳下建立迷人的畫廊。幸福的歲月,飄散的酒香。我們的家園是人間的天堂。”一曲《家園》,唱出了肅南各族牧民的心聲,也激蕩了我等蕓蕓眾生的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