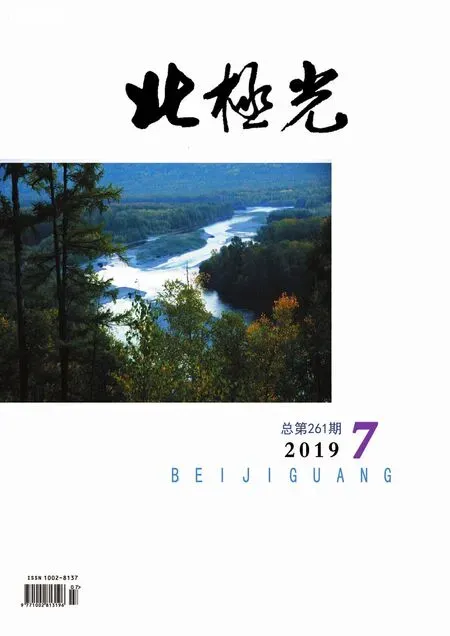半枝桐花煙雨中
⊙洪 波
梧桐花苞炸開了!用不了幾天,樹頂就會傘篷一樣了。似印度舞女,神秘、肥碩而健壯,晃動著綴滿腰肢的鈴鐺,打著響板,啪啪地開放著。
香氣襲來,尋,卻又似無。只聽得蒼茫大地上,一簇簇號角發出的賴音,一陣陣掠過耳畔。你若深深嗅上一口,一準兒會被這積蓄了整整一冬的氣息襲個跟頭。
那花實在是太濃密、太茂盛了。
森林公園
去年,我觀梧桐花盛開的滋味不同于往年。如果說以往是梧桐花香的淋浴,由上而下的,去年則是香熏浴了,是由下而上的。因為我是在四樓向下望了。蓬蓬團團的樹冠,紫氣升騰著,直讓人踉踉蹌蹌走不成溜了。
去年這個時候我有家了,流浪了十七年的人有家了。向窗外一望,便被蒸騰的花氣降伏在那里。都說人生有百般滋味,這是關于自己家的第一般滋味了。那蓬勃而盛大的氣勢啊。久已切盼的家庭的溫馨就藏在這花里了。
做夢也沒想到會在這里買房子。距離我客居了十年的地方那么近,而且公園依然很近。
這公園是那么小,以至于回農場探親看到農場的森林公園就聯想到她。她要是像森林公園那么大該有多好啊。她默默陪伴了我十年,無論我多么落寞,她都接納著我。草坪上,光滑的石頭上,栗子樹下曲曲的甬路,還有那密密交織著的紫藤蔓……
令人欣喜的是,小公園真的在我的期盼中擴大了。可與農場的森林公園媲美了。不同的是,森林公園三面環繞的是成片的叢林和一望無際的田野,而青州旗城(北城)公園三面環繞的是居民區。我經常把旗城的小公園想象成農場的大森林公園,那么,我所在的梧桐花篷蓋上的居處,與森林公園相對應的地方,就該是那密密匝匝的叢林了,偶爾會有松鼠和鼴鼠光顧花園里的歐式長椅。蹦蹦跳跳地、機敏地張望著,倏忽就沒了蹤影。云雀在樹梢上劃了一個優美的弧線,便悠然從一棵樹腰那里消失了。莊周夢蝶,蝶夢莊周,旗城公園真的成了我心目中的森林公園了。
純粹
買房子是一個標志性的轉折。我的生活方式、人生轉型皆從這一年有了實質的變化。哪怕一點點有益的進步,我都堅信自己還在為理想做著什么。從沒有停止過,從沒想過要放棄。一輩子都做一件事。死了也不悔。死的時候只會考慮自己沒有為理想做得再多些,而不是被一些東西牽絆著荒廢了許多時間。
這些年為理想積蓄的一切氣韻和力量,都有了明確的歸屬和依傍。有了明確的地位。她們越來越名正言順。我理順著她們,修復著她們,她們越來越俊美,越來越硬實。
這幾年我積蓄了很多美妙的東西,沒有無謂地消耗她們。揮霍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完好無損地保留著那些最初的瓊漿一樣的東西。她們只有到現在才能噴薄而出,難以遏止,永無干涸。我需要好好整理她們,繼續前進。
一想起未來,看看前面的那些大師,又會嫌自己積蓄得太少,不夠勤奮。終是為浮躁的心荒廢了許多美好的東西。我吃著咸菜,喝著清水,穿著自己縫制的衣服,我崇尚沒有被物化的理想。我固執地清苦地堅守著,不曾后悔,我為自己終究還是個純粹者而暗暗欣喜著。哪怕是個乞丐浪人,甚至流落風塵,也是要來得純粹些。我還是我,最困難的時候都曾經純粹,以后還有什么能使你不純粹呢?
想要有個家
二零零七年初我寫了十個愿望。關于自己的愿望只有兩個,第一個是成為一名編輯,這個愿望那么樸素那么容易使我滿足。我想象它有六成是與才情有關,其余的四成與機遇有關。我干脆就把這個愿望交托給天了,讓天替我擔當等待的焦急、切盼的苦悶吧。
第二個愿望就是有個自己的窩。我知道,所謂的愿望,大抵是指難以實現的事。但同時我也想,那么簡單的幾個夢想,總該有個結果,總會有個結果的。果然,梧桐花開時,我有家了。本來我早已經放棄買房子,一心供下孩子上學就不錯了。自己的曲子讓他自己去唱吧。可是房子竟然有了,天意誰能猜得透呢?
其實,誰沒有個家呢?多少人一下生就都預備好了。一次爬山,路過一個漂亮的雞舍。我想,雞尚有個窩,我卻沒有。那陣子真敏感。為著一個鳥的巢穴,一只狗的居所。
曾把房子叫做鋼筋水泥的棺材,沒裝修的時候,不就是個丑陋的棺材嗎?裝修好了,就被稱為房子、華屋、別墅了。不是有很多人把墓穴叫房子嗎?一個稱呼而已。
以前從小區走過,只要看見女人提著鑰匙開門,我就會想,她的家在這里,我的家在哪里?她們七拐八拐,嘩啦啦掏出鑰匙去開那扇自己的家門……
她們從不同的地方拐出來,到商場學校火車站和菜市場,再回到一開始出來的地方。那個地方就是家。她們的家。而我則穿過一條條胡同向別人的家里拐,我的鑰匙開的是別人家的門。我從那個家里拐出來,去這里去那里。從不是自己家的地方去不是自己家的更多的地方。我已經習慣用鑰匙開別人家的門。已經習慣用最快的速度把別人的家當成自己的家。已經習慣孩子繞在身邊說,媽媽,咱回家吧。
連我自己也數不清,這些年我一共有過幾個家。幾個呢?反正,最后的客居地是東店中街。
東店中街十年
穿過那個曾經客居了十年的東店中街時,總是忍不住回眼望那間房子。洪月制衣、夢羅蘭制衣、內衣新方向,這些我曾經用過的門號已被一一地摘去了。
房子被一個賣茶葉的南方人租去了,那里除了一幅我親手貼在墻上的《牧羊人》,已經與我沒什么關聯了。當時我正小心翼翼地摘那幅畫時,南方女人說:那幅畫你還帶走嗎?我看了一眼她略有殘疾的眼睛流露出對畫中牧者的崇敬,我讀懂了她的心情,心照不宣地對她說:留給你吧。我們不約而同地笑了。
其實我很喜歡那幅畫,打算再去教堂買一幅。后來教堂里又來了好多版本的《牧羊人》,有的甚至還是很精湛的油畫,但都沒有我帖的那幅《牧羊人》畫得純凈、澄明。
那夫妻兩個人不錯,路過的次數多就會忍不住去坐一會兒。我曾經是這里的主人,賓朋滿座,高談闊論,煙霧繚繞,甚至有時候還想醉酒。
他們有一個剛上學的小男孩。他們寵著他,給他買防真皮毛的駿馬。他們把房子打扮得還算可以,看得出已經盡力了。與我不同的是,他們盡可能衣食住齊備方便,而我則是充滿了藝術氣氛填充空虛的靈魂而已。他們在他們的世界里生活著,我在我布置的世界里生活過。曾經掙扎、抗拒,也快樂過。以后仍會有這些東西。只要活者,這些東西就總會有。
他們給我倒茶、讓座,把我當客人待。他們忙著的時候,我空閑的心找不到一絲作為主人時的感覺,終究還是告辭了。
幾次路過這里向新買的家走去,都走過站了。好像才從原來那個家出來要去別的地方一樣。當我恍然醒來,就會奔跑著上樓,像以前看到的那些女人一樣,手提鑰匙打開那扇鎖著的門。心里盤算著如何去接父母來住一陣子。
記不清以前從這里走過多少遍了,風掠過草原一樣沒有痕跡。從沒想過這個朝東開著的大門里面有一幢樓與我相干。那其中的單元里有寬大的陽臺和一間小書房——伍爾夫說的一個女人要有自己的一間房子。還有什么能比這更讓我知足的呢?無論去哪里,走多遠,多么辛苦,最后都可以回這里休息。
在精神上追求純真到極致的人,在物質上如此容易滿足。我想,上天給我這樣的心性兒,是為著一種匱乏和豐富的平衡吧。
南屋家的
東店中街之前,我們曾在青云橋下住過整整四年,叫高家園。那個時候我剛從農場來到小城。我說,這哪里是高園,分明是低園。那房東小老太太所問非所答地糾正說,這是在一溜崖頭的下面。
小老太太的腰總是彎成九十度,整天背著她的寶貝孫女在高家園的街上轉,一會不見就叫魂似的到處喊她的小名。我每次出去買東西回來迷路的時候,都會在街上看見她,然后跟她一起回家。不知道她是否看出一個新娘找不到家的窘迫與羞澀。她現在應該八十多歲了吧?那個寶貝孫女也應該做新娘了吧?聽說小妮子出落得很漂亮了。她的媽媽曾經救過我的命。那年過小年,大家都趕河灘集去了,只有我在家用蜂窩煤爐子蒸饅頭。我感冒了,窗戶上糊著塑料布還嫌冷,披著大衣用小鼓風機吹爐子里的焦炭。她回來了,聽見我在屋里微弱的喊聲……我被灌了綠豆湯,用折疊床放在屋子外面了。沖著高家園的大街,身上蓋著才結婚的大紅被子。有人問這是誰啊?房東老太太說:南屋家的。
他們管我的丈夫叫南屋,管我叫南屋家的。因為我們住的是南屋。我們的孩子就在那里出生的。孩子被叫做南屋家的孩子。南屋沒有院子,這個朝北開門的屋子在房東家的院子外面,挨著房東家朝東開的大鐵門。南屋門向北有個巷子,住著幾家劉姓的人。房東家的人和巷子里的人經過南屋的時候,都隨便說話,摩托車也哼哼地過。南屋真像個傳達室,誰來了,誰走了,我們都一清二楚。我們全家吃飯睡覺生活的時候,都在為他們當保安。經常會擔心孩子被摩托車的轟鳴聲嚇壞了,然而那個可愛的小家伙對這些聲音充耳不聞,一派鎮定自若的樣子。
每次上廁所都得到房東家院內的馬廄里,總是害怕那匹馬因為陌生傷到我。其實我在農場是見過馬的,還坐過父親趕的馬車呢。后來我懷孕了,阿厚就和我一起去到橋上公廁。每次去公廁都像去出游,手挽著手,沿著青云橋一直向電影院走,向火車站走。哪里有長椅,哪里有花壇我們都能悉數。真是開心呢。
駐防城和菜園
四年以后我們搬到駐防城去了。這次是租的北屋,終于洗請了那個“南屋家的”名字。后來在街上遇見高原房東家的人還是稱呼我為“南屋家的”,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不知道這是房東對客家的態度,還是儒家傳統男人對女人地位的習慣定位。
北屋的房東稱我為小洪。房東是個老鄉。后來聽說,房東的丈夫出車禍走了。房東的弟弟,一個很英俊的男生,在與鄰居出車的時候也出事了,他還沒嘗過愛情的滋味呢。那個善良的房東的母親,對我們特別好,我真想去看看她,安撫她痛失獨生愛子和姑爺的傷痛。
兩年后,為了孩子上學方便,我又搬到火車站附近的菜園去了。這次租的是西屋。房東夫妻非常恩愛,丈夫坐在自來水邊上洗衣服,妻子站在丈夫身后給他搖蒲扇,驅趕炎熱和蚊蟲。偶爾我會想,從南屋到北屋,又到西屋,就差東屋了。是不是四個方向的屋都住過了,才能有自己的屋呢?
一年之后,我來到東店中街租了一個門市房,果然是東屋。為著自由和不羈的個性,為著一場至今讓我心有余悸的迫害,我必須自己做生意了。時值1997年香港回歸。那時東店中街還是一條土街,只是住戶和抄近路的人從這里走。北城花園石碑那里零零落落有幾個賣蔬菜水果的。我的服裝店在這里一做就是十年,我見證了整個東店中街的興起和消失。
有一個外地女人在這條街上苦做了十年,最后買房子走了——人們這樣傳說著。
現在這條街要被拆遷了。大家已經在討論改名叫石坊路,還是衡王府路了。
回頭想想,這些年好像一直在為這次買房子生長根須。現在找到了合適的地方,一并扎下去,留在這里了。所有的往事,都留與煙雨中那半枝桐花慢慢訴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