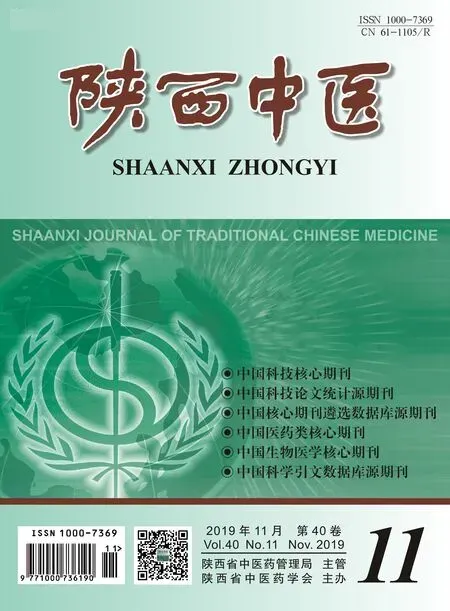神經復元方治療缺血性卒中后抑郁臨床研究*
蔡 麗,劉 毅,陸小青,董耀榮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市中醫醫院 (上海 200071)
腦卒中是各種原因引起急性腦循環障礙導致局限性或者彌漫性腦功能受損的一組疾病,根據基本病理學表現又可分為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是當今世界危害人類生命健康的最主要疾病之一,具有極高的致殘率和死亡率。其中缺血性卒中約占腦卒中總數的60%~80%[1]。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是腦卒中后經常伴發的病癥,可發生于卒中后的任何時間,影響約 1/3 的卒中存活者,累積發生率可達55%[2]。PSD 嚴重影響了卒中患者的神經功能康復及回歸社會的能力,導致腦卒中的復發率及死亡率明顯提高。神經復元方是上海市中醫醫院老中醫李如奎教授治療神經系統受損恢復期臨床驗方,筆者采用隨機分組、安慰劑雙盲對照、多量表測定的研究方法,規范評價察神經復元方治療缺血性卒中后抑郁的療效,并初步探討其作用機制是否與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相關。
資料與方法
1 一般資料 選擇2016年12月至2019年1月期間在上海市中醫醫院腦病科、心病科以及合作單位上海市靜安區神經內科門診確診的缺血性卒中后抑郁患者120例,采用分層隨機法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每組60例。兩組在年齡、性別、HAMD評分等方面評定情況見表1。在研究過程中,對照組脫落4例,治療組脫落3例。

表1 兩組基線資料比較
注:兩組間基礎資料比較,性別比例、年齡分布及HAMD基線評分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診斷標準:參照《卒中后抑郁臨床實踐的中國專家共識》[3]。符合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病學術會議制訂的腦梗死診斷標準《各類腦血管疾病診斷要點》[4],并經CT或MRI證實;同時符合《中國精神疾病分類方案與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3)[5]中抑郁癥診斷標準,且腦卒中與抑郁有明顯的前后相關性。
納入標準: ①經CT 或MRI 證實腦梗死的腦卒中診斷;②診斷符合上述診斷標準,且抑郁發生在卒中后1年內;③年齡≥40歲和≤80歲;④7分 排除標準: ①腫瘤、血液病所致腦卒中;②合并有嚴重心血管疾病、血液病、肝腎功能異常、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或嚴重消化系統疾病者,或合并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壓)控制不良者;③合并癲癇或者神經精神疾病者;④嚴重腦卒中病史引起的肢體功能障礙、嚴重失語、失認無法溝通者;⑤過敏體質及對試驗藥和對照藥已知成分過敏者;⑥妊娠或哺乳期婦女;⑦有藥物及酒精濫用史;⑧漢密爾頓焦慮量表 HAMA評分≥14分的患者;⑨近1個月內參加其它臨床試驗者。符合上述其中一項者,即予排除。 脫落標準: ①發生某些突發性嚴重疾病、嚴重并發癥等不宜繼續本研究方案者;②出現嚴重不良反應不宜繼續本研究方案者;③因故不能繼續參加臨床試驗或無任何原因患者自行退出者。 2 治療方法 本研究采用隨機分組、安慰劑對照、雙盲分析設計。參照研究方法[7]。制作隨機信封,受試者經診斷確認,隨機分配到治療組和對照組。試驗前按受試者編號給藥品編號,研究醫生給予受試者開具中藥處方,藥物管理人員管理信封并按受試者編號發藥,研究醫生和受試者均不知組別。治療組、對照組在內科常規治療基礎上分別予以神經復元方治療和中藥安慰劑治療,療程8周,治療過程中做好各類量表、問卷的統計,形成病例報告表。所有病例報告表雙份入庫,數據庫鎖定,然后進行盲態審核會。第一次揭盲只列出每個受試者分屬兩個組別(如A、B組)而不標明具體組別,交由統計分析人員分析形成報告。再進行第二次揭盲,明確A、B具體為對照組還是治療組,最后評價整體療效。對缺血性卒中后抑郁患者,西藥基礎治療采用百優解(國藥準字J20160029),20 mg/片,1d1片。兩組病例在試驗觀察期內不改變西藥種類和用量。 2.1 治療組:每天服用神經復元方藥,采用單味中藥配方顆粒,該方由熟地、制黃精各15 g,石菖蒲12 g,廣郁金、丹參、僵蠶各9 g,全蝎3 g組成。2次/d,每次1包,用開水沖服。 2.2 對照組:服用中藥安慰劑,制備方法參照文獻[7],取神經復元方原方藥量的1/20,余量補以麥芽糊精和食用色素,其包裝、外觀、色味和服用方法等與原方相同。 3 觀察指標 3.1 BDNF水平檢測:治療前、治療第2、4、8周,于安靜清醒狀態下,上午8~9時取血測定,采用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LISA),根據購自上海恒遠生物技術發展有限公司ELISA試劑盒說明進行操作,檢測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水平。 3.2 安全性指標:治療前及治療2、4、8周時分別檢測兩組患者血常規、尿常規、糞便常規加隱血、肝腎功能、尿N-乙酰-β-D-葡萄糖苷酶(尿NAG酶)、尿微量白蛋白、凝血功能、心電圖等指標,隨時觀測并記錄不良事件。 4 療效標準 分主要療效指標和次要療效指標,評定主要療效指標包括: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評分、日常生活能力評定(Activity of daily living,ADL)與改良Barthel指數(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評分。入組前采用HAMD[6]量表(17項標準)進行評分篩選,判斷標準為:7分<評分≤17分有輕度抑郁; 17分<評分≤24分有中度抑郁;>24分表示有重度抑郁。治療中用HAMD量表評估病人抑郁改善程度,通過計算治療前后減分率予以判斷,HAMD減分率=(治療前分數-治療后分數)/治療前分數×100%,臨床痊愈:減分率≥80%,主要核心癥狀(情緒低落、言語動作減少、思維遲鈍)消失,接受康復治療很主動;顯效:50%≤減分率<80%,核心癥狀基本上消失,生活自理能在肢體功能許可范圍內進行,能較好的配合康復治療,但興趣未完全達到正常;有效:30%≤減分率<50%,抑郁癥狀有一定改善,但接受康復治療還比較被動;無效:<30%,抑郁癥狀無改善[8]。采用改良Barthel指數MBI[9]評估患者生活質量,分數越高,表示患者獨立自理性越好。采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10]評估患者生活能力改善情況,分數越高,表示患者功能障礙更嚴重。 次要療效指標包括:中醫癥候積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評分和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A)。中醫癥候積分評定標準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試行)》[11]擬定,通過治療前后減分率來評價患者中醫癥狀改善情況。痊愈:判證依據是治療后癥狀消除或基本消除,減分率>75%;顯效:癥狀明顯改善,減分率51%~75%;有效:癥狀有所改善,減分率25%~50%;無效:癥狀沒有改善,減分率<25%。NIHSS[12]評估患者神經功能缺損程度。HAMA[13]評估患者焦慮癥狀嚴重程度。上述指標分別在患者入組時和治療第2、4、8周時測定,共4次,動態觀察評定療效指標變化。 1 兩組HAMD評分及抑郁癥狀改善程度比較 見表2~3。治療組治療兩周時較治療前明顯減少(P<0.05);治療4周和8周后顯著低于治療前(P<0.01),且顯著低于對照組(P<0.01)。對照組在治療兩周時較治療前變化不明顯(P>0.05),治療4周和8周后,與治療前比較差異明顯(P<0.05)。計算兩組治療前后減分率評價抑郁癥狀改善程度,兩組總有效率分別為94.8%和69.7%,治療組顯著優于對照組(P<0.01)。 2 兩組ADL量表評分比較 見表2。治療組治療兩周時,相比治療前差異不明顯(P>0.05)。治療4周、8周后較治療前均顯著降低(P<0.01),且評分明顯低于同時間對照組(P<0.01)。對照組治療2、4、8周時評分較治療前差異不明顯(P>0.05)。 3 兩組MBI量表評分比較 見表2。治療組治療兩周時較治療差異不明顯(P>0.05)。治療4周、8周后較治療前均顯著增高(P<0.01),且評分明顯高于同時間對照組(P<0.01)。對照組治療2、4、8周時評分較治療前差異不明顯(P>0.05)。 表2 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前后主要療效指標評分比較(分) 注:經t檢驗,兩組治療前比較,P>0.05;同組內與治療前比較,△P<0.01;與對照組同時間比較,◇P<0.01 表3 治療組與對照組抑郁癥狀改善程度比較[例(%)] 4 兩組NIHSS量表評分比較 見表4。治療組治療兩周較治療前評分變化不明顯(P>0.05);治療4周時較治療前有明顯降低(P<0.05);治療8周后較治療前顯著降低(P<0.01),且顯著低于對照組(P<0.01)。對照組在治療4周和8周后較治療前差異不明顯(P>0.05)。提示神經復元方可有效修復抑郁患者神經功能缺損。 5 兩組 HAMA量表評分及焦慮癥狀改善程度比較 見表4~5。治療組治療兩周較治療前評分變化不明顯;治療4周和8周時評分均明顯低于治療前和對照組(P<0.01)。對照組在治療兩周和4周時較治療前無明顯變化(P>0.05),治療8周時較治療前明顯降低(P<0.01)。計算治療前后減分率評價療效,兩組改善焦慮癥狀的總有效率分別為73.7%和12.5%,治療組顯著優于對照組(P<0.01)。 6 中醫癥候評分及改善程度比較 見表4~5。治療組治療兩周、4周、8周后較治療前均有顯著降低(P<0.01),且顯著低于同時間對照組(P<0.01)。對照組治療2周、4周時評分差距不明顯(P>0.05),8周時評分較治療前有明顯降低(P<0.05)。提示神經復元方可改善患者中醫癥候,隨著療程增長,改善程度越好。計算治療前后減分率評價療效,兩組中醫癥候改善總有效率分別為85.9%和14.3%,治療組顯著優于對照組(P<0.01)。 表4 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前后次要療效指標評分比較(分) 注:經t檢驗,兩組治療前比較,P>0.05;同組內與治療前比較,△P<0.01;與對照組同時間比較,◇P<0.01 表5 治療組與對照組焦慮癥狀及中醫癥候改善程度比較[例(%)] 注:兩組計數資料經χ2檢驗,兩組焦慮癥狀改善程度比較,χ2=43.05,P<0.01;兩組中醫證候改善程度比較,χ2=44.92,P<0.01 7 兩組患者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的比較 見表6。治療組在治療4周后,BDNF含量較治療前明顯增高(P<0.01),且較對照組差異顯著(P<0.01);對照組治療后各時間較治療前均無明顯差異(P>0.05)。分析HAMD與BDNF相關性,從圖1中數值線的趨勢看,隨著BDNF濃度增加抑郁量表HAMD評分逐漸減少,兩者呈負相關。 表6 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前后血清中BDNF含量比較(ng/ml) 注:兩組治療前比較,P>0.05;同組內與治療前比較,△P<0.01;與對照組同時間比較,◇P<0.01 圖1 HAMD與BDNF相關性分析 8 兩組患者安全性指標比較 觀察期間,治療組出現胃部不適2例、腹脹不適1例;對照組出現輕度胃腸脹氣不適2例。受試者治療前后血常規、尿液分析、糞便常規+OB、尿微量白蛋白、尿NAG酶(N-乙酰-β-D-葡萄糖苷酶)、肝功能、凝血功能及心電圖檢查未見明顯異常變化。對照組與治療組不良事件發生率分別為3.57%、5.26%,兩組差異不明顯(P>0.05)。 PSD是發生在卒中后的一系列郁證的表現,目前很多研究者認為本病屬中醫學“中風病”、“郁證”范疇,屬于“因病致郁”兩者合病而成。中醫學認為,中風的病因病機是在內傷積損的基礎上,復因外邪、情志、飲食等而誘發,導致氣血逆亂。郁證的病因病機是七情所傷,情志不舒導致肝氣郁結,氣機運行不暢。卒中后抑郁是中風后氣血上沖于腦,加之情志不舒,肝氣郁滯所致。其病位多責之于腦,發病多涉及心、肝、脾、腎等諸臟,與風、痰、瘀、虛有關,屬本虛標實之證。所以臟腑氣血陰陽失調、腎虛肝郁是本病之本,氣滯痰瘀為標,治療當滋補心氣和腎精,同時疏肝利氣,化痰祛瘀,從而達到治病求本的目的。本研究對入組的PSD患者中醫證候要素進行分析歸納,發現陰虛、痰濕、血瘀、氣滯證所占比例最高,符合本病肝腎陰虛為主,痰瘀氣滯為標的病機特點。神經復元方源于名老中醫李如奎教授臨床驗方。方中熟地、制黃精,補腎健脾,意在使脾氣健運,氣血生化有源,精血轉化充足,精旺以養神。石菖蒲配伍廣郁金,祛瘀定志,豁痰開竅,暢氣達郁。丹參活血補氣,寧心安神。佐之以全蝎、僵蠶,平肝熄風,化痰散結。諸藥合用,心肝脾腎同補,氣血兼顧。 從治療結果分析,結果表明神經復元方可有效改善患者抑郁癥狀、焦慮癥狀和中醫癥候,提高患者生活質量,一定程度修復神經功能缺損。從治療時間上看,治療4周后綜合療效更加明顯。 “神經營養假說”認為BDNF在維持和促進多種類型神經元的生長、發育以及神經再生中起著重要作用,而且其在神經元損傷后的再生修復和預防神經細胞退行性病變等多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14-15]。抗抑郁藥物發揮治療抑郁作用可以通過增加腦中BDNF的含量、改善突觸的可塑性和促進神經元的生存達到的。大量關于外周血中BDNF水平的研究包括幾篇meta分析,其結論一致認為:PSD患者外周血的BDNF水平低于正常人[16],而經過抗抑郁治療后BDNF水平會隨著癥狀的緩解而升高[17];蔣華玉[18]等研究發現PSD患者在腦卒中恢復期血清BDNF含量顯著降低,且腦卒中后抑郁程度與腦卒中恢復期血清BDNF含量呈負相關。雷敏[19]等研究發現丁苯酞改善腦卒中后抑郁患者抑郁狀態時,患者血清中神經細胞因子(NGF)和腦源性神經因子(BNDF)水平均顯著高于對照組。本研究對神經復元方的效用與BDNF含量改變之間的相關性進行了檢測分析,發現經過治療后治療組BDNF濃度明顯增加,且隨著治療的延長濃度增加的趨勢更明顯。同時對HAMD評分與BDNF含量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隨著BDNF濃度增加患者HAMD評分逐漸減少,且趨勢一致,兩者呈負相關,這說明神經復元方改善PSD抑郁狀態可能通過上調BDNF進行介導,這可能是其療效機制之一。下一步需通過動物和細胞實驗更加深入的研究神經復元方的作用機制。
結 果






討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