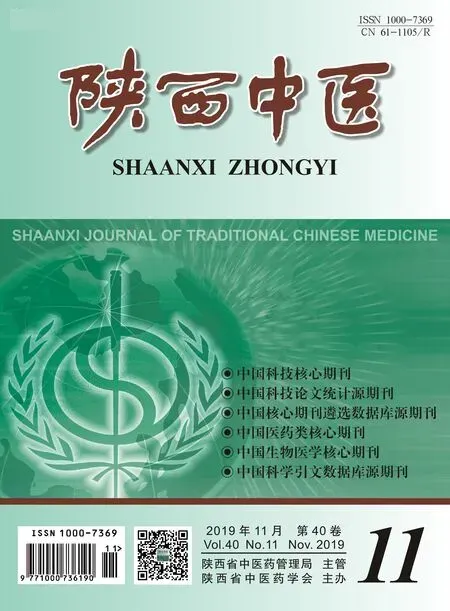四川文氏皮科流派協定方治療慢性濕瘡臨床研究*
譚 強,肖 敏,余倩穎,尤雯麗,雷 晴,陳明嶺△,艾儒棣
1.第四軍醫大學西京皮膚醫院(西安 710032);2.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成都610075);3.青島大學附屬醫院(青島266003)
慢性濕瘡相當于現代醫學慢性濕疹,是皮膚科臨床常見病、多發病,因反復發作及瘙癢,嚴重困擾患者。四川文氏皮科流派為全國首批中醫學術流派建設項目,文氏皮科流派門人在艾儒棣教授帶領下,結合四川地域特點及患者臨床表現,將慢性濕瘡分為濕熱蘊膚證、脾虛濕蘊證及血虛風燥證,運用協定方治療取得滿意療效。
資料和方法
1 一般資料 收集到有效并納入統計患者共277例,這些患者來自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皮膚科門診。納入標準:①年齡在18~60歲之間;②符合《中醫皮膚科常見病診療指南》[1]中慢性濕瘡和趙辨主編《中國臨床皮膚病學》[2]中慢性濕疹的疾病診斷標準;③符合《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3]中慢性濕瘡部分關于濕熱蘊膚證、脾虛濕蘊證、血虛風燥證三種證候中任一證候診斷標準;④簽署經倫理委員會批準的知情同意書。
排除標準:①由藥物引起或懷疑是藥物導致的頑固性濕疹樣皮炎;②近1周內接受了外用糖皮質激素類制劑的治療,或近2周內有使用系統治療藥物;③伴有其他皮膚病,或者其他系統性疾病有皮膚表現者;④伴有嚴重系統性疾病的患者;⑤計劃妊娠或已經妊娠或處于哺乳期的女性,有生育計劃的男性患者;⑥對需要使用的協定方中任何一種中藥過敏的患者;⑦剛剛結束或已報名參加其他臨床研究的患者;⑧研究者判斷有上述情況以外的其他原因,不適合參加本研究的患者。
在277例患者中,有濕熱蘊膚證145例,男82例,女63例;平均年齡(38.46±1.04)歲;平均病程(3.05±0.17)年。脾虛濕蘊證107例,男48例,女59例;平均年齡(43.7±1.23)歲;平均病程(2.54±0.21)年。血虛風燥證25例男14例,女11例;平均年齡(47.12±2.77)歲,平均病程(3.99±0.77)年。
2 治療方法 所有患者均辨證給予中藥口服治療,其中濕熱蘊膚證給予文氏馬齒莧湯(馬齒莧、生地、龍骨、地膚子、磁石各20 g,金銀花、連翹、川射干各15 g,黃芩、紫荊皮、石膏、知母各10 g,生甘草6 g)加減;脾虛濕蘊證給予文氏健脾除濕湯(南沙參、炒白術、馬齒莧、地膚子、石決明、磁石、夏枯草各20 g,茯苓、金銀花、連翹、牡丹皮各15 g,陳皮、川射干各10 g,生甘草6 g)加減;血虛風燥證給予文氏潤燥止癢湯(女貞子、地膚子、磁石、珍珠母各20 g,生地、金銀花、連翹各15 g,墨旱蓮、制首烏、當歸、白蒺藜、牡丹皮各10 g,生甘草6 g)加減。以上中藥為配方顆粒,并由醫院門診中藥房調配,每劑配成三格。1劑/d,100 ml/格/次,3次/d,開水沖泡,飯后半小時溫服。同時給予外用蛇黃膏(院內制劑,包含蛇床子、黃柏等藥物),2次/d。
3 觀察指標 治療前及治療4周后評價皮損面積百分比、濕疹面積及嚴重度指數(Eczema areas and severity index,EASI)評分及瘙癢評分。EASI評分法我們采用趙辨教授改良的評分法[4];瘙癢評分則根據語言評分量表(Verbal rating scale,VRS)[5]評定,研究醫生根據患者的瘙癢程度分別給予0,1,2,3,4分。
4 療效標準 根據治療前及治療后EASI積分評價療效[6]。療效指數=(治療前積分-治療后總積分)/治療前積分×100%。其中療效指數<20%判為無效;療效指數在20%~59%之間為好轉;療效指數在60%~89%之間為顯效;療效指數≥90%為痊愈。顯效率=(痊愈例數+顯效例數)/總例數×100%。
5 統計學方法 應用GraphPad Prism 7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其中計量數據用均數±標準差表示,采用t檢驗;瘙癢評分采用配對秩和檢驗;計數資料采用卡方檢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1 各證候患者治療前后病情評分變化 見表1。濕熱蘊膚證患者治療后皮損面積百分比較治療前明顯下降,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t=11.6,P<0.0001);EASI評分較治療前明顯下降,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t=10.92,P<0.0001);瘙癢評分較治療前亦明顯下降,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001)。脾虛濕蘊證患者治療后皮損面積百分比較治療前明顯下降,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t=11.37,P<0.0001);EASI評分較治療前明顯下降,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t=9.351,P<0.0001);瘙癢評分較治療前有明顯下降,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001)。血虛風燥證患者治療后皮損面積百分比明顯下降,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t=4.686,P<0.0001);EASI評分亦下降明顯,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t=3.85,P=0.0009);瘙癢評分較治療前亦有下降,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001)。

表1 不同證型治療前后病情評分比較
注:各證候治療前后比較,*P<0.01
2 不同證型療效分析 見表2。各證候患者在治療后均以取得顯效以上療效的患者居多,總顯效率達62.8%。各證候之間的療效比較,脾虛濕蘊證患者顯效率最高,達69.2%,濕熱蘊膚證患者顯效率最低,為58%,它們之間的差異經過統計學分析,無統計學意義(χ2=3.339,P=0.188)。
3 各證候回訪情況分析 見表3。我們對取得顯效和痊愈的患者在治療結束后6個月進行電話回訪。其中有部分病例在治療4周結束觀察后,經過進一步治療取得了痊愈的效果;有部分病例在治療結束后會有復發,濕熱蘊膚證復發率高于其他兩種證型;有部分病例因為電話變動等原因失訪,其中濕熱蘊膚證失訪6例,脾虛濕蘊證失訪7例,血虛風燥證失訪1例。各證候間的痊愈和復發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332,P=0.514)。

表2 不同證型療效情況[例(%)]
注:各證候療效比較,P>0.05

表3 各證候回訪情況[例(%)]
注:各證候回訪情況比較,P>0.05
4 不良反應 所有患者在治療觀察期間,均未出現嚴重不良反應。但是濕熱蘊膚證有6例在服藥后出現輕微腹痛,大便偏稀,囑其飯后半小時溫服藥物后癥狀緩解;其余患者未出現其他不良反應。
討 論
慢性濕瘡是皮膚科常見疾病,一般認為屬于血虛風燥證,多給予養血祛風止癢之藥治療,除我們熟知的當歸飲子外,還有養血祛風湯[7]、四物消風飲[8]等方藥。當前慢性濕瘡的治療亦不僅局限于使用養血祛風的治療方法,如周濤等[9]運用清熱利濕方、魏建華等[10]運用健脾除濕飲、潘學東等[11]運用滋陰除濕湯治療慢性濕瘡均取得了滿意療效;除此之外,郭娟莉等[12]研究發現運用紅光配合外用藥治療慢性濕疹亦有較滿意效果。四川文氏皮科流派認為慢性濕瘡的病因病機,除了日久血虛陰虧致風燥以外,還包含了脾腎不足、濕邪蘊積、毒邪內生等三方面,并認為慢性濕瘡的常見證候為濕熱蘊膚證、脾虛濕蘊證、血虛風燥證,分別給予協定方文氏馬齒莧湯、文氏健脾除濕湯及文氏潤燥止癢湯治療。
文氏馬齒莧湯中取馬齒莧、黃芩兩藥共為君藥;一方面馬齒莧能清熱解毒利濕、涼血消腫,另一方面黃芩不僅能清熱燥濕,還能瀉火解毒,且兼具涼血消腫,二者合用能清熱除濕解毒,故共為君藥。金銀花、連翹同為“瘡家圣藥”,有疏散風熱,清熱解毒之功,常用于熱毒性疾病的治療;生地黃清熱涼血止血,射干清熱解毒、祛痰,二者合用重在清解熱毒;石膏清熱瀉火,并且經過煅制后還能收濕斂瘡,可治療三焦、皮膚、腸胃之熱,知母亦能清熱瀉火,石膏、知母合用能解中焦熱毒熾盛,水濕之氣泛溢肌膚之病。以上金銀花、連翹、生地黃、射干、石膏、知母六藥,既能疏散在表之風熱,還能清解在里之血熱,同時直折中焦火熱,均有解毒之效,共為臣藥。紫荊皮能活血、解毒、通淋,能促進皮膚愈合,我們取“以皮治皮”之意,常用來治療濕熱毒盛之瘙癢性皮膚病;地膚子清熱利濕,祛風止癢,可治療皮膚之熱和各種惡瘡,也適用于皮膚有風者,因此地膚子為風疹、濕疹等皮膚病常用之藥,與紫荊皮合用,共奏除濕止癢之效。龍骨、磁石二藥均有鎮心安神之效,因濕瘡患者瘙癢難耐,易于煩躁,加之濕熱之邪熏蒸,熱擾心神,因此給予二藥鎮靜安神,如此則神安而癢止。以上紫荊皮、地膚子、龍骨、磁石四藥配合,重在止癢以治標,共為佐藥。生甘草不僅作為使藥,還有清熱解毒之效。全方在清熱除濕的同時,還主要體現了中醫學“給邪以出路”的思想,予銀花、連翹疏風清熱之品,使邪從上從表而去;并取紫荊皮、地膚子利尿、除濕,導體內濕熱之邪從小便而去,如此上下表里同治,使濕邪無所蘊積,共同促進病邪的祛除。因此,全方合用,共奏清熱除濕、解毒止癢之效,切合慢性濕瘡濕熱蘊膚證的病因病機。現代研究也證實,方中多種藥物可用來治療濕疹皮炎類疾病:如胡一梅等[13]研究發現,馬齒莧提取物可降低濕疹炎癥因子和瘙癢相關因子達到治療濕疹作用;黃芩的提取物黃芩苷有很好的抑制變態反應的作用,并被制成了黃芩苷滴丸用于臨床,景濤等[14]報道其可以治療特應性皮炎;孟子琦等[15]研究發現地膚子可能通過下調IL-2、IL-6、IL-10的表達,達到治療濕疹的目的。
文氏健脾除濕湯則體現了中醫學“扶正祛邪”的思想。扶正以健脾為主,我們選用異功散,它由南沙參、茯苓、炒白術、陳皮、甘草五味藥物組成,有健脾益氣除濕之效,重在恢復脾之運化功能,以奏祛濕之源。在祛邪方面,予銀花、連翹疏風清熱,除祛風透邪之外,還取“風能勝濕”之意;馬齒莧、射干清熱除濕解毒,牡丹皮清熱涼血散瘀,既取其“散結聚,除血熱”之功,也取“以皮治皮”之意,結合地膚子,四藥共奏清熱解毒止癢之功;同時因為本證候患者與濕熱蘊膚證一樣瘙癢明顯,日久擾及神明,故予石決明、磁石鎮靜安神;夏枯草能清熱消腫散結,合牡丹皮功在消腫散結,對慢性濕瘡紅斑、腫脹或斑塊效佳;甘草益氣、解毒,調和諸藥為使。全方合用,補瀉兼施,具有健脾除濕、解毒止癢之功,故可用于慢性濕瘡脾虛濕蘊證的治療。雖然異功散以補益為主,現代研究證實沙參、茯苓、白術、陳皮等藥有調節免疫、抗炎作用,可能通過促進IFN-γ逐漸恢復達到治療作用[16-19]。
文氏潤燥止癢湯主要用于血虛風燥證的治療,方中制首烏補肝腎、益精血;當歸補血活血,為“血中要藥”,且能治療皮膚中的寒熱之氣,對各種瘡瘍、金創外傷都有奇效,與制首烏共為君藥。女貞子補肝腎,強腰膝,能養陰氣,平陰火,能夠針對陰虛患者解煩熱骨蒸,止虛汗,故該藥常用于腎陰不足的治療;墨旱蓮亦能補腎益陰,與女貞子合用,即為二至丸;我們選用此二味藥物,一是考慮慢性濕瘡的發生與腎陰不足相關;二是考慮精血同源,血屬陰,對于血虛風燥證患者可以補腎陰以養血;三是該藥平補腎陰,補而不膩,不像熟地、黃精滋膩,易礙阻脾胃,滋生濕邪;四是二藥藥性平和,不溫不燥,且能涼血止血,不致血燥更甚。丹皮、生地黃均能清熱涼血解毒,且丹皮能散瘀,生地黃能生津,合用化瘀散結而不耗血動血。以上女貞子、墨旱蓮、丹皮、生地四藥,滋陰養血,其性甘寒而止其血燥,共為臣藥。銀花、連翹疏表散風,去膚燥瘙癢之風,兼解燥毒;蒺藜解郁祛風止癢,合地膚子共奏祛風止癢之功;磁石、珍珠母鎮靜安神止癢;此六藥合用共祛內外之風,為佐藥。甘草一方面可清熱解毒,另一方面調和諸藥為使。本方配伍之妙,在于以補腎陰、補腎精之法為主,選用制首烏、生地、女貞子、墨旱蓮等藥物,正所謂“精血同源”,以補腎達到養血潤燥的目的。此類藥物補腎滋陰養血,藥性平和,不溫不燥不膩,無化燥助熱生風之虞,對于慢性濕瘡屬血虛風燥者最為適宜。
因此,從表1可以看到,三種證候的患者在治療后皮損面積百分比、EASI評分及瘙癢評分均得到了明顯下降,治療前后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提示3個協定方均能顯著改善患者病情。從表2可以看到,在治療4周后,所有患者的總體顯效率達到62.8%,各證候之間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且通過回訪發現,部分患者在觀察4周結束后雖然沒有取得痊愈效果,但是經過后續治療取得了痊愈,提示我們濕疹患者通過更長時間的治療,可以提高疾病的痊愈率,并使疾病得到鞏固,且未見明顯不良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