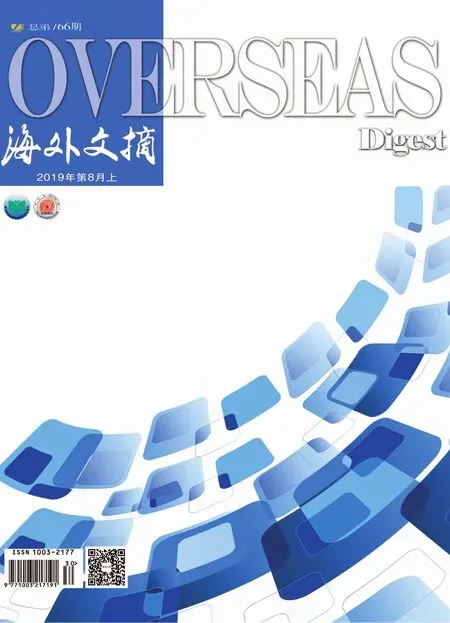日本低欲望社會現象探究
張荷
(天津工業大學,天津 300380)
1 “低欲望”的含義
“低欲望”一詞最早出現于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的《新國富論——胸無大志的時代》中。所謂“低欲望”傾向,并不僅僅只是經濟學家所分析的一種經濟現象,而是可以說得上是一種體現于日本各方面的社會現象。其實大前研一在其2009年的作品《再起動、職場絕對生存手冊》一書中也早已提到過,消費經濟的低迷加速了低欲望社會的形成。現在的日本年輕人和過去年輕人的行為模式大相徑庭,并且擁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對于“擁有物質”毫無欲望,連出人頭地的欲望也比先前世代大幅度降低,不再像父輩那樣做一個踏踏實實的“企業戰士”,犧牲掉自己的家庭幸福,為企業做奉獻。他將其稱“喪失物欲和成功欲,極儉生活的世代”。
作為社會主體的新一代年輕人喪失進取心,對各種事物缺乏欲望,遠離潮流時尚與名牌、遠離買車買房,甚至遠離戀愛與婚姻。不想因結婚生子而增加自己的負擔、不想因背負車房貸款而苦惱一生,這些想法越來越深地盤踞在年輕人的腦海中,導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欲望萎縮,不斷向“低欲望”狀態發展。
2 “低欲望”一代的消費觀和生活方式
人口減少、超高齡化、少子化……日本所面臨的這些社會現實問題超前于其他國家,不僅如此,低欲望社會也是日本相比于世界上其他國家較早出現的社會現象。象征“低欲望社會”的顯著現象之一,就是雖然銀行貸款超低利率,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及中堅世代也毫無反應。對于大多數年輕而人來說,向銀行申請二三十年的購房貸款,人生就類似于“輸在起跑線上”,從“負債幾千萬日元”開始。超低利率房貸無人問津的背后是20、30世代“不想承擔責任”、“不想有責任”、“不想增加自我責任”的思想。這個前所未有的族群,可以說使日本的消費層面元氣大傷,很有可能無法成為新大陸時代的經濟支柱。
細觀日本現況,在泡沫經濟破滅后,從1990 年代到2000年代經歷了“失落的二十年,”經濟狀況持續低迷。不管多么努力也很難獲得加薪或晉升,即使獲得升遷也只是窮忙而已。因此將“貧窮卻充實”當成個人生活風格就成了無可厚非的事情。最新數據表明:2012年度“尼特族(NEET族)”再創歷史新高,達63萬人,占同齡人總數的2.3%;“飛特族(freeter)”多達180萬人,占同齡人總數的6.6%[據內閣府2013年版『子ども? 若者白 書』]。2010年、2016年日本內閣府針對15-39歲“繭居”者的調查結果分別為70萬和54萬。飛特族或尼特族的出現也很可能與便利店的普及密切相關。便利店創造出一天的飲食消費大概只需1000日元就能解決生計問題的社會,即便不工作也不會有被餓死的危險。這種生存條件變低,貌似走投無路也能活下去的社會,如果對房子、汽車、時尚潮流等物品不抱任何欲望的話,很容易就會喪失生產生活的驅動力成為“低欲望”一族。
3 “低欲望”年輕人受到泡沫經濟世代的影響
現在的日本年輕人之所以抱著低欲望的心態生活,一方面不可忽視的原因是受到其父母人生經歷和生活狀態的影響。這些人的父母剛好是泡沫經濟的世代,為了滿足自己的物欲、占有欲以及想要出人頭地的欲望拼命地工作,但是在他們眼中所看到的卻只是父母“庸俗”的一面。
松田久一將泡沫經濟一代不同于其他年代人的顯著特征——“上進意識(climbers)、他人意識(considers)、競爭意識(contenders)、自卑感(confused)”歸納為“4C”。和其他年代的人相比,泡沫經濟一代喜歡在社會上立足,向往明治時期盛行的“出人頭地”。雖然表面上過著有序性的富足的生活,實際上卻背負著房貸的巨大壓力。只埋頭于工作的父親為了出人頭地并不關心自己的家庭責任,不考慮自己與妻子、孩子之間的家庭關系。而現在的日本“低欲望”一代的年輕人受此影響,長大之后并不想再認同父輩那套“用工作和奉獻體現價值”的價值觀。所以也不再想變成那樣的人,故此選擇降低欲望悠閑地生活。他們更重視自身的想法和內心的感受,逃避社交,討厭競爭,從而產生了“低欲望”的心理特征。
4 日本教育制度與“低欲望”
目前在日本尼特族、繭居族、單身寄生族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周刊雜志》也以專題系列報道了“小孩不工作,不結婚,不出門”的問題。年輕世代會如此“向內、向下、向后”(意指個性內向,向下沉淪,后退消極),這些“低欲望”現象的背后原因與日本的教育制度是緊密相關的。日本教育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處于“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時代,以培養的整齊劃一的人才為目標。
產業能率大學綜合研究所于6月19日發表了“2019年度新員工的公司生活調查”的結果。這個調查從1990年度開始每年進行,這次已經是第30次。這次,在調查對象當中,回答“對于把某個地位當成目標這件事不感興趣”的人占42.7%,是這10年間最高的。他們完全沒有想要成為高層管理者的野心,相較于在工作中出人頭地,他們更愿意安安穩穩過自己的生活,保持“小確幸”的生活態度。而改變這一狀態讓日本社會及企業恢復朝氣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徹底改變這種均一教育的模式。事實上,培養一流杰出人才的教育模式,日本早就用在了音樂和運動領域。總之,普通的教育課程教育課程也要像日本的運動和音樂一樣,不能只是依照文部科學省的指導大綱讓所有孩子接受一律平等的教育,對于有天賦潛力的還在應施以“英才教育”。
5 如何看待國內年輕人的“低欲望”現象
如今,低欲望社會似乎“飄洋過海”來到了我們身邊,其典型表現就是是喪文化的蔓延。從火爆網絡的表情包“葛優躺”,到風靡一時的手機游戲《旅行青蛙》,再到“佛系”一詞的流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給自己打上了“喪”的烙印。他們用著各種喪氣的表情包,說著各種調侃的流行語,表達著頹廢、自嘲的消極情緒。但在我國的社會背景和教育體制下,在國家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氛圍里,這種“低欲望”與日本有著截然不同的含義。
因為在我國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新時代的“四大發明”——高鐵、支付寶、共享單車、網購已經滲透到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VR技術、自動駕駛等新興科技名詞還在源源不斷的產生。這些技術在豐富和方便我們生活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不確定。其中影響較大的是職業前途的不確定。科技迅猛發展導致職業快速更迭,曾經的熱門職業轉眼可能就成了夕陽行業。職業的不確定意味著生活的不安穩,進而會導致心理上的焦慮。人們在這種“不確定”的氛圍中變得被動茫然,缺乏安全感和歸屬感。
于是,人們將價值關注點從外部世界逐漸轉入內部世界,滿足當下幸福的“小確幸”成了更多人的精神安慰和支撐。所以低欲望并不等于頹廢、放棄,目前我國年輕人所展示出的“低欲望”其實是他們達到認知協調的一種手段。比如抖音、快手等直播平臺的流行,其實隱喻著人們在適應科技爆炸帶來的被動與茫然——那就是通過降低欲望,用淺薄、輕松的自我表達,提醒著自己人生仍然需要樂趣和創新,需要朝氣蓬勃努力奮斗。所以我們應該極力避免盲目效仿日本的“低欲望”狀況,應該理解我國年輕人所表現出的“低欲望”或“佛系”其實質是一種面對挫折與困難的處世態度,是一聲對無奈境遇不妥協的吶喊。它本質上更像是一種假象,雖然我們自嘲、悲嘆,但并不妨礙內心對美好生活的憧憬與向往;雖然我們畏懼、跟風,但并不會阻礙在行動上對幸福人生的拼搏與追求。我國新時代年輕人的生活其實是,嘴上說“喪”,心態較“佛”,行動很“燃”,他們依然在腳踏實地砥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