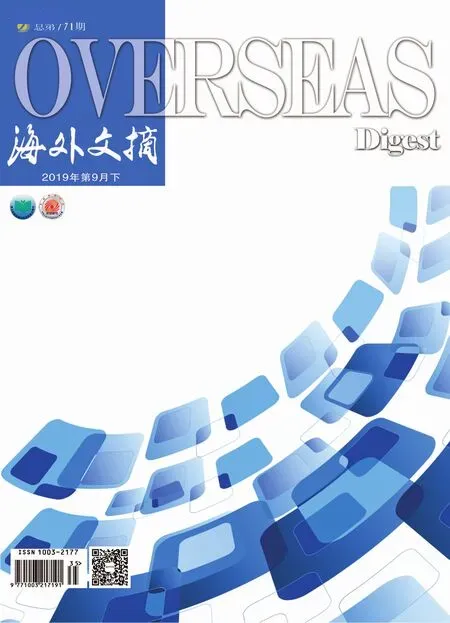朝鮮殖民地時期新女性文學的研究
隋寧 李燕 李靜晗 王明梅 韓夢
(聊城大學,山東聊城 252000)
1 知識分子和知識
在韓國,最初提及到有關知識分子的問題是殖民統治時期。接受著殖民國家的教育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們,他們所學知識不僅沒在提升身份或賺取金錢上的有所幫助,反而變成負擔,只能屈辱的活著。女性的情況更加糟糕。在傳統認知上,知識被認為具有女性屬性的因素,人們都戴著有色眼鏡看待女性,在女性接受教育的事件上更是持極度否定的態度。 在傳統保守的社會中,一直被蔑視智慧的女性,在知識只能預示不幸的殖民地時期開始學習。保守勢力早已將近代化視為挑戰,在這樣的情況下,接受教育的女性很難得到社會的認可。因為近代化的矛盾和與殖民地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社會對女性知識分子持否定看法。而且,新女性們主張的男女平等、女權、女性解放等問題,對家長體制來說是巨大的挑戰。
2 寫作——選擇和賦予意義的工作
寫作是一件難事。從圍繞我們的世界眾多事物中分離出一個,給予關注,賦予對象特別的意義,說服讀者的工作絕非易事,作者在寫作品時,從眾多素材中找出一個,賦予它自己獨特的主題意識,并以有效的方式重新構思文學世界,因此作家的工作具有重要意義。此時的寫作領域中對新女性的偏見在同為知識分子的作家中也是一樣的。因為是同一時代的作家,所以在可能形成同質感的情況下,男性作家們大多投身于自己固有領域,受教育的知識分子發表詩或小說的情況較多。不僅如此,女性作家們也常常以男性為中心,以傳統尺度看待自己所屬的階層。初創期新女性們認識到了這種歪曲的視角的不合理性,她們團結起來,為糾正男性作家的偏見而做出了努力,這形了對新女性進行細致觀察和寫作的方式。
3 女性作家——作為新女性對女性生活的考察寫作
這時,已婚和單身這兩類人在生活上有很大的不同。已婚者如禽獸一般,“乞求別人賺的米,乞求別人吃剩下的飯”;而單身的人自食其力,自給自足。作者認為,雖然這兩種極端不同的生活態度存在很大的問題,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婚后尋求女性社會地位的認同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果她想要被社會認同而選擇獨居的話,在當時那個禁止女性獨立的社會,她會受到經濟上的問題、社會的壓力和侮辱。
在殖民地統治下,作為初級知識分子,女性能夠用文字表達的是生活與知識之間的聯系,是即將被新認識的女性生活問題,是橫亙在自己面前的女性解放問題。當男作家們把女作家們的文章看成有性傾向,膚淺的寫作上時,女作家們卻在探索并解剖深層的女性問題,用文字來表達她們對女性解放問題的思考。伊利耶伊說:“因為女性在自己心中是毫無窮酸感的擊球手,有時會變得神經質,不得要領,容易動搖,因此,關于女性的寫作只能通過女性得到凈化。”
女作家的“關于新女性的寫作”,無論是從苦惱的表現手法還是主張來看,都區別于領先性的“男性的寫作”。但也有女作家對新女性進行歪曲的情況,這是因為她們從自己一直受到教育的男性的角度看待新女性。
4 知識分子的寫作態度分析
在殖民地統治下,知識分子所表達的“認知”僅限于“當代社會的表面現象”。因此,作家們比起民族或國家至上的問題,更傾向于自己身邊的小問題。作為其中的一環,新知識人士逐漸開始關心女性。男性作家們創作了很多以新女性為原型的作品,這也體現了當時社會知識分子對女性的關心程度。但是,在當時保守封建的社會,新女性仍是社會批判的對象,以迎合社會的文筆寫作,絲毫不表露對女性的關心,那只是知識分子們的所屬群體的意識形態,保守傾向的表達而已,根本看不到作為知識分子的進步趨勢。
對于否定新女性的情況,男性作家們一致表現出紊亂的現象。這種現象千篇一律,可見是想用純潔意識形態這一當時最高價值的規則來裁剪和否定新女性。而且知識分子女性也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這種純潔至上的價值觀,通過男性作家認可的新女性形象表現出來。他們都受惠于新教育和新思想,卻未能擺脫強調精神、肉體上純潔等傳統習俗的框架,無法自覺實現自己在生活中的主體性,雖然是知識分子,但無法達到先覺者的目的,是一種偏離的形象。可以說,在當時的作品中,頻繁地產生的這種女性形象,是使女性學習變得毫無意義的時代意識形態的產物。這是通過默認或明示的學習后天獲得的傾向的體制,也是發生性構圖的系統。
30年代的作家們以近代的教養和思維方式武裝自己。作為認識的主體,他們對第一代人進行反省,對當代現實進行科學合理的判斷。盡管如此,他們的作品相比于第一代作家,在女性氣質方面似乎有所退步,原因何在?其一,第一代女性受到象征暴力的影響,向后一代女性作家證明了存在家長意識形態壁壘的事實。在崔貞姬作家描繪已婚女性的作品《三脈》和姜京愛作家的作品中寫道,女性可以安于家務。文中,放棄了沒有愛情的婚姻、想要和相愛的人復合的善英,為了孩子而再婚的妍,和初戀求婚的恩英等人,歸根到底都沒能擺脫母性情結。善英想通過孩子看到許允尚的樣子,所采取的是在不拋棄家庭的情況下,可以最小限度地向現實妥協的方式;妍放棄再婚的家庭前往孤兒院,乍一看好像是離家出走的行為,實則她放棄了自己的生活,選擇了只為孩子著想,所以結果還是完全被母性情結所壓倒。作家們強調對離婚者或寡婦的象征性暴力也是出于這樣的原因。在《地脈》這一作品中,善英成為寡婦,為生計發愁;像芙蓉這種離家出走的女人,只能在冷酷的社會現實面前孤獨地生活著。善英決心以被搶走孩子的芙蓉和母親離開后彷徨的河順為教訓,勇敢守護自己的家。作家們一味強調女性的性,強調母性、生殖,這說明他們的寫作理由是基于維護“家”的這一目的和意識。開化期以后,以基督教為中心的女性教育與家長制相結合,強調古典的母愛,女性作家們信奉了這種思想。不僅如此,30年代的女性作家將此作為對抗時代外壓的思想武器,贊同這種被稱為進步和改革的政治理念的背井離鄉的社會主義。因此,對于她們來說,女性問題不可能比階級意識更先進。日本的“皇國女性、徹底服從型女性形象”也強調女性的母性,讓女性把主體覺悟轉移到了后頭,結果女性作家們只能被家人和母性意識形態所壓倒。
5 關于新女性的寫作批評
以上是對殖民地時期知識分子作家們有關新女性的寫作形式的觀察。關于殖民地統治下的知識分子女性、新女性的寫作,可以成為作家更客觀地觀察自己所屬的階層、預測未來的最佳工具。在殖民地統治下,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很嚴重,尤其是女性知識分子的情況,更是如此。因為知識分子必須經歷時代的痛苦,再加上近代化的矛盾,所以才會如此。
男性作家們把新女性人物刻畫成雖然受惠于新教育但未能擺脫傳統習俗的人物,是沒有自覺,只追求表面膚淺之物的人物。在當時的作品中經常出現的這種女性形象,是時代意識形態的產物,即女性的學習沒有任何意義。女性只有在家時才是有價值的存在,可以說是對當時積極的新女性的大力反擊。他們把新女性描繪成對時代進步毫無用處的存在后,新女性形象開始被歪曲。
如果說男作家們是處在男性支配性社會的守舊立場,以譴責或引導新女性的姿態進行寫作的話,女作家們則不得不忍受長期滲入的傳統女性觀之間的分裂傾向而堅持寫作。所學和新學的東西,都被傳統的女性觀歪曲,和對自己新創造的新女性形象的苦惱等等,這些促使了她們的寫作。從先驅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雖然她們在努力打破這種對新女性固定的認識,但之后很難繼承,只有歪曲新女性的文本被積極流通和消費。這與過去流通的主體是男性的文學狀況有關。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也可以積極流通、消費的今天,關于新女性的寫作可能需要重新嘗試和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