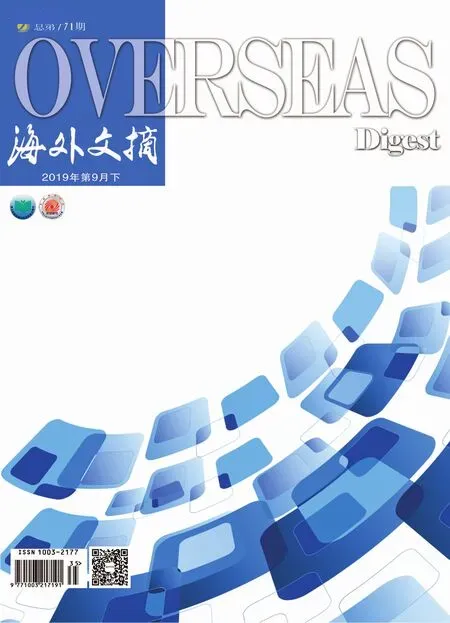法律規制與路徑探尋
——人民調解協議司法確認制度之優化
楊夢馨
(浙江省臺州市三門縣人民法院,浙江臺州 317100)
當前我國的法制環境和司法確認制度本身均存在著制約其發展的瓶頸因素。為進一步實現司法確認制度在分流案件、消弭糾紛方面的突出功能,本文擬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結合當前我國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剖析司法確認程序存續的必要性,反觀其在司法實踐中的運行困境,探求司法確認制度的優化路徑,以期對該制度的理解、運用和完善有所裨益。
1 司法確認制度之必要探究
自身優勢:司法確認書正當性的實質來源為當事人對可自主處分權利的意思自治,只要人民調解協議在內容和形式上不違反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的禁止性規定即為合法。司法確認程序吸收了人民調解經濟性和快捷性優勢的同時加注了訴訟的確定性和強制性保障,促使更多民事糾紛當事人趨向選擇以人民調解的方式來解決糾紛,有效地減輕了司法負擔。
比較優勢:人民調解較之其他非訴調解最顯著的優勢就是可以通過司法確認程序獲得強制執行力。其次,人民調解的工作范圍更接近民事訴訟的受案范圍。
人民調解較之訴訟更具成本優勢,其收取任何費用,司法確認案件也不收取任何費用,降低了當事人的維權成本。其次,過程較之訴訟都更具便利優勢,程序簡便快捷且受限少。
2 司法確認制度的現狀檢視
2.1 宏觀層面——程序細則不詳導致陷入運行誤區
2.1.1 程序適用范圍違法擴大
《訴非銜接若干意見》其明確將行政機關、人民調解組織、商事調解組織、行業調解組織或者其他具有調解職能的組織調解達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質的協議全部納入司法確認程序的范圍。但2012年修改的《民訴法》中卻未承認這一開放式設計,而是使用了“人民調解法等法律”和“調解組織”的表述。但實踐中部分基層法院忽視法律位階,以最高院在2015年施行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下稱《民訴法解釋》)及之后的若干文件為由全面放開司法確認程序的適用范圍,違反了《民訴法》對程序適用范圍的限定,降低了司法確認程序的公信力。
2.1.2 實質審查有違非訴本質
無在實踐中部分法院雖然采取書面審查方式,但其在對調解協議的自愿性和合法性進行審查之外,還對調解協議中涉及的雙方當事人實體權利義務進行實質審查。
2.1.3 救濟不明致使程序休眠
(1)當事人救濟渠道欠缺合理性。司法實踐中既存在法院未能及時查明調解協議背后隱藏的真實意愿而作出錯誤的司法確認裁定的現象,也存在當事人對駁回裁定有所不服的情況。由于司法確認裁定存在再訴禁止效力,要消除該效果應當經過再審程序。依據《民訴法解釋》第三百八十條之規定,當事人對司法確認裁定不服的,無法通過申請再審予以救濟,但又未設置專門的救濟程序,導致當事人在權益受損時無法獲得有效救濟。可見,當前立法對兩種不服情況均采取禁止再審的規定有違合理性。
(2)案外人救濟力度明顯不足。近年來,虛假訴訟屢禁不止,調處更為自由的非訴領域同樣難以防治雙方當事人為侵害他人權益進行的惡意調解。司法確認制度的設立為人民調解協議提供了強制力的保障,使得部分有損他人權益的調解協議披上了“合法”外衣。而對案外人的救濟力度卻明顯不足。
2.2 微觀層面——協作運行不暢導致程序效果不佳
2.2.1 法官角度:制度局限下的“理性”選擇
法官在面對“有瑕疵”但未達到不予確認標準的人民調解協議時無法可依,況且確認人民調解協議效力的裁判文書不屬于上網公開范圍,法官對哪些情形下確認有效、確認部分無效或確認全部無效時缺乏一致性的引導,讓法官們分別走向了實質審查和敷衍了事兩個極端。再者,司法確認案件在各基層法院的業績考評中占比遠低于民事一審案件,除卻此類案件數量較少的原因之外,與司法確認案件被誤當成簡單的小微案件有很大關聯。因此,在制度內因和考核外因的雙重制約下,法官極易傾向于將其引入訴訟調解環節或對調解協議進行實質審查的誤區。
2.2.2 當事人角度:理念指引下的“無奈”選擇
在立案登記制為當事人敞開了訴訟大門的現實背景下,司法確認程序的救濟渠道尚未完善,讓專業性更強的法官通過嚴格的審查程序調處糾紛成為群眾的首選。這一局面是司法確認制度自身不足的無奈之選。
司法確認程序啟動需雙方當事人共同申請的規定,無形中提高了司法確認的門檻,為一方當事人的反悔留下來極大的空間,降低了人民調解協議獲得強制執行力的可能性。
2.2.3 人民調解員角度:博弈困局下的“利益”選擇
人民調解所針對的糾紛類型日益復雜,但部分人民調解員的文化程度、法律素養及調解工作技能還難以適應新形勢下人民調解工作的需要。面對是否告知并協助當事人申請司法確認這點上,人民調解員們更陷入了一種博弈困局:一方面他們深知人民調解協議本身缺乏強制力保障,當事人極易事后反悔;另一方面,由于部分調解員對司法確認制度的意義及具體程序規則還不熟知,因而無法及時告知當事人共同申請法院司法確認。再者,部分調解協議內容存在瑕疵甚至違反法律規定,若當事人申請司法確認也很難通過審查,反倒會給自身帶來補充相關證明材料等附加工作,多項因素的累加使得人民調解員有選擇性地告知當事人提交確認申請。
3 司法確認制度的優化路徑
3.1 立法引領,理性矯正實踐誤區
3.1.1 調整程序的申請方式
建議將申請方式放寬至“一方提出,另一方書面同意”,或者在人民調解協議簽訂時由雙方當事人共同委托人民調解組織向法院提交申請。筆者認為應盡快調整司法確認程序的申請方式,減少一方當事人隨意反悔現象的發生。
3.1.2 規范程序的審查內容
在基本法層面對實體審查作禁止性規定,并就司法審查的具體內容在司法解釋層面對主體資格及調解依據予以實質性規定。審查主體資格時,除了對雙方當事人及人民調解員資質審查外,還應對當事人行為能力、調解是否當場進行予以核實;審查調解依據時,以法律審查為主,事實審查為輔的原則,避免介入對事實的審查和認定。
3.1.3 縮限程序的適用范圍
應及時明文廢止與之相沖突的司法解釋,并在基本法層面對程序的適用范圍予以明確規定,通過提高立法層級的方式對程序適用范圍進行有效規制。
3.2 完善程序,再造新型救濟模式
3.2.1 適當補足當事人救濟方式
實踐中,涉及當事人權益救濟的主要為以下兩種情形:(1)當事人對確認裁定不服的;(2)當事人對駁回裁定不服的。針對確認裁定的救濟,多起因于調解協議達成時當事人意思表示存在重大誤解或顯失公平等情形,筆者認為此種情形下應允許當事人向原審法院申訴請求撤銷錯誤裁定,在錯誤裁定撤銷時再向法院進行起訴,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對于消極的駁回裁定而言,筆者認為需要增加再審的救濟途徑,在《民訴法》第二百零一條中“當事人對已經法神國法律效力的調解書”后附加“及司法確認裁定書”,以此補足當事人的救濟方式。
3.2.2 拓展案外人救濟途徑
現行法律及司法解釋為案外人構建的救濟程序筆者已在前文予以論述,但在實踐中卻無法切實保障司法確認程序中案外人的權益,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在現有的救濟程序基礎上加以補充完善,具體做法如下:(1)引入審判委員會作為案外人異議成立與否的具體審查者;(2)若案外人有實體訴求的,由審委會決定轉入訴訟程序,并將撤銷請求與實體請求進行合并審理。
3.3 明確職責:探索建立協作機制
3.3.1 法院:“內部調整+外部指導”
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規定哪些瑕疵可以由法院向當事人釋明后予以矯正,如涉及文字表述、調解依據及履行約定等瑕疵。對司法確認程序中發現的問題要及時反饋至調解組織,助推調解協議質量提升。另外,基層法院應加強對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進行業務指導,必要時可組織法官對人民調解員開展專業培訓。
3.3.2 人民調解組織:“內部規范+外部反饋”
針對人民調解協議的規范性問題,應確立調解協議的省域模板,以減少調解協議中法律性瑕疵,減輕司法審查負擔,提高司法確認通過率。人民調解組織還應在現有的受理程序下嵌入司法確認程序告知與釋明環節,在調解協議達成后,針對當場履行且符合司法確認范圍的協議當事人進行告知。可主動對接法院,暢通線上司法確認程序申請,實現當事人調解后司法確認“零次跑”。
司法確認制度作為我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迄今為止唯一獲得全國性立法確認的成果,在有效指導人民調解工作、推進訴調銜接機制完善及基層治理等方面發揮了多重功效,其發展前景不容小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