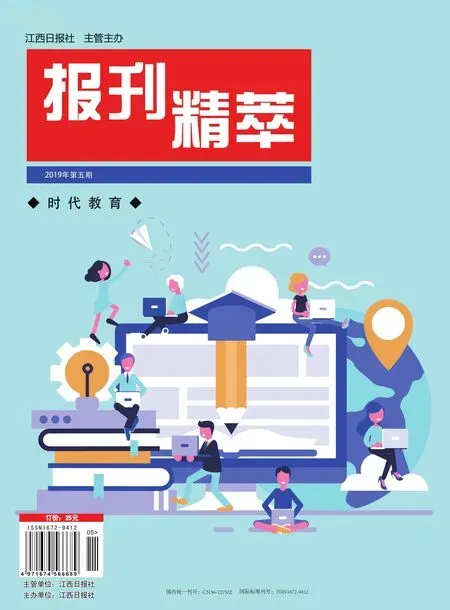亂世行走 至善一人
——對歷史人物鮮英的解讀
羅發義
四川旅游學校
一、處亂世獨善其身 隨本心忠恕守仁
1、追隨張瀾,投軍效國,相助中共
鮮英(1885—1968),西充縣太平鎮鮮家溝人。鮮英的家鄉西充自古以來便是王道教化之地,儒釋道三教并存,佛寺林立,學宮閭巷,道韻悠然。鄉人尚武習文,民風淳樸。這里從來不缺乏走出盆地,沖出四川的偉人與豪杰。“誑楚開漢”、為忠義而獻身的紀信將軍,蜀中孔子、《三國志》作者陳壽的授業恩師譙周,左宗棠帳下驍將、晚清民族英雄徐占彪等皆出生于此。這里也是一塊孕育自由的沃土,近代“布衣圣人”張瀾、“保路先驅”羅綸都是西充子弟。鮮英,幼時家貧,后在親友的資助下進入私塾。1907 年,順慶求學,他與小一歲的儀隴馬鞍人朱德成為張瀾的學生。從此,鮮英與張瀾結下了一生追求民主與自由、甘苦與共、守望相助的師生情緣。
2、創實業,支持革命,心懷天下
1921 年,鮮英36 歲,被川軍總司令劉湘委任為總司令部行營參謀長兼重慶銅元局局長。銅元局本來是鑄幣廠,由于軍閥混戰,急需軍火,加之銅元利薄,1922 年,將銅元局改為子彈廠。銅元局生產的雖然是特殊商品軍火,但在20 世紀20 年代的四川也算是現代企業了。主持銅元局,是鮮英最早接觸實業。再加之軍閥混戰中凋敝的民生現狀,使他深刻地認識到了棄政從商振興民族實業的重要性。1930 年,恩師張瀾因為抗議國民黨壓制思想和學術研究自由,辭職回南充,繼續從事中小學教育。張瀾因痛恨軍閥割據,且不愿意助紂為虐,為當政者不喜。老師的遭遇使他更加堅定了仿陶朱公作一名富家翁、實業救國的念想。1931 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四川善后督辦公署,劉湘看中鮮英的經營和管理天賦,任命他為督署參贊兼惠民兵工廠廠長。此期,沉浮多年的鮮英終于在重慶上清寺建起了私宅1 處,以其號而命名“特園”。此后,“嘉陵江上的巨人”張瀾先生應鮮英之邀入住特園。一師一友的兩個西充人,在重慶下起了一盤左右中國命運的大棋。
二、靖國難倡民主,重慶特園大放異彩
1、創辦“特園”,民主之家,光明在望
重慶特園始建于1929 年,由其夫人金竹生經年累月建成。據鮮氏后人鮮述秀說,鮮夫人金竹生多年來一直用煤渣打成煤磚出售,修建房屋出租積累資本,個中辛酸,實為充國女中模范。1938 年底,董必武陪周恩來拜訪鮮英。當時在國民黨的政治高壓下,為避免麻煩很多人不愿與共產黨接觸,更不敢給共產黨提供活動場所。因此,周恩來旁敲側擊探問鮮英的態度,沒想到鮮英坦然回答說一愿意,二不怕。此后,鮮家私宅“特園”便成為中共南方局和八路軍駐渝辦事處活動的主要場地,社會賢達、進步人士開始頻頻出入。有了鮮英的支持,“特園”成了真正的“民主之家”。中共方面的人、國民黨左派、地方軍政要員、社會賢達人士如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王若飛、鄧穎超、郭沫若、沈鈞儒、李公樸、陶行知、黃炎培、柳亞子、馮玉祥、李濟深、史良、章伯鈞、梁漱溟、鄧初民、朱蘊山,經常匯聚一堂,共商國是。抗戰期間,荷蘭大使館、蘇聯軍事代表團以及盟軍軍事代表團等機構都曾借駐于此,而民盟的總部在還都南京前一直設在特園,鮮英本人則擔任民盟中央執行委員兼重慶支部主任委員。
2、支持民運,策反楊森,守護山城
鮮英雖人在商海,但也一直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關注和支持民主運動,包括出資支助民主活動、營救被捕民主人士等。1946 年5 月,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在即,重慶各界人士100 余人舉行時事座談會,鮮英與羅隆基、史良、鄧初民等90 人發表宣言和發起簽名,呼吁和平,反對內戰。李聞血案發生后,重慶各界6000 余人在青年館舉行追悼大會。在“民族之魂”四個大字下,須發蒼蒼的鮮英凄哀悲痛地朗誦祭文,沉痛悼念在昆明為民主殉難的民盟同志。1947 年6 月1 日深夜,重慶國民黨當局出動大批軍警憲特,對進步人士進行大搜捕,一時間數百名進步人士身陷囹圄。“六一事件”中,民盟總部機關報《民主報》被捕的記者、編輯和其他工作人員及印刷廠工人多達30 余人,鮮英緊急召集工作人員商討對策。鮮英通過梁漱溟先生出面,在《大公報》發表公開聲明,呼吁當局立即釋放非法逮捕之‘民主報’全體員工。事后統計,《民主報》被釋放員工中就有近10 人是中共地下黨員。
三、一生大度乃從容,舍家為國又何妨
1、仗義疏財,家風謹嚴,勤儉持家
抗戰最緊要的關頭,重慶作為國民政府的陪都,來自淪陷區的抗戰激進分子、民主人士、國民黨要員、社會名流得知重慶“特園”主人古道熱腸,待人接物優禮有加,紛紛慕名而來。據許多社會名流回憶,當年貴客盈門,車水馬龍,堪稱盛況空前。“特園”經常是“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金竹生女士回憶說:“當年每天在特園用餐的人很多,最多時上千人。全天開‘流水席’,隨到隨吃。”那時吃飯,米是從南充用船運下來的,每天都有挑夫絡繹不絕往特園送菜。鮮英還聘請重慶“姑姑筵”的傳人為廚師,提高鮮宅家宴的品位,獨創“鮮味齋”,香飄四溢。鮮英不吝家產,仗義疏財將經營實業的相當一部分所得都投入到了“民主之家”的招待應酬上。深懷感激之情的董必武為特園取了一個名字,叫“民主之家”。大量的開銷也讓女主人金竹生女士常常感到捉襟見肘,但從無怨言。鮮家雖是大戶,但鮮英夫婦卻推崇勤儉節約度日,對子女要求甚嚴,吃飯不能喧嘩,若將飯粒掉在桌上,必須撿起來吃掉。鮮家子女從小沒有零食可吃,為解嘴饞,孩子們就在“特園”各處尋覓,鐵線草、酸莖草都成了零食。因為“民主之家”出入的都是社會名流,金竹生女士對子孫管教嚴格,說話的聲音不能高,不許罵人臟話……金竹生女士還親自參加勞動,她在“特園”空地廣種花草果木,以補充“特園”所需。當時常有衣著光鮮的小姐太太慕名造訪“特園”,問鮮太太在不在家。當金女士從地里站起來回答‘我就是’時,訪客無不驚愕不解。
2、不計得失,從容大度,舍家為國
新中國成立后,作為愛國民主人士,鮮英榮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和首屆全國政協委員,并被推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但“窩藏戰犯眷屬財產”的嫌疑始終緊箍咒一樣伴隨著他,土改、鎮反運動展開后他更加坐立不安。在給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張瀾先生的信中,鮮英坦言:“行情不悉,錯誤實所不免。”后在張瀾的復信鼓勵下,鮮英決定將“特園”內外房產全部捐給國家,然后舉家遷往北京地安門恭儉胡同居住。那是他早年在北海公園附近買下的一座四合院。董必武在重慶市政府呈送的請示中批復:“特園很有紀念意義,要作為紀念館原樣保存。鮮英的一生寫滿了傳奇,但他的事跡卻鮮為人知,對于一位有功德于社會的人,我們應該永遠記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