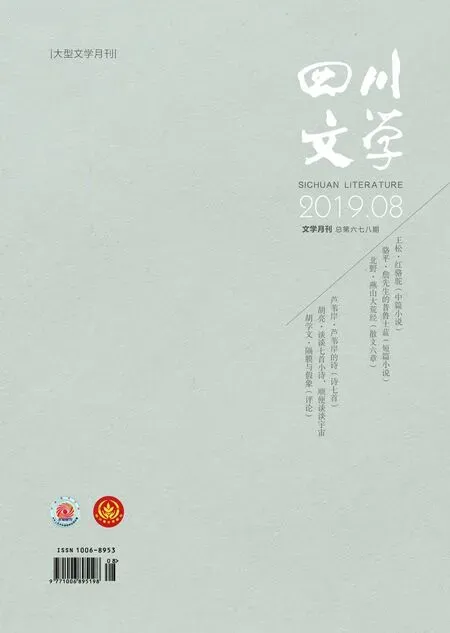路魘
□文/朝顏
鼠尾草已在搖籃中枯萎——
面對新的死者,迷迭香失去了它的芳香——
即使艾草也只有昨天才苦澀。
慰藉的花朵過于微小
不足以補償孩童一滴淚的苦楚。
——奈麗·薩克斯《安慰者的合唱》
一
盤桓在南方的寒氣被春節的熱烈氣息驅散。再過一天,就是一年中最盛大的除夕了。等待和團聚,豐盛的食物和鬧騰的話語,從城市到鄉村,一切都是歡喜、祥和的樣子。
一個父親載著兩個花骨朵一般鮮嫩的女兒去親戚家串門,卻再也沒有回到家里。
206國道,煙汕線,就在他們即將靠近自己無比親切的村莊之時,一輛小汽車從他們身后飛速駛過來,撞上了三人乘坐的電動車。
這一天是2月14日,西方舶來的情人節在這座小城里像傳染病一樣恣肆蔓延。這一天,兜售鮮花的人擠擠挨挨地充斥于街頭巷尾,超市將巧克力擺在最顯眼的位置,餐廳適時地推出了情侶套餐。據說,這一天酒店的大床房早已爆滿。
沒有人能預測前方是否潛藏著災禍,時間中那么多的暗合瞬間從偶然走向必然。誰知道呢,一些原本毫不相關的人,如何就從貌似命定的情節里相遇,然后相殺。開著奧迪小汽車的李生,他完全不知道會有這樣的一個夜晚,會有這樣的人禍發生。他踩著油門以超過安全規定的速度飛奔著,是要匆匆奔赴一個情人節之約,還是僅僅因為一種開快車的慣性,他沒有說。他還那么年輕,24歲,意氣風發,有優裕的家境。他甚至不需要經過自己的努力和打拼,就開上了奧迪車。如果不是剛從看守所押解過來,他應該有比現在更清爽、更帥氣、穿著更得體的樣子。
但是,猛踩的油門和盲目的自信,釀成了一個家庭的滅頂之災,也從此改變了李生的人生軌跡。
受害人的親戚在證詞里回憶著一家三口去他家里做客時的情景。那天晚上,壯年的父親領著兩個年幼的女兒來家里串門,大人小孩歡天喜地,一團和氣。夜晚約八時許,大人們正相談甚歡,小女兒嘉嘉嘟起了小嘴巴,催促著父親說:“爸爸,我想回家,我們快點走吧。”于是,父親止住了話頭,領著兩個女兒出了門。他們與親戚道別,相互說著各種吉祥的祝福。誰知道幾分鐘以后,這個慈愛的父親和兩個撒嬌的孩子,生命戛然而止。
李生在庭審中回憶起那驚魂一幕,似乎仍舊心有余悸:“當時,我與一輛大貨車會車,前面沒有看到任何車輛,視線一覽無余。但是會車后,突然發現前面出現一輛電動車,我一下子蒙了,已經沒有任何反應的余地。我撞上去時,急踩剎車,安全氣囊打開……”
李生的車輛在事故之后進行了速度鑒定,時速在86到94公里之間。顯然,他在遭遇大貨車的時候,并沒有減速,也沒有普通人在面對大車時的警惕和防范。他依舊踩著油門,一路高歌猛進,超速行駛,把開放性的國道當成了高速公路。即使那時候,正在會車,正是夜晚,正是視線最容易出現盲區的時候。
人們通常喜歡把激情和速度這兩個詞語聯系在一起,仿佛充滿了高效的、快捷的、光明的、希望的、創造的力量。但是,速度同時又是一個多么可怕的魔鬼。它像颶風一樣席卷生命,覆蓋心跳和血液中繼續的可能,讓一切光明、希望和創造轟然結束,化為烏有。
有數據顯示,交通事故一半是因為車速過快。當車速超過每小時50英里時,車速每增加10英里,碰撞力就會翻一番,造成致命交通事故的概率也大大上升。也就是說,車速越快,造成當事者不可挽回的死亡概率越高。當車速達到上限時,一旦發生爆胎或碰撞等事故,生還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飛速旋轉的車輪,帶著李生飽嘗了速度和激情的快感,也飽受了恐懼與無力承擔的夢魘。“砰”的一聲巨響,世界天旋地轉。他終于從驚魂中鎮定下來,打開車門,看見一大兩小的三具肉身無序橫陳。鮮血洇紅了他的眼睛,以及整個大腦,整個世界。甚至,還將洇染在他后半生無可逃脫的靈魂里。
他們那樣安靜地躺著,任由熱騰騰的鮮血自體內汩汩地逃跑。他們已無力動彈,甚至連呻吟都發不出一聲。他蹲下身來,卻沒有勇氣去觸碰他們的身體,只是用顫抖的手撥出了急救和報警電話。然后,向父親和所有的親人求助。他乖乖地等在那里,等待著道德的譴責和良心的審判,還有法律的懲罰。這時候,如果有人罵他,打他,他都是愿意接受的。就像小時候做錯了事,低著頭等待老師或父母的責罵,罵過后,他會覺得自己內心的負擔也變輕了。
二
我曾經無數次地領著孩子穿過城市的十字路口,她學著我的樣子,口中念念有詞:“紅燈停,綠燈行……”從小,她那么乖,那么嚴格地踐行著掌握到的那一點點交通安全知識。可是,關于安全,一個人一生中需要掌握和防范的又豈止這些?
現在,她開始自己騎著自行車上學、回家,自如地穿行在大街小巷。她明亮的身體正在向著天地伸展,像一尾投入清水的魚兒,那么暢快,那么自信地游弋著。而我望著她遠去的背影,常常有種莫名的擔憂。我把一個活蹦亂跳的孩子交給紛紜的世界,交給穿梭不停的人流車流,世界會始終對她報以微笑嗎?
她時不時回來吐槽,小汽車的霸氣占道,三輪車的橫沖直撞,摩托車的呼嘯飛馳,常常將騎自行車的學生娃攆得無路可走。她還不忘幽默地戲說一番:“這就叫‘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是的,我們無力更改所面臨的現實,除了教她多一些警覺,寧愿謙讓也不與人爭搶之外,還能怎樣?即便如我,在各種道路上行走了三十多年,面對復雜的路況復雜的他人,似乎也只有退讓一條路可走。
五歲,外婆牽著我的手在馬路邊上慢吞吞地走,一輛自行車擦過來,將我掛倒,哇哇大哭一場;十五歲,我騎著自行車從泥濘的田塍路上歪歪扭扭地走,為了避讓迎面而來的人,跌進水稻田,自己爬起來;二十五歲,我去學校上班,已經到了校門口,一輛摩的風馳電掣地飛奔過來,將我刮傷,沒等我反應過來,對方已揚長而去……
當一個人年紀越大,閱歷日深,經見的險境愈多,也便日漸深懷畏怯。我們知道,并不是每個人都通曉規則,都有心或有能力遵循著規則生活。保護自己,永遠是第一要務。
那時候我還沒有自己的孩子,還在學校做一名教師,我常常依著學校的管理制度教育孩子們,盡量自己走路上下學,不要讓家長來接送,因為校門口實在太擁堵了。然而家長們照樣駕駛著各種交通工具,準時出現在校門口。后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忽然間有了一種靈魂被接通的開悟,我懂得了他們,就像白天突然懂得了夜的黑。
但是即便如此,誰又能保證你的小心翼翼就可以獲得一勞永逸的平安。
就在兩年前,離一所中學不遠的大路上,一位每天辛勤地擔負著孫兒接送任務的爺爺,正載著他的孫兒謹慎地騎行著,沒有任何預兆的,被一輛突然沖過來的大車碾壓。突然發生的事故,突然空下來的座位,慌亂了多少學生和家長的心。
而一家超市則經歷了更離奇的飛來橫禍,人們正在熙熙攘攘地進出、購物、結賬,工作人員正在有條不紊地排貨、導購、服務,一輛小汽車突然從停車場瘋狂地沖進超市,一時人群像炸開的馬蜂窩一樣慌亂,驚叫。那家超市因此冷清了許久。
雖然所有的肇事者最終都將被法律嚴懲,但死傷的人和他們的親人,卻承受了永遠也挽不回的痛苦。
還在教書時,學校曾推薦我去市里參加《品德與生活》的電教公開課比賽,內容自選,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交通安全的題材。大部分教學內容,書上是沒有的,必須自己找米下鍋。
我來到交警隊事故科,以期尋求一些知識和材料上的幫助。“學校太需要多上這樣的課了。”他們說,“干這一行,看到很多悲劇發生。”他們熱情地為我捧出一大堆宣傳用的小書簽和畫冊,然后,打開了電腦。
我看到一行行整理有序的事故圖片文件夾,每一個都清楚地標記著時間、地點、名字,打開細看,無不觸目驚心。面對血肉模糊的現場照片,恐懼、惡心、冰涼,各種難受的感覺摻雜交替,緊緊地攫住了我的心。同時,課堂的脈絡也在大腦中隨之清晰起來。
我選了幾組與孩子們的日常相關的圖片,制成課件,并為之配上了動情的話語和背景音樂。悲劇的畫面給孩子們帶來了強烈的心靈震撼,我看見他們有的捂住了嘴巴,有的蒙上了眼睛,還有的眼睛紅紅的。我們一起為死去的孩子祈禱,并一起感受生命的寶貴和脆弱。當音樂停止,他們一個個面色凝重,陷入長久的思慮,甚至流下淚來。
后來,這一堂課,我在很多地方很多個班級上過。那些平素快活的孩子,嬉皮笑臉的孩子,沒有一個不被震動,并暗暗握緊了小拳頭。其實,這樣的課堂每進入一次,我都感到心力交瘁。我多么害怕看到那些慘痛的畫面,多么不愿意讓幼小的孩子親歷這樣的疼痛。可是,蒙住眼睛,就能阻止事故的發生嗎?
我知道,我所做的也許極其有限。但是,哪怕只為他人種下一粒種子呢,一粒也好。
三
如果按年齡推算,站在被告席上的李生,正好與我當年教過的學生一般大小。此刻,他低垂著頭,溫馴、倦怠,多么像一個受到驚嚇初獲平靜的孩子。他剛剛被法警解除了手銬,雙手仍保持著僵硬和規矩的姿勢,仿佛轉動方向盤時那種灑脫和自如已經離他遠去。
身穿制服的公訴人神情端肅,即使是坐著,也能看出他的魁梧和威嚴。他在誦讀訴狀時語調鏗鏘有力,鼓點般聲聲敲擊著耳膜:“被告人李生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駕駛機動車超速行駛,并發生交通事故,致三人死亡,且負事故主要責任,其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在幾分鐘的訴狀宣讀過程中,我看見李生數次閉上了眼睛。每一個音節都像堅硬的石子,重重地擊打在他的心上。每一次重溫事故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細節,都讓他再一次陷入恐懼和戰栗。是的,如若不是心知此事與我無關,在這樣的環境,這樣催人懺悔的語勢覆頂的時候,我都能感覺到心驚膽寒。
而法官依例的詢問一波接著一波,姓名、職業、年齡……李生像一個小學生回答課堂提問那樣一一答復著。他答得很流利,他已經不是第一次接受這樣的問訊了。只是當法官嚴厲的目光掃視過來,并大聲喝問“你是否認罪”時,他還是禁不住身子一抖,忙不迭地點頭,聲音明顯弱了下去。“我認罪。”他說,有一種再也無力抗爭和辯論的頹廢感。
從2月14日出事到5月11日庭審,短短三個月里,他經歷了怎樣的精神煎熬,我們無從揣測。每當夜靜更深之時,他躺在看守所里,閉上眼睛,是否會一次又一次幻出一個父親和兩個小女孩的形象?從案卷可知,他是有自首情節的。當他雙手抱頭在馬路邊蹲下來,等待著交警的趕赴,他一定已經預知了今天的后果。那時候,下弦月還沒有從天空中升起來,四周黑得有些瘆人,除了偶爾路過的車燈,除了不遠處的村莊透過來的星星點點的燈火。幸而交警火速趕到,他束手待擒,一五一十地承認了自己肇事的事實,仿佛獲得了某種依靠和解脫。
同樣是在這三個月里,李生的家人也許扛起了更加沉重的精神和經濟負擔。作為親人,只要還有一點點能力,自然不希望看到李生承受長期的牢獄之災。他們必四處奔波,低聲下氣,從公安局到看守所,從律師事務所到法院,從醫院到受害人家屬,他們必一遍一遍地前往,尋求幫助,請求諒解。最后,他們付出了182萬元的昂貴代價,換取了受害人家屬的刑事諒解書。
可是,再多的賠償也不能換回三條鮮活的生命了。當一個悲傷的妻子和母親在一夜之間突然失去了丈夫和兩個孩子,當她多年的愛和付出被一夜清零,有什么能將感情和記憶隨之抹去,有什么能夠撫平她內心的劇痛和余生都無法停止的懷念?殞命者一去不返,金錢可以減輕一部分的刑罰,但不會潔凈一個人的罪孽。一紙諒解書,原宥的,只是肇事者的悔恨,但他犯下的粗暴行為和對生命的踐踏,不會在時間和事件中抹去。因為,生命只有一次。
人們喜歡在新年時許下愿望,彼此祝福。現在,新的一年已經走過三個月了,李生正面對刑罰,而他親手碾碎的那個家庭,再也不會有圓滿的新年之夢。時間中有那么多的不確定,我們總是希望未知的到來的都是美好。如果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終日都需要為著生命安全而擔憂,將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通常,每個人都不愿意面對公安、法院和檢察機關,這里,也許是為公民的生命安全以最后托底的地方了。
來自檢察院的公訴人,一定不止一次在庭審中提到生命這個詞語。他的最后陳述擲地有聲,而又動心動情:“本案帶給我們的啟示,不僅針對肇事者本人,也告誡我們每一個人,一定要珍視生命。作為一個社會公民,請一定遵守交通規則,請一定不要做違反公共安全的事,請一定尊重他人的生命!”一氣呵成的祈使句式,氣勢如虹的真誠話語,在偌大的空間里回蕩。
剎那間,法庭里安靜極了。李生,還有他身后的家人,無不面露怍色。也許,每一個人心里都在設想著無數個如果:如果當時車速再慢一點,如果不讓李生開車跑那一趟,如果沒有那輛影響視線的大貨車……任何一個如果,都有可能阻止這一次事故的發生。
然而,生命沒有彩排。
四
像一個相處日久,漸生麻木的物體一樣,生命常常于倦怠中被漠視。這種漠視,無論對于他人,還是自己,都像給生命裝下了不定時炸彈。
那個夜晚,女人騎著電動車持續手機語音聊天的畫面被我拍下。那是一輛體積較小的電動車,坐著三個人,一個六七歲的男孩伏在前面的龍頭上,一個八九歲的女孩趴在女人的背后。彼時是晚八點,街市上最為熱鬧的時候。她的左手上,始終握著發亮的手機,一會兒是盯著屏幕看,一會兒是貼著耳朵聽,一會兒是對著手機說話。一輛摩托車正飛一般從正前方駛來,她渾然不覺。直到“嗖”的一聲擦肩而過,險些相撞。街燈打在女人的臉部,照見她驚慌失措的表情。
當我把這個畫面發在微信朋友圈之后,引發了群情激昂的憤怒。有人罵她愚蠢、作死,有人譴責她對自己和孩子不負責任,還有人提到了交通規則,并一一指出她的違規之處。是的,她一定還沒有因此吃過虧,所以如此麻痹大意。
在安全的籠子里豢養太久的人,往往意識不到危險隨時都能像蛇一樣吐著信子噴射毒液。
自從手機成為普羅大眾的掌中玩寵,此情此景幾乎無處不在。多少人無論身處任何情境,隨時隨地掏出手機,就為接一個也許無關緊要的電話,回一個并非十萬火急的微信,刷一下可看可不看的朋友圈。他們大多數時候安然無恙,感覺危險離自己很遠很遠。
那些打著電話開車的人,不系安全帶的人,進入危險路段仍不減速的人,喝完酒騎摩托車在道路上風馳電掣的人。他們是我們的親戚、同學、同事、朋友,以及更多的陌生人。他們多是現實生活里堪稱本分,少有逾矩的人。他們不想成為悲劇的主角,也不愿意傷害別人,但他們又隨時可以成為馬路殺手。他們,是這個世界上集體無意識的龐大一群。
在李生的庭審中,律師指出了受害人騎電動車無牌無證,不戴頭盔,違規搭載十二周歲以下公民等行為。他的最后陳述沉痛而動情:“悲劇已經發生,一起三人死亡的交通事故,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具有較高的社會關注度。我們指出受害人違規的目的,不是為了指責某個人,而是希望法庭公正處理,以喚起更多公民重視安全知識,防止其他事故的發生。”
我曾在庭審結束后,與一位因危險駕駛罪被判一個月拘役的男人之妻聊天。“我們真的不知道這樣也會犯法。”她說。在女人眼里,丈夫是一個顧家、誠實的好男人,他在建筑工地上做工,每天辛苦賺錢,愛著家庭和孩子,他怎么會想要犯法呢?
然而誰能保證自己永遠是幸運的那一個?偌大一個世界,每天都在發生險情。我曾看著一個年輕人剎不住車,從麥菜嶺的陡坡路上疾馳而下,經石橋翻入河溝。我的一個鄰居道慶,為著生計去市區販魚,搭乘改裝的簡陋小六輪,從石羅嶺翻下懸崖,當場殞命。他的兒子,曾經是我剛參加工作時發蒙的學生,是我從教十多年來所遇的天資最聰穎學習最上進的孩子。可是由于道慶的亡故,他居然連大學都沒有考上。
正月里,人們正喜氣洋洋地奔走在道路上,走親戚、逛街市。而一輛從市區開往鄉鎮的公交車卻在經過臨縣境內時翻入深壕,造成了十幾人死亡、幾十人受傷的重大事故。那個鄉鎮,是我長期掛點扶貧的鄉鎮。在確知了掛點村無一人乘坐那輛車之后,我的心仍然于驚悸中顫抖。在那之前,我們單位工作人員進村經常租用一輛堪稱破舊的中巴車,在同一條蜿蜒的公路上,顛簸一個多小時。
后來,聽說事故原因是車輛嚴重超載,并且車子也已老舊。再后來,我們沒有再租用過那樣的車子進村。也許,那輛車不允許載客上路了。承包了城鄉公交的運輸公司新添置了多輛中巴車,每個座位都設置有安全帶。很多本來即存在,但久已疏忽的管理條例被重新嚴格執行起來,沿路都設有嚴格的檢查崗。所有的過往車輛不再允許超載,連同小孩。有時候我進村,也乘坐這樣的公交車,我看到那些從沒有系過安全帶的山區鄉民,被一再提醒和示范系緊安全帶,有時候還需要隨車工作人員親自幫忙系好。對于頑固不系的,甚至以趕下車作為威脅。
我在想,如果這些規范管理能夠長期地,一以貫之地實施下去,很多不該發生的事故,是不是就會被扼殺在搖籃里?如此,那一場發生在春節里的慘劇,無異于讓更多人獲救。
從來是亡羊補牢,猶未晚矣。
五
“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對于在憂患中度過了半年的李生及其家人來說,不啻為一個利好的結果。在這五年里,他將循規蹈矩,溫和,低調,收斂起年輕氣盛中所有的鋒芒,做一個決不觸碰法律邊界的良民。
擔任陪審員的這幾年,我參與陪審的交通案件,已達幾十起之多。當事雙方以及保險公司在法庭上因著民事部分的賠償反復拉鋸,其中因交通事故致傷致殘者居多。他們爭論著誤工費、醫藥費、床位費、護理費、營養費、交通費等等費用,還爭論著受害人的農民或城鎮居民身份,以使賠償標準于己方有利。
這樣的案件,如果購買了保險還好一些。現實是,一些報廢車無牌無證車無保險車輛仍在偷偷上路,一旦發生事故,對于雙方家庭,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
我多次在法庭上見到當事人家屬的爭吵、悲憤、痛苦、無奈和眼淚。一個六十多歲的婦女被車禍所傷,肇事者無證駕駛,并未購買保險。他一再逃避責任,更換手機號碼,只說自己沒錢,連過年都不敢回家。受害方氣得捶胸頓足:“如果是你自己和你家人受傷,再窮再苦,你會不去治嗎,會眼睜睜地看著人痛死嗎?”受害方一再降低自己的期望,從十萬元的賠償訴求降至三四萬,對方仍說沒有錢。肇事者的父親一直說不關他的事,直到害怕兒子坐牢,才提出愿意賠償,但聲明沒有錢,只能慢慢分期付。
受害人最后是哭著離開法庭的:“沒錢,你就不能好好騎車嗎?”
是的,這句話觸及了太多人的痛處。如果前文中的李生,如果沒有錢,那么他就無法以高額的賠償換取受害人家屬的刑事諒解書。而像李生家庭這樣具備較好經濟賠付能力的人,在社會上永遠只是極少數。更多的人,一旦出事,則意味著赤貧、巨債,隨之而來的,也許還有家庭的破碎和離散,子女教育的無以為繼,親人疾病的無力醫治。
從人民網官方微博的數據可見,中國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已是世界第一。近年來,每年死亡人數高達六萬多人。不用說,每一起事故的背后,都裹挾著家庭的悲劇與活著的困境。
我注意到,在李生的檢查報告中載明,他的血液里沒有檢測出酒精和毒品。這一事實,成為他被減輕刑事責任的一項重要依憑。毒品、酒精,這兩樣充滿魔性的事物,食之,能讓人亢奮,讓人狂妄,讓人由內而外散發著癲狂的力量和唐突的攻擊性。也因此,每當交通事故發生,雙方當事人都必須接受酒精和毒品的檢測。
這其中,毒品是違禁品,接觸者畢竟不多。而酒,卻幾乎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氣氛調節劑。老與少,貧或富,坐在一起,即可喝酒,將自己,將他人灌至爛醉,然后搖搖晃晃地各自回家。有時候,他們仍過度相信自己的行動和控制能力,滿嘴噴著酒氣,開著汽車,騎著摩托車、電動車,沖上道路。在酒駕檢查不太嚴厲的那些年,這樣的畫面是男人們酒足飯飽之后的常態。
即便有人尚留理智,捂住酒杯,聲稱還要開車,但他們必不會被酒友放過,自有一幫勸酒者激將道:“再喝幾兩,這點酒對你來說算什么?上次我喝了一斤還安全開到家。”在鄉村工作時,會聽到更多關于酒后失控的故事:比如一個計生辦主任自恃酒量高,車技好,一次喝完酒回鄉鎮,將車子開進了水稻田;比如村里一個男人夜晚酒醉后騎摩托車回家,馬路前方駛來了一輛汽車,他將兩個車燈認作是兩輛摩托車,硬從車燈的中間直沖過去……更多的是聽到某某喝醉酒打了吊針,過了一兩天又被兄弟們拉上酒桌的事件。只要一息尚存,他們樂此不疲,他們甘愿受罪,甚至將之上升為酒文化。
就在前不久,我的老家麥菜嶺的一位堂叔突然打通了我的電話,訴說因酒駕被扣了車子。他的舌頭還有點大,酒一定喝得不少。他囁嚅著對我說:“你在市里上班,能不能幫我找一下交警的關系?”那一刻,我感到被大水淹沒般的窒息。沒錯,在那個小村子里,我是他們眼中唯一一個出來吃公家飯的人。可是我知道自己幫不了他,假若被查獲的人換作我,也只有乖乖認罰的份。
然而在我的記憶里,他是一個對人多么好的人。小時候,他把難得的零食塞到我手上,親昵地叫我秀秀;老家建房時,他開著小六輪幫忙裝運磚頭;有一年除夕,我家車庫的卷閘門突然壞死,找不到一個可以救急的人,是他開著拖拉機,載著工具前來修好,并堅持不收一分錢……
現在,他第一次有事求我,可我卻什么也做不了。我該恨自己的無力,還是他的無知?我狠心地給了他一個無望的答案,掛斷了電話。他會懂得我的無力嗎?也許不會。那個晚上,我失眠了。李生在庭前受審時懺悔的樣子,還有案卷中三個血肉模糊的尸體的照片,輪番在眼前跳躍。
這時候窗外的弦月升起,冷輝照進居室以及心房,如同路魘,陷我于虛弱,陷我于一個人的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