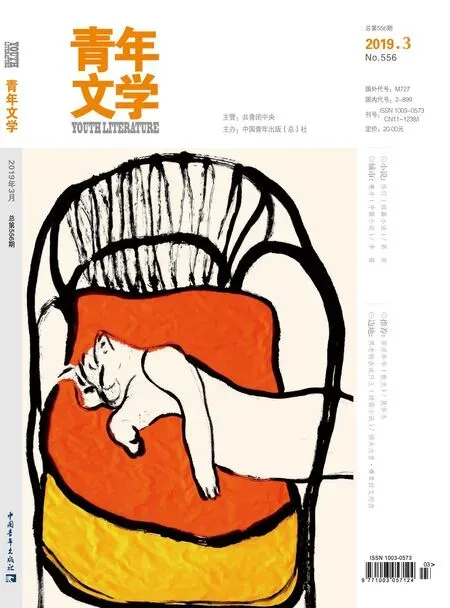空曠的人性
2019-11-13 14:59:30⊙文/李笛
青年文學
2019年3期
關鍵詞:人性
⊙ 文 / 李 笛
《兼并》是個很普通的復仇故事。與那些發生在真實世界的事件相比,這篇故事的情節遠遠算不上跌宕起伏。由于行文比較幼稚,重讀這篇作品時,每每令我自己汗顏,感到它只能算作一個文學愛好者的習作。因此,我想利用這篇后記的機會,來闡述一下自己沒能在故事中表達清楚的創作意圖。
為什么平杉有機會完成這場復仇?他那些看似復雜的、通過操縱心理而實施的、最終甚至手不沾血的犯罪,是難以實施的嗎?
在我們所熟悉的物理世界之中,身邊的每一個物體都是質密完整的。譬如一個鐵塊,它看上去是那樣的堅硬,沒有絲毫漏洞。然而假設我們能夠以原子的尺度去觀測它,一切都大相徑庭了:原子核孤零零地飄浮在空間中央,周圍稀疏地環繞著電子。我們熟悉的鐵塊無影無蹤,眼前空曠得就像是撤去了所有藏品的博物館一樣,到處是寂寥、巨大的空洞。
人性就像是另一個鐵塊,看似質密完整,實際極其空曠。平杉就行走在空洞中。通過與前述類似的觀測尺度,他得以看到那些巨大的機會,因而能毫不費力地踱步過去,直達人性之中的弱點,通過操縱對方的心理去完成復仇計劃。
當然,這個故事無疑是“偶然”的。例如易鳴實施謀害父親的行為,抑或是故事開始時的那場車禍。一眼看上去,假如它們并未恰好發生,似乎這場復仇就無法實施了。實際上,這些“偶然”并不是故事的瑕疵。因為大多數宏觀上的偶然,都由微觀上的必然構成。……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雜文月刊(2021年11期)2021-01-07 02:48:01
阿來研究(2020年1期)2020-10-28 08:10:14
攝影與攝像(2020年12期)2020-09-10 07:22:44
文苑(2019年24期)2020-01-06 12:06:58
新產經(2018年3期)2018-12-27 11:14:16
海峽姐妹(2018年4期)2018-05-19 02:12:54
影視與戲劇評論(2016年0期)2016-11-23 05:26:47
工業設計(2016年10期)2016-04-16 02:44:06
人間(2015年17期)2015-12-30 03:41:08
南風窗(2003年12期)2003-04-29 00:00:00